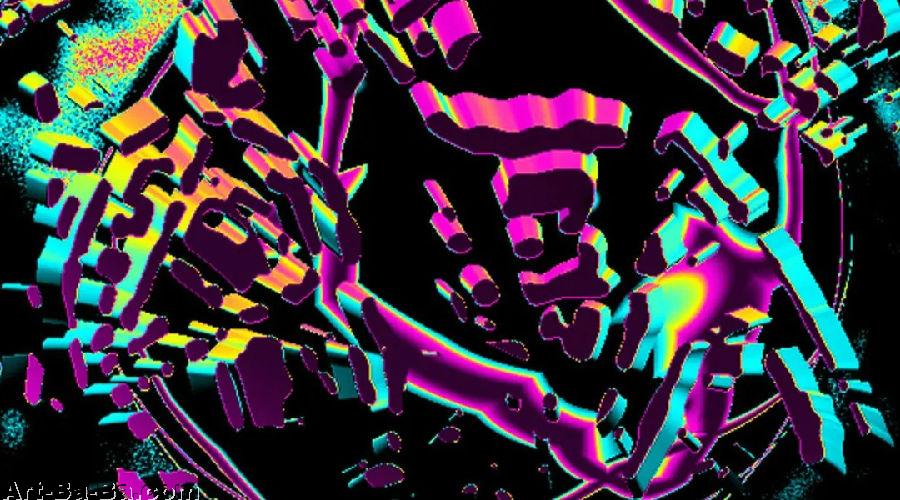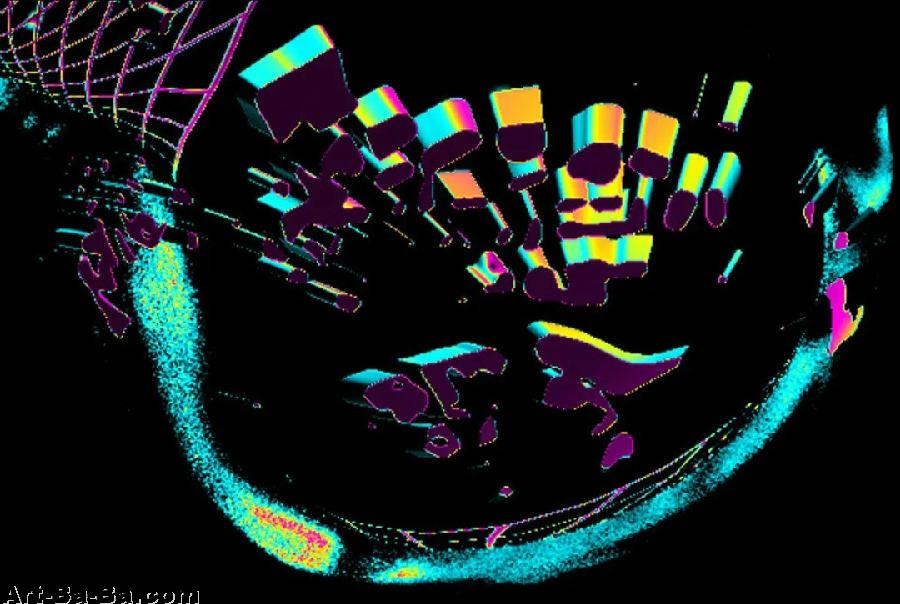来源:黑齿杂志
编者按:
新冠疫情在全球继续肆虐,在美国和欧洲因种族仇杀引发的#StopAsianHate和#BlackLivesMatter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病毒性和病毒式传播:针对一个标准的生命单位》一文以实验性的方式试图思辨“病毒”和“暴动”之间的关系,将病毒的两种复制模式(溶源性和溶解性)与暴动的滋生过程、社会效应进行类比。通过合作书写的方式,两位作者结合各自的背景知识(H·博林[H. Bolin]是作家和翻译家,索纳利·古普塔[Sonali Gupta]是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候选人)探索生物政治、全球资本关系、国家机器和西方政治秩序等话题。与此同时,这种尝试难免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文章中文译者朱晓闻所指出的:某些段落较为艰涩,她在翻译过程中多次请教王冠博士,力求准确;此外,文章主旨和概念以美国中心主义为框架,尽管力图客观仍不免有所局限。
译者按:
两位作者联系当下两大热点:“病毒”和“暴动”,且将病毒的两种复制模式(溶源性和溶解性)与暴动的滋生过程、社会效应进行类比,某些段落对于距离生物学较远的读者来说不免艰涩。翻译过程中,译者多次请教王冠博士,力求准确,如若有误,欢迎读者不吝赐教。另,本文主旨和概念框架偏美国中心主义,译者以学习心态进行翻译,并不敢苟同文中所有观点,特此声明。
自从我们作为单细胞生物在地球上爬行以来,病毒就一直在挑战人类的进化命运。病毒将自身基因插入其感染的细胞中,从而混淆每一个遭遇它的生物的家谱。 病毒既能破坏身体,大肆传播,又能利用身体的免疫反应对之进行编码。这种持续不断的互生共存就是病毒驱动地球上每个物种进化的方式。新冠病毒所引发的疫情对于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持续存在的形式和功能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冠状病毒像攻击我们的肺、心脏和免疫系统一样,顽固地占领了全球帝国的庞大身躯。联结全球贸易和资本主义循环系统的供应链由此变得岌岌可危。断绝接触、偏执妄想和看似无尽的等待标志着隔离的特征,亦反映了全球范围内的深度代谢疲劳。
面对这一威胁,我们能否以一种超越善恶的方式来理解病毒?也就是说,既不赞扬(如优生论者或厌世主义者那样),也不因恐惧而瘫痪——不加批判地接受国家采取控制和紧缩的措施,以期恢复正常。前者口含天宪,后者贪生怕死,皆不尽理想。综上所述,这两种极端有效催生了生物政治治理的逻辑——使人生死存亡。我们应承了以健康为基准的政治,无论是采取诸如强制执行军事化隔离和宵禁、胁迫接种疫苗、对社交聚会施以行政罚款的措施,还是诸如接触者追踪及位置追踪一类侵犯隐私的措施,都看似合理——因为部分民众会因此获益。国家控制进一步迅速扩展到生物政治领域,唯一与之对峙的,是一批狂热者,他们沉迷于否认新冠病毒,支持阴谋论、反口罩言论,甚而包括财政紧缩措施——这些措施本质上是优生主义,它们选择了让人死亡。我们寻求一种避开生物政治的生存方式,即使在第六次大规模灭绝中,这种生存方式也要直面病毒存在的事实,以表现出新的生命形式。只要危机不威胁到全球资本关系,由病毒引发的死亡就仿佛无伤命脉。尽管登革热或黄热病等病毒仍在肆虐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造成死伤无数,但我们未见有国际协调的国家应对措施。[1] 与之相对,新冠病毒疫情在东亚、美国和西欧蔓延,这些地区恰好构成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核心。如果我们认为,资本无休止的增长破坏了栖息地,从而导致了冠状病毒大流行这一溢出事件,[2] 那我们可以说,面对疫情,国家层面的应对措施使我们陷入当前的窘境而没有做出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的生物政治控制法无法应对病毒的成因;它们将物种维持在消亡的状态。病毒在肉类加工厂、隔间农场和监狱中溃烂,这些场所原本就以令人发指的生命消耗为周转条件。新冠病毒揭示了这一点,即帝国被感染的核心只会复制疾病,因而,在全球范围内彻底重组生命成为当务之急。革命的问题现在成了进化攸关的问题。这场疫情爆发于全球前所未有的暴动浪潮之中,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3] 是否有可能将病毒和暴动视为一股合力的两种表现形式——为了躲避全球资本和经济治理的帝国?我们进行这种比较并非出于类比,而是为了了解,正如伊德里斯·罗宾逊(Idris Robinson)所书:“围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隐藏的党派知识,也可以被利用和武器化,以对抗现有的权力体系。” [4]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政治控制措施未能充分应对我们的集体局势,这一局面在下一波疫情和下一波示威游行之间持续振荡。然而,我们将其视为统一的现象,它有自己的逻辑,自成一体,趋舍有时。病毒的计谋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行动的投射,令我们在日益难以居住的星球上,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得以开拓新的视野。超越生存演算的生命
也许上帝是一种寄居在我们体内的病毒。
——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
大卫·凯利(D**id Cayley)在一篇关于生命政治的精彩文章中写道:“‘史上最严重的医疗危机’所要求采取的措施……明显以避免死亡之由,削减了公民保护生命的自由。” [5] 政治治理者将生命本体作为对象,试图强迫其适应,更重要的是,在面对物种的选择压力时,不去改变。 如果是这样的话,生命政治可以帮助我们与生命的统治者作斗争吗? 我们如何在这种对抗中插入不对称性? 只有超越生命或介于生命之间的事物才能做到这一点。病毒并没有依附于生命、自然和历史这些内在范畴来指导我们的政治想象,而是为我们注入了一种陌生的知识,令我们重访神学的问题:超越这些既定范畴的是什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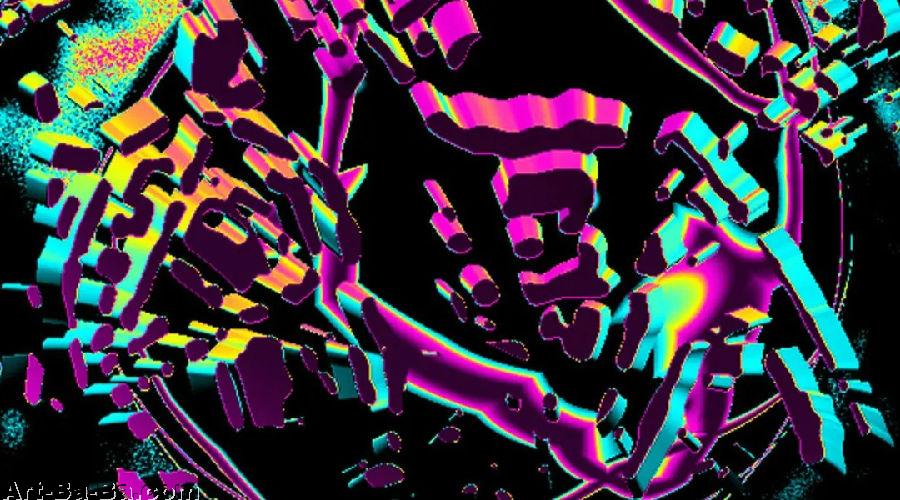
病毒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阈限空间内。少量的遗传物质包含在一个完美几何形的分子包膜里,以某种方式进行自我繁殖,操控其环境,适应且进化,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在生命中找到。 然而,病毒无法呼吸。无论你称其为“普拉那”(prana,能量、生命素)、“气”还是基本的生物化学,呼吸都只是能量转换的代谢过程。 能够呼吸的最小实体是细胞,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其定义为“生命的基本单位”。 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和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遗言“我无法呼吸”反映了美国黑人的特殊经历。 然而,当全球疫情扼杀数百万人的生命,不可控的森林野火摧毁地球之肺时,这句话也像一种幻影般的痛苦在我们胸中回响。在这座星球的窒息中,我们关注那些不呼吸却仍然活跃的病毒。从流行病学模型到通信网络,治理系统寻求绘制信息来源,构建各种谱系,以约束和引导信息流。 相形之下,病毒式的信息传播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受限制和反系谱的。病毒爆发的起源通常是未知的,犹如一次咳嗽般短暂。 在没有任何中心逻辑支配其传播的情况下,病毒只是简单地通过任何可用的媒介繁殖,就像野火一样。 病毒不在乎宿主是住在监狱还是白宫,从而跨越了应经济而生、由国家维持的秩序。 现有的感染点,如工作场所、教堂、夜店、法院等,都被暂停运营,因为我们的关系首先被界定为我们与病毒的关系。作为对疫情的迅速反应,互助和住房保障网络在美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为人们觉察到,国家无力控制危机。这种资源和通信网络的大规模重组产生了不一样的连接层面,即丰富的政治蔓延媒介。用生物学的术语来说,病毒信息的传播是通过基因水平转移的。 病毒会将一种宿主的基因转移向另一宿主,从而使基因可以在种、纲、目,甚至界(kingdoms)之间横向共享。[6] 因此,如果物种根据基因实现个体化,DNA是生物主体的条形码,那么病毒就是大自然去主观化的机器。作为生态系统的同步者,病毒通过纠缠它们遇到的所有生命形式的遗传轨迹来促进协同进化。病毒对于生命通过系谱分类而被赋予的树状目是陌生的。相反,病毒扮演一个连接的角色,解开生命之树,遇到每个身体,仿佛超越属(genus)或界,自立门户。今天,我们看到这种病毒性传播模式开始破坏现有的政治家谱。 如果二十世纪的革命进程是由特定构成的团体指挥的,无论是党派、工会还是阶级,那么在今天的起义中,这些力量将被模因(memes)、信息图表和Instagram“故事”所取代。信息流突破了他们的控制论约束,并帮助无领导者小组与完全陌生的人协调行动。 起义成为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唯一的联结元素,不需团结为一个机构集团或连贯的革命主体,就能使预先编纂的联盟和身份受到质疑。 病毒性传播指的是一种传播方式,这种方式破坏了机构集团之间的相互联系,混淆了它们在既定秩序中的地位,为产生剥夺性权力奠定了基础。冠状病毒在两种病毒复制模式,即溶源性和溶解性,之间具有生物学转换,分别对应于两个不同的时间和功能。 溶源性由长期的、缓慢的、无形的重构组成,而溶解阶段的特征是速度和破坏。 在溶源性模式下,病毒基因整合到宿主基因组中并通过宿主细胞的常规复制繁殖。 当溶源性变为溶解性时,宿主细胞成为生物工厂,新生病毒数量呈指数级上升趋势。 到此时,宿主才有症状显现;只有当潜在感染超过临界点时,病毒才会现身。就像病毒插入其基因以转化宿主的基因组一样,即使它继续发挥正常功能,也会改变身体;因此,在社会破裂之前,人们应进行隐秘的重建(或解构)。如果说,新冠病毒的溶源阶段为2至14天,则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活动的溶源阶段则为数年。溶源阶段可视为“社会和平”时期,没有症状,亦没有明显的动荡迹象。这些时期提供了孵化的机会,在这个阶段中,现实的支持者有时间用编码的指令和框架来感染社会主体,因而当溶解阶段(总是不可预测地)开始时,我们有公式可循,而此时,维系我们世界的物理定律已然瓦解。2019年,伴随暴动蔓延至全球的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这波浪潮迟早会席卷美国的东西海岸。我们注意到起义,并且寻找用于协调的工具和策略。随着激光、雨伞和处理催泪瓦斯技术的引入,这些知识在美国许多城市中日夜夜夜地被重复使用。2020年5月26日,当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活动开始时,在疫情初期为协调房租罢工而组建的“电报”(Telegram)小组改头换面,转而帮助游行人群利用警讯监控仪提供的实时信息战胜警察。将一个社会的和平时期转变为溶源阶段,意味着试图解构形式和主体的现有功能,使它们成为逃避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病毒不一定会通过破裂影响宿主的功能。实际上,我们的DNA中有8%是由古代病毒的残留物组成的。[7] 这些病毒遗传序列最初被认为是“垃圾DNA”,因为与那些映射到细胞内具有明确功能的基因相比,它们的表达是沉默或嘈杂的。现在我们知道,DNA中的这些病毒成分调节着我们的天然基因,对于怀孕和免疫等基本功能至关重要。[8] 因此,当病毒潜伏期足够长时,它就会成为记忆。一位哲学教授在去年感叹说,他大学一年级课程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记得“占领”运动。他说,如果不了解这一历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有助于解放的视野。一年后,我们发现青少年和刚从高中毕业生都参与了街头最勇敢、最具创意的抗议运动。我们不需要记住“占领”,就能知道在合适的时机如何行动。这样一条嵌入记忆的线索看似沉默,但仍会在其自身的时间尺度上表达自我。我们从政治宗谱中追寻历史,而事实上,历史恰恰是由那些破坏既定宗谱的因素所创造的。从溶源性到溶解性的快速转变中,病毒基因开始系统地重新利用细胞机制,以指数方式产生新病毒,这些新病毒从破裂的细胞中爆发而出。 当社会机构消解时,战术、形式和思想就会自我复制。我们看到,文明的身体成为记忆的媒介,正如细胞成为纯粹繁殖的温床。 我们的目标不再是阻止资本流动;相反,作为欲望自由流动扩散的必然结果,资本成为困兽。就像法农所言:“我要试着彻底溶解这个病态的身体。” [9]病毒是地球上进化最快的有机体。它们的进化速度可归因于其指数级复制——单个实体的副本越多,获得适应性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 每一种变异都增加了(免疫)逃逸(evasion)的可能性,使病毒传播难以控制。例如,流感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有些年疫苗的有效性只有10%。[10] 这里有一个极具意义的概念,即系统中的冗余会产生新的逃逸向量。洛杉矶警察局局长最近表示,一个一万人口的单位比十个一千人口的单位更易控制。[11] 这些冗余都保留了分化为新威胁的能力,分散系统资源以遏制不断演变的传染。这种动力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活动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传播使联邦政府的协调反应失去方向。在明尼阿波里斯市,有这样一个故事:抗议者经常在发生爆炸事件后,被人群中的某人警告说,国民警卫队就在十分钟车程之外!这个空洞的警告被重复多次,以至成为一个“狼来了”的笑话。实际上,国民警卫队在当地事件平息后才到达示威游行地点,而此时抗议活动已然在另一座城市达到顶峰,警卫队则只能负责清理和收拾残局。 全国范围内的溶解速度反映出,在国家机构、公司、左派组织和非营利机构面前,人群能够“观察、定向、决策和采取行动”,[12] 留给警卫队的,不过是满目疮痍的辖区或是被洗劫一空的商店,他们也只能做一些类似尸检的工作。溶源和溶解阶段之间的转换是不确定的,是概率性的。病毒基因在宿主的生物学环境中形成复杂的组合,如各种环境刺激,对系统的短暂扰动,以及活体生物持续的背景噪音,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突破溶解阶段阈值的可能性。[13] 同样,也没有算法规定导致社会破裂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策划暴乱。一场特定的选举或对一个杀人警察的无罪判决,会导致民众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预测和权威意见不断落空,因为迅速过渡到破裂只取决于内部随机因素的不断复合。这种相变(phase transition)的固有统计性质是(免疫)逃逸的必要特征;如果这个过程是确定性的,就可以排除它。(免疫)逃逸只有当(突变达到一定程度)病毒被惊讶到的时候才会发生。冠状病毒疫情的到来具体化了维护西方政治秩序的各种类别的不稳定,而国家的管理和民众的反应则在混乱中反映了这种不稳定:右翼在抗议封锁时似乎高举自由的火炬,而左派则坚持规章制度并对右翼作出回应。尽管政治两极似乎暂时被颠倒了,但这并不奇怪,无论是哪一极,还是任何一种既定的政治权力,都没有对我们集体弊病的根源作出回应。全球性的起义浪潮指向一个仍然模糊的地平线,超越了挟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新型经济控制形式。虽然这些起义似乎侵犯了二十世纪的政治范畴,但政党、阶级和程序的缺失(或是过时)也使它们陷入一种类似于困扰秩序的混乱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澄清这个时代的新思想,只有通过学习病毒的语言——消除政治家谱,对社会主体及其古老的移动速度进行潜在的重新配置——我们才能开始了解这些新形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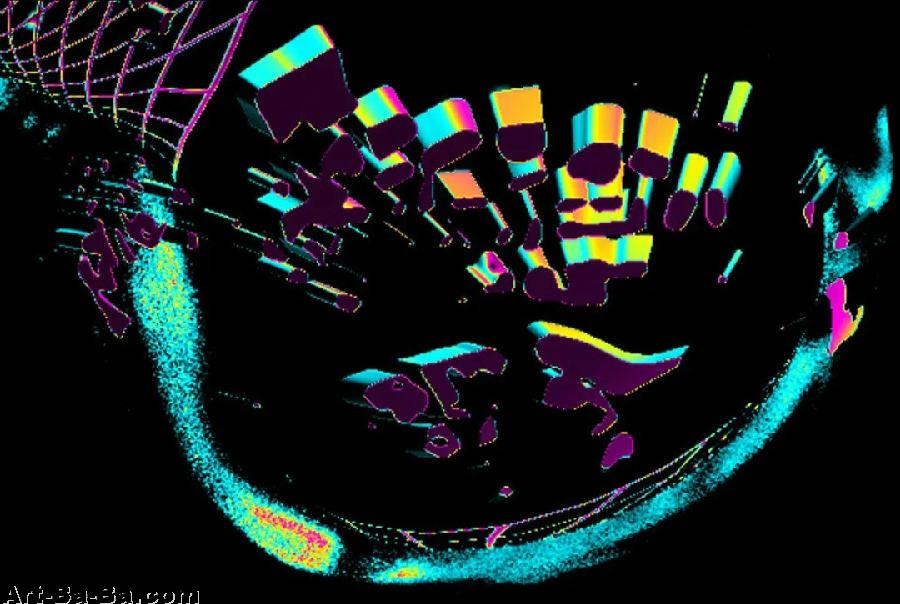
病毒是生物界的罕见事物。由于没有可追溯的起源,病毒既是史前实体,也是进化的最前沿。病毒始终是逃犯,永远不会“属于”它所寄居的生物体,至多对身体来说是陌生的,而最坏的情况是感染。病毒本质上是不纯的;它已被一切所接触,却又不可救药地寻求进一步接触。病毒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在巨大的记忆时间和微生物复制的超快时间尺度之间摇摆。它通常是沉默的,但就像弗雷德·莫顿(Fred Moten)谈及某些音乐时刻的所言:“被误认为沉默的东西,会在突然间变得不可思议。” [14] 病毒基因组永远不完整,不断被重写,它破坏了生命的语言,就像一条连接过去和未来的通电管道。病毒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何形状,呈无数种形式,但不能称为生命形式。病毒总是小于生命的基本单元,它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微小空间中,似有还无,带着血迹——也正因此,病毒生生不息。*原载于《e-flux journal》第#115期,2021年2月
*所有图片均由彼得·波拉克(Peter Polack)提供
原文作者:H·博林 & 索纳利·古普塔
英译中:朱晓闻
译文编辑:翁笑雨、顾虔凡
[1] CDC, 《全世界的登革热》“Dengue Around the World,”cdc.gov, https://www.cdc.gov/dengue/areaswithrisk/around-the-world.html[2] Chuang, 《社会传染:中国的微生物阶级战争》“Social Contagion: Microbiological Class War in China,” chuangcn.org, 2020, http://chuangcn.org/2020/02/social-contagion/[3] 自2021年1月6日极右势力入侵美国国会后,“暴动”一词在主流话语中经常被用来指代对国家权力这块空白地带的一场日益暴力的仲裁。我们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是完全不同的。笔者用暴动来指代集体发明的新地形,正如整个乔治·弗洛伊德抗议活动所展示的那样。[4] Idris Robinson, 《应该怎么做》“How It Might Should Be Done,” Ill Will Editions,2020年7月20日,https://illwill.com/%20howit-might-should-be-done[5] D**id Cayley, 《从伊万·伊里奇的角度来看关于当前疫情的问题》 “Questions About the Current Pandemic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van Illich,” d**idcayley.com, 2020年4月8日,http://www.d**idcayley.com/blog/2020/4/8/questions-about%20-the-current-pandemic-from-the-point-of-view-of-ivan-ill%20ich-1[6] Shahana S. Malik et al., 《病毒会在生命超级王国之间交换基因吗》“Do Viruses Exchange Genes across Superkingdoms of Life?” 《微生物学前沿》(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2017年10月21日,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icb.2017.02110/full[7] Nicholas Parrish 和 Keizo Tomonaga, 《哺乳动物的内源性病毒序列》“Endogenized Viral Sequences in Mammals,” 《医学病毒学评论》(Current Opinion in Microbiology), no. 31 (2016年6月):第176–83页。[8] Edward B. Chuong, 《胎盘里的病毒:逆转录病毒控制妊娠期基因表达》“The Placenta Goes Viral: Retroviruses Control Gene Expression in Pregnancy,” PLOS Biology 16, no. 10 (2018年)。Tara P. Hurst and Gkikas Magiorkinis, 《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激活先天免疫反应》“Activation of the Innate Immune Response by Endogenous Retroviruses,” 《普通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9] 法农, 《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Pluto Press, 2008年),第3页。[10] Edward A. Belongia 等人合著, 《从2004至2005年流行季节到2006至2007年流行季节,灭活流感疫苗的有效性因抗原匹配而有很大差异》“Effectiveness of Inactivated Influenz***accines Varied Substantially with Antigenic Match from the 2004–2005 Season to the 2006–2007 Season,” 《感染病杂志》(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199, no. 2 (2009年): 第159–67。[11] Bill Melugin (@BillFOXLA), 《最新消息:洛杉矶警局的消息来源给我发了一封摩尔局长周六晚发给警察的信》“NEW: LAPD sources sent me a letter Chief Moore sent out to officers Saturday night,” Twitter,2020年11月9日,https://twitter.com/BillFOXLA/status/1325986523766947840[12] 这种决策范式被称为OODA循环,由美国军方开发,但在抗议活动期间被示威者最有效地付诸实践。[13] Abhyudai Singh 和 Leor S. Weinberger, 《随机基因表达作为病毒潜伏的分子开关》“Stochastic Gene Expression as a Molecular Switch for Viral Latency,” 《医学病毒学评论》(Current Opinion in Microbiology) 12, no. 4 (2009年):第460–66页。[14] Fred Moten, 《黑暗与虚无(肉体的神秘主义)》“Blackness and Nothingness (Mysticism in the Flesh),” 《南大西洋季刊》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2, no. 4 (2013年):第737–80页。作者H·博林(H. Bolin)是作家和翻译家。他的作品见于《口罩杂志》(Mask Mag)、《绊网》(Tripwire)和《新探索》(The New Inquiry)等。
作者索纳利·古普塔(Sonali Gupta)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候选人。中文译者朱晓闻,是一名居住在柏林的艺术家和写作者。她的双语艺术家书《Oriental Silk 乡绸》于2020年由德国出版社汉杰·坎茨(Hatje Cantz)出版。她的个人网站是:zhuxi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