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ARTDBL

欧宁,2012年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摄影:王久良
受访者:欧宁
采访及编辑:黄紫枫
受疫情的阻滞,全球性流动大幅停摆,无论是被动的蜗居,还是主动的驻留,如何重新面对地方、思考地方的涵义已是每个人生活中难以回避的问题。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艺术机构围绕着“地方”的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应,寒山美术馆的展览《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则让我们看到了对待地方的别样呈现:“地方”不再站在和观众相互对望的位置上,在预先设定的地方框架下,地方话语并没有强势地挤压着个体经历,反倒是随着收敛的作者性、恰当的地方叙事尺度,以声场般的包围感,形成了一种朦胧的、开放的、却能被“把握”的本地感知。
为此,我们和本次项目的主持人欧宁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搭建平台、激发参与的协调员,同时,我们也能从他研究员的身份,以及过去不同场景的工作中,梳理与“地方音景”工作方法的相关线索。文章发布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文中用图,如无特别说明,均由寒山美术馆提供。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田野录音现场
ARTDBL:先谈谈你作为主持人介入“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这个项目的契机?
欧宁:我和寒山美术馆馆长布达认识是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布达还在法国留学,办了一本独立文学杂志《生羊毛》(Surgemagazine),想要跟我要一首诗刊登,就这样认识了。等到他回国做了寒山美术馆的馆长,也陆续保持着联系,这次项目他来找我,出发点是看到苏州还有二十几家唱片店,在现在这个实体音乐衰落的时代里挺不容易的,他想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提到唱片店,我就想到了声音这一媒介,正好2017年秋天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研究生学院开设了“地方营造与策展实践”的课程,我建议布达或许可以用工作坊的形式进行这个项目。课程探讨社会参与艺术和地方营造的关系,强调艺术活动的社会参与要素,通过艺术的形式去加强社区联系和地方认同感,再通过进行工作坊,以展览的产出作为工作坊的结果。
我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做了很多音乐活动,后来慢慢过渡到声音艺术的工作中。2006年,蛇形画廊曾经邀请我在伦敦巴特西电站策划一个声音艺术的展览项目“唤醒巴特西”,这是我第一次做声音相关的展览项目。巴特西电站曾出现在平克·弗洛伊德一张经典唱片《动物》的封面上,可是因为建筑年久失修,涡轮大厅的顶部经常掉灰,很危险,观众无法走进建筑内部,于是我便找了二十几个中国声音艺术家,他们基于来自各省的田野录音进行创作,最终将时长接近4小时的音轨安装在大厅内部,这样一来观众站在入口能听到声音的作品。为此我还成立了“声音学院”(Institute of Sound),以此命名参与该项目的艺术家们。
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声音艺术家们基本上处在一个演出的状态之中,哪里有演出,带上一个笔记本就去了,放出来的声音都是噪音,我感觉这种形式跟社会的连接太少了。伦敦这个项目之后,我提出声音作为重要载体的主张,声音负载着很多有意思的社会信息,或许能够将田野录音跟城市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结合在一起。到2007年大声展的时候,颜峻负责声音艺术部分的策展,我们一起做了很多有意思的项目,比如 “听游记”,我们把声音艺术家根据田野录音创作的作品放进车里,观众坐上车,一边听声音,一边跟着田野调查的路线去看对应的街景。
所以在决定要做苏州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还是沿用了强调声音和城市关系的这一思路,而地方研究也是我这几年来非常关注的事情,最终确定了展览的标题叫做“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同时加入“地方”的概念,强调整个行动过程跟苏州这座城市的关系。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田野录音现场
ARTDBL:听你的描述似乎切入点在于声音,而苏州更像是试验场一般的存在,能否说相应的方法论可以套用在不同的地方之上?
欧宁:这次工作坊的消息发出去以后,我就收到了两三个邀请,3月份我将会去到苏州东山太湖边上的一个农村,接下来会在太原再做两个类似的工作坊。在一个只针对农村的语境里面,肯定会有新的东西,这类项目在农村做可能会比城市更有意思。现在很多人会去农村旅游,住民宿,找当地的风物,却很少有人从声音的角度去感受农村,它和城市音境一定是很不一样的。3月份是东山碧螺春采茶的季节,我非常期待那个时节农业生产的声音。
尽管我们采用了一样的方法,但它并不会成为一个“模式”,我们要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和城市。在同样的大框架内,我们要根据地方去调整,这也是“地方知识”的原则——它不可言传,无法学习,一直在实践中发展,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
项目英文名叫做Native Soundscape,指的就是本地才有的声音特性,强调声音作为媒体对某一特定地方的呈现,去挖掘一个地方的声音遗产,当代的声音标志,找出在声音上区别于其它地方的特点。我们提出“声音遗产”这个概念,无论是物质遗产、还是非物质遗产的保护,都是这几年来很多地方在进行的工作,却很少会有人说要整理声音遗产。这次苏州的项目,我们是在建立一个针对特定地方的完整方法论——通过在地工作坊、田野录音深入地方,再通过教学的方式产出展览。
ARTDBL:既然有了一个相对可依循的方法,参与者又是带着怎么样的视角、什么样的问题,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去进入田野的?
欧宁:田野录音最根本的一点是要进入城市生活的现场,我们会在进行田野录音前做一些调研——苏州分为几个区,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古城区主要是历史的积淀,东边是由新加坡企业出资建造的工业区,西边是高新区,太湖周边则主要是农村。我们还向负责苏州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了解这座城市的规划是如何进行的,所以我们在真正走上街头时,是带着一个预设框架的,但我们并不会排除走街时的意外收获。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工作坊现场
ARTDBL:在工作坊的教学过程中,它的教学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和学院教育的流程有什么不同之处?
欧宁:我把工作坊的教学实践称为Alternative Pedagogy(另类教育学),学校是老师教学生,而我们是“共学”的,我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按照学校里的制度方法来说,我就是导师,但实际上我总共讲了4课,还有颜峻、李劲松、张安定、郭廖辉、王基宇、王婧六位特邀演讲者,此外,公开征集的16位参与者,每个人也要作出各自20分钟的分享。他们讲的时候,我在下边听,学习,跟着他们一起走街串巷做田野录音,实际上打破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区别。
我们的参与者中有技术方面非常厉害的声音工程师,特邀演讲者中有人类学学者,像王婧,她或许是现在中国最前沿的一个声音研究者,声音理论做的非常深入,而且以像德勒兹哲学的理论去引导研究。尽管她立场可能是基于声音本体论的,和我的看法有所出入,但我还是能从不一样的观点中学到很多,特别是她认为“音景”(Soundscape)这个词还是带有视觉中心的倾向,人并没有在声音其中,于是她提出了人被声音包围的“音境”(Acoustic Milieu)概念,这恰好跟我对地方的研究理念是一致的。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田野录音现场
ARTDBL:音景、音境、地方、空间的旨意具体差异在哪?
欧宁:Soundscape中文叫做音景,是从人文地理学Landscape(风景)那里来的,然而Landscape总带着一种从外部观看的视角,主体是在外的。就像是旅行者去到一个景点一样,对于他们而言,那里不存在社会关系,没有个人记忆,也无法形成身份认同,他们永远是站在外面往里看的,只有当人的主体安放其中,才成了“地方”(Place)。地方是有感情、有个人记忆、有历史,并永远身处其中的,这些是旅游者难以感知的东西。
“空间”(Space)跟地方是不一样的,Landscape跟Place也是不一样的。如何让一个空间变成一个地方,这是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主题。一个刚装修好的房子,那只是一个空间,当你把家具搬进去,开始在那里的生活,空间才开始成为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地方认同感的显现,最简单的情形就是当一个人身处其中,发育记忆,以至说出“我是苏州人”并开始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我们是想通过这个展览来挖掘苏州的地方知识,型塑这种地方感。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展览现场,林意欣:《漂流者》
ARTDBL:对于苏州的移民而言,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地方的通道是什么?
欧宁:展览中林意欣的作品《漂流者》,便是讲述移民故事的。移民对地方感的获得,往往是比常住居民要困难得多的,而移民跟地方的关系最能折射出一个地方怎么样从空间转向地方的过程。苏州是除了深圳以外的第二大移民城市,我们去到苏州葑门桥采访那些来自安徽和河南信阳的移民,有的人大概大概1989年1990年就来了,虽说仍旧在给人装修、做木匠,但就是不想回老家了,他们会说待了20多年,习惯了,日久他乡便成了故乡。
“地方营造”(Placemaking)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力成为本地人,去到本地人才知道的地方,学习本地才通行的地方知识,不过这并不代表人一定要在这里出生成长。为什么要欢迎外来者,因为极端化的地方感会带来地方的过度骄傲与排外。我经常喜欢引用美国一个可持续农业专家韦斯·杰克逊(Wes Jackson)的一句话,他说,通过欢迎外来者成为本地人,其实是打造了一种开放的本地性,由此才会产生社群,进入社群以后,人对土地的感情、对自己所生活的地理定位所产生的感情,对共同生活的态度都会发生改变。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田野录音现场
ARTDBL:当地方丰满了个人的经验跟感情之后,移民对地方感的塑造有着什么样的贡献?
欧宁:地方营造要欢迎外来者,欢迎移民,创造一种开放的地方性。移民参与了这个地方之后,自然会对地方产生贡献。这些来自外省的短工包揽了家庭装修这些工作,对苏州来讲很重要的,包括那些在大城市里做保姆的人,都解决了本地人日常生活里面很多细碎的问题,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和居住地,他们也为这个城市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服务。所以一个地方一定要有城中村,要有贫民窟,为这些从事低端劳动的人提供一个去处,拆除城中村,看似解决了城市外观的问题,其实是切掉了城市身体之中一个必要的器官。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展览现场,张一丁:《石路南行》
ARTDBL:对于已经具备地方感的城市而言,地方仍然需要被营造吗?
欧宁:地方当然是需要营造的,现在已不像早年殖民者那样要去到荒野,创造一个新的地方。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地方也在随着时代氛围的变迁发生改变,即便一个地方已经存在,它也可能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
现在很多房地产商都在讲社群这个概念,我发现我讲的社群和他们口中的社群是不一样的,城市中的社群更多是一种兴趣共同体,缺乏更深层的、乃至经济层面的联系。现在大家都住小区了,邻里之间没什么交流,没有交流就不可能形成社群,建筑形态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居住和社会交往的模式。所以在已经形成的地方中,它的地方感、社群的凝聚力、地方人的认同感可能会受到不同时代氛围的影响而波动,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艺术的介入,通过动员地方人的互动、参与来增强他们的地方感和归属感。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田野录音现场
ARTDBL:作为地方外部的人,我们能否借助一些既定的描述去想象地方呢?比如说贾樟柯式的山西,比如今年很火的五条人的海丰,又比如已经非常烂俗的“东方威尼斯”苏州?
欧宁:五条人的走红,大家对于乡土内容的兴趣,说明生活在没有差异的所谓全球化城市里,人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精神需求。对家乡的追寻,其实在我们当代社会里一直存在,人们并没有忘掉自己的家乡,只不过在忙碌的大城市生活里边,没有时间去想,一到过年的时候对家乡的社会情绪表达就出来了。“东方威尼斯”这些名头,完全是城市营销的简单化的刻板套路,然而地方感绝对来自民间,它是由极其丰富和细腻的细节支撑起来的,只存在于个人的身体记忆和经历之中,是粗线条的名目所难以描绘的。
我在编《天南》的时候做过一个方言文学的专题,发了五条人和钟永丰客家话的歌词,我对地方的兴趣大概是从2010年开始的,而且这种兴趣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新冠”之后,全球化的进程停滞了,城市密集的交通、居住方式反而成了传播疾病的温床,大家开始更加想要回到地方,回到分散的农村居住之中。研究地方其实对全球治理是有参考意义的,当跨国流动不再作为一个现代化指标的时候,却能从远离中心的地理布局、分散式的居住、较少的人口流动中,找到控制病毒传播的机会,这正好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进行一个反思吧。疫情是危机,也是机会嘛,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当下的发展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倡导地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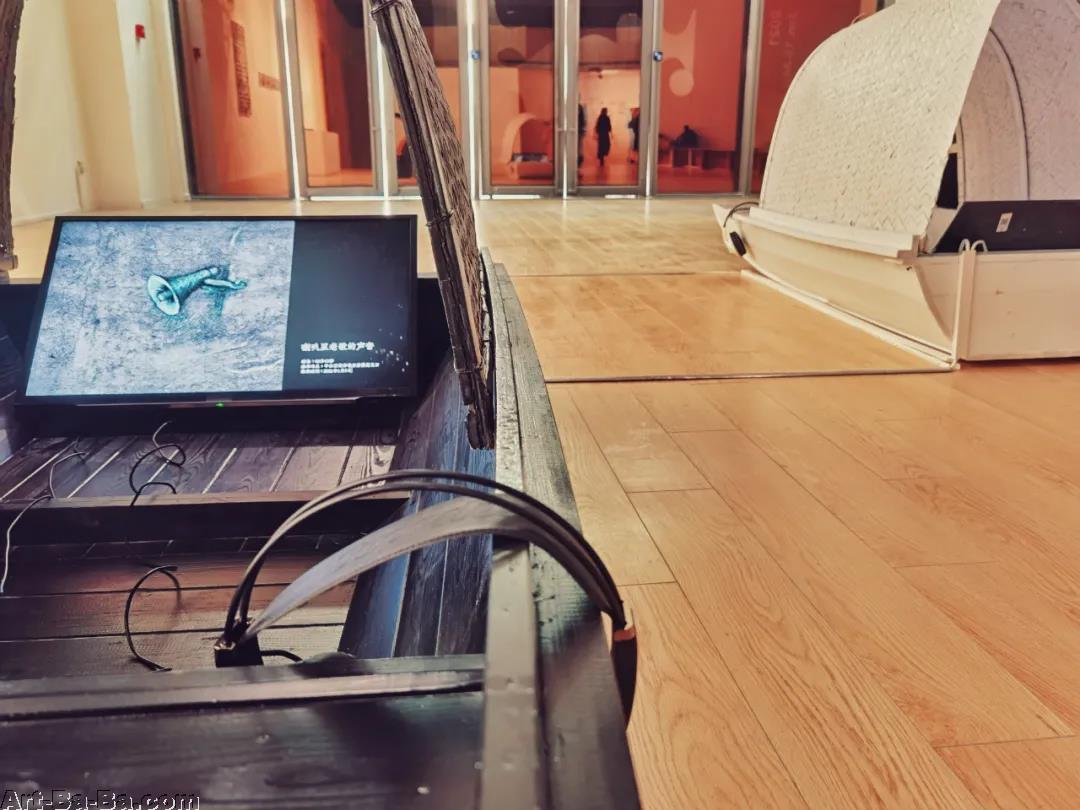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展览现场,常兰×刘呗宁×蔡宇潇,《卧游去苏州》,图片摄影:Lu Beini
ARTDBL:我在阅读展览相关信息,会发现你在讨论地方之前,往往会再后退一步,刨除社会历史的因素,回到一个“空间”的状态考虑其自然层面的因素。包括你过往相关的文章中,也提及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黄仁宇提出15英寸等雨线,那么,我们要如何处理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关系?
欧宁:从空间上来讲,我们生活的地球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空间和人类居住的空间,人在地球上,是在不断地攫取自然,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地方的产生,比如早期的殖民者到达地方以后,通过命名的行动,往空间当中添加社会、文化这样来自“人”的信息。即便是根本没有人生活的“绝对空间”,一旦有了人类拓展的步伐,空间就有了成为地方的可能,而自然也会反过来影响人类活动。
自然和人类之间是持久的互动关系,人可能是在经营地方,但实际上总离不开自然的回应。我之所以提到15英寸等雨线和竺可桢的历史气候研究,其实是从通过某些气候的标志,来看自然是怎么影响人类历史的。竺可桢是科学家,他对5000年历史气候的研究并不涉及人类政治社会的因素,但从他画的那张气候变化曲线图里边,可以明显看到气候的变化与中国历史的兴衰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唐朝的气温明显高于现代平均气温线,那是一个盛世,但是在两宋之交确实一个低温点,到了明亡清兴的时候,又是一个低温点。这之间一定有种规律,因为极端气候会影响农业歉收,饥荒出现后,北方的游牧民族便跨过长城入侵中原,中原的农民也可能揭竿而起,产生的冲突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展览现场,张大静 x 周沛勇 x 方奋筹:《曲终人散》,图片摄影:张大静
ARTDBL:从视觉的层面而言,摄影技术的出现和普及,或许改变了我们传统绘画中散点透视的表达,那么回到听觉上,技术的更迭是否也会影响我们对声音的感知?
欧宁:从聆听经验上来讲,声音的传递和感知主要就是靠耳朵,没有什么过高的技术。技术对声音的影响大概只在于一些发烧友会追求高保真的音质,这导致了一种选择性的聆听,低保真的声音无法“进入”他们的耳朵,噪音和日常生活的声音就这么被忽略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以视觉为中心的社会,我们太依赖视觉了,依赖双眼来抓取各种文化信息,双耳虽然在工作,却习惯性忽略了双耳接触到的信息。聆听的经验,没有所谓的民族性,更多是一种选择性聆听习惯的变化,只是当你把声音与地方联系在一起的话,它就有了地理特点。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展览现场,金佐宁:《归》,图片摄影:黄紫枫
ARTDBL:我在展览中体验到声音的存在并不“纯粹”,文字、图像、装置等不同的媒介信息都附着在声音之上,这不像是一般视觉性的展览中,观众和作品一直是一个对望的关系,反倒是形成了一个声场,似乎有了更加综合性的体验。
欧宁:开始这个项目,我们便期望展览能以一种“关闭视觉,打开听觉”的方式呈现。尽管我们反对视觉中心,但并非全盘否定视觉,而是强调希望能让听觉和视觉能得到同时的发展,提升听觉的被使用程度。展览最终的呈现还是免不了许多视觉层面的内容,借助一些实体物件,这当然和展览、美术馆以视觉为基础的制度有关,不过我们试图把声音和地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能以声音这单一媒体去表达地方的题目,让展厅成为除了声音什么都看不到的样子。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声音的展览中,艺术家丁敏却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在他的一些作品中,是用没有声音的视觉产出来表达声音,《FM》这个作品是把电台调频的数字画成画;另一个关于拆迁的作品,则把拆迁的名单排列为有节奏的乐谱一般,我感觉在拆迁这么激烈的主题上,他很好地做到了视觉和听觉的平衡。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展览现场,序厅
ARTDBL:对于声音的捕捉和记录而言,文字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日常经常会使用不同的拟声词,但在生活经验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当下,这些长久相传的语汇还能否发挥过往的表达作用?
欧宁:文字表达声音有着很大的可能性,但用拟声词来表达声音是一个最笨的方法。使用文字表达的基础是在于与读者共享的听觉经验,我在序厅里辑录了《吴歈百绝》和《清嘉录》中所有和声音有关的片段,便需要观众在读的时候调用以前的听觉经验形成联想。录音当然是最直接的体验,古时候没有录音机,只能用文字去记录和描述,声音的场景却依然活灵活现,根本不需要用到拟声词。在汉语言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从古汉语中继承了很多非常棒的表达,简练、准确,甚至因为语言的精炼,为读者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是现在直白的网络语言所无法比拟的。
这次展览文本工作量非常大,我从1月4号到苏州,基本十几天都在美术馆和酒店两点一线之间工作,要处理大量的文本,进行大量的文本和展签写作。这是一个声音艺术的展览,所以除了一般展签上的作品信息介绍,作品中用到的每个音轨,我们都以列表的形式给出了很详细的信息,像刘潇的作品有365个音轨,我们在展览中就逐一呈现365条信息,具体到哪录的,是哪一天录的,几点录的,甚至是具体到用到的设备都有对应的描述。
诚然,这些展签是文献性的,不列出音轨信息的话,大家看展览都还是在视觉的习惯里,一个长的录像观众都不会看完,何况声音?把音轨的信息列出来,让观众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声音的内容在里面,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试图提醒一下观众,改变一下观展的习惯,通过具体信息的罗列,让他们知道其实这个作品里边有这么多声音信息,这是一个提醒,也是展览文献的精确性所在。
*更多详细内容,可参考阅读由欧宁撰写的文章《风土与声音:苏州的历史音景》,网址:https://www.douban.com/note/793402431/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田野录音现场
ARTDBL:那么,对你而言,在录音机已经能够清晰地记录下声音原初片段的前提下,我们借助其它媒介的必要性是什么?
欧宁:我一直都带着录音机,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它就像写作的工具一样,是记录声音非常重要的工具。但它并不意味着我要排斥其它的工具,录音机只不过是通过录音,让我能够重新捡起那些过去忽略的声音资源,提供一种不一样的媒介方式去做研究,去记录日常的生活。
所以在使用声音这个媒介的时候,我并不排斥其它的工具,还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情况,甚至更进一步,当创作者、编者面对一个声音和文字材料,要进行第二层转译创作、重新编码工作的时候,不同的文献或是材料本身就带来了新的解读入口吧。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李依蔓:《存档﹒苏州》展览现场,图片摄影:张大静
ARTDBL:说到在展览中组织研究成果的问题,你怎么样看待文献展?
欧宁:文献的方法论在中国已经有了非常长远的历史,有着一整套非常专业的方法论,其中无差别收集的“全宗原则”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呈现文献的展览非常重要,在我们当下艺术生态里边,观众往往关注的是工作结果,但并不关心创作的过程——艺术家做了什么调研,看了什么书,画了多少张草图,这些都不是展览呈现的重点,仿佛最终挂在墙上的便成了作品的终点,而过程是需要通过文献来展示和表现的。所谓的文献,是在为将来提供研究的材料,对一张画的研究,假如完善收集了艺术家的推理、草稿、日记的话,才会有更多后续理解的依据。
这几年,我对文字作为一种媒介,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和热情。我们使用展览来应对“苏州的地理音景”这样一个题目的做法,更大程度上是由美术馆机制所决定的,抛开制度,我认为文字是更有效的表达,花那么多精力摘下历史文献中和声音有关的描述贴在墙上,传递的信息可能还不够看我一篇文章有效,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同时,展览的研究应该要是使用不一样的表达媒介,我们在招募参与者的时候,要求每个人在结束展览和工作坊以后都要写一篇东西,集合成为一本书。对于这本书的编辑,我希望它首先是有内容的,其次是可以进入图书市场的一本文集。出书的必要性在于,研究类的内容为整个项目提供了一个知识图景,书的内容密切关联项目的题目,但它可能并不会与展览有过于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仍在展厅内保留了大量的文字。
ARTDBL:为什么你如此看重图书进入市场?
欧宁:以前一到展览,好像做个catalogue就成了标配,厚得要死,书中充斥着大量的图片,没什么可读性,做完了以后印刷量也少,只能当作是一个文献留存,实际辐射的读者范围非常小。我们强调让这本书进入图书市场,就是想要更多的人去阅读,围绕着“地方音景”这个题目,可论述的东西非常多,而这些论述也有着相应的读者需求。
为什么要出书?书籍这个形式,在进入了市场之后,就成了一个长效的东西,图书馆会收录,会在市场上流通,档案馆会收藏,甚至再过5年、10年,你还在可以孔夫子旧书网、在某处的书摊可以买到它。关键是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组稿做一本好书,形成的文献,便是为后人提供研究的材料。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欧宁导览现场,图片摄影:张大静
ARTDBL:联想到过去曾经读过你在深圳做的一些有关音乐、电影的zine,在拍《三元里》时做的一本正方形小书,还有在策划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时做的系列书籍,或许在你对地方这个议题产生明确的兴趣之前,就已经在用文字、书籍去描述一个地方的实践上有了相当多的尝试。
欧宁:这大概是跟我在1980年代的文学经验有关吧,我整个人生经历里,第一个身份是中学时候就开始的写作者身份。1980年代的社会氛围,对我人生影响太大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文字就变成了我基本的媒介,因为它最简单,可能性也最大。只要条件许可,我都会做书,从在深圳做音乐会的时候出的zines,到拍纪录片做《三元里》的书,再到每个展览相关的各种书,文字写作、编辑、出版物,几乎贯穿了我后来所有的工作。
对我来说,做档案并不是为了积累我个人身后的名声,而是在archiving,在档案(archive)后面加上ing,让文献成为一个行动。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很依赖文献,那当我在创作或者做其他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不给别人也留下文献?体会过找文献过程中的那种痛苦,便深感假如自身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研究对象的话,应该具备这么一种积累文献的自觉。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田野录音现场
ARTDBL:文献作为行动,似乎也一直贯穿在历史的书写中,包括我们谈论到乾嘉考据学,回溯考据行动者意志的主动性,对我们理解历史也提供了另外的样本。
欧宁:考据学是在追问历史的真实,但是考据的过程又是众声喧哗的。什么是伪经,什么是真正的原作?争论非常大,不可能有一个唯一的标准,这也是考据学里边最意思的地方,实际上所有留下来的历史文本都可以有不同的读解方式,所有对文献的解读都参与了历史的重构,去建立自己的历史叙事,为历史增加多一个版本。
文献的存在必然带着一定的选择性在里面的,它的倾向性和目的性是很强的。文献是历史叙事的材料,是带有强烈政治性的,同样的文献,可以剪裁出截然不同版本的历史叙事,有官方历史的版本,我们老百姓同样可以用文献去发展出不一样的历史叙事,这里边有话语权的争夺,有身份认同的依据。
我们今天看所有的史学作品都是主观的,历史的真实,只有那个身处其中的人才会知道。但是这种主观又非常有意思,它提供了多元化的理念,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很大的空间。至于文献在未来的剪裁和解读,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主体去完成。这次我们在网络征集了很多苏州人提供的文献,基本上一种来自民间的角度,对文献的追溯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那样,在一个清心寡欲的档案馆里面守着故纸堆,文献是介入现实的行动,我们也需要通过文献行动,发出多元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