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Review Asia 文:Rahel Aima
在印度导演摩楚(Mochu)的影像世界中,控制论的假体与艺术史、卡通物理学与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中的迷幻遗产相融合。这位印度艺术家的产出横跨多种媒介,但人们通常将摩楚视作一位用电影摄影机写作的作者。或以散文、或以讲演随附,如水的文字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电影中溢出。如同前苏联电影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ertov),摩楚的视频作品避开了直截了当的平铺直叙,而转向一种由素片堆积而成的数据库电影以及对特效的自由使用。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科技进步将二人分离,这两位电影作者却都表露过对观察模式与超人主义乌托邦的兴趣。维尔托夫将相机镜头理解为第二只眼,而在摩楚的手中,镜头变得愈发时髦、诡谲,它进入超越历史的浩瀚星辰,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第三只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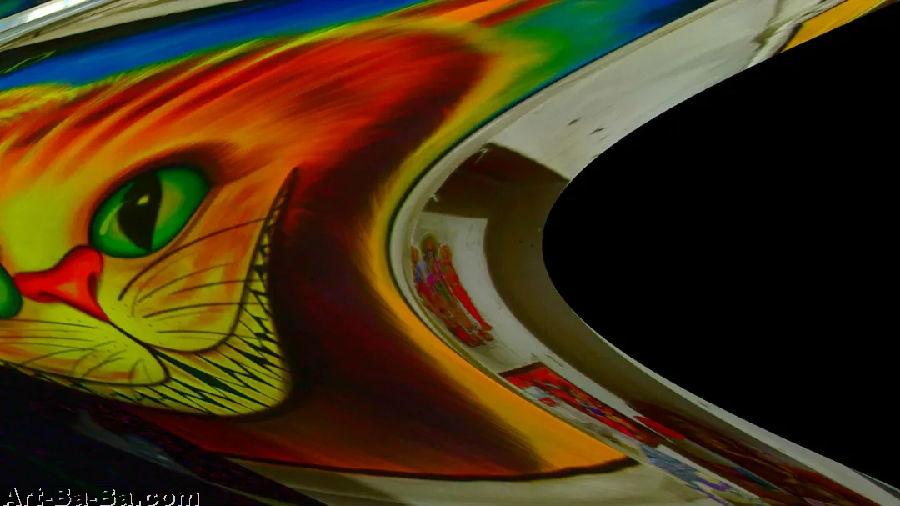
摩楚出生于喀拉拉邦,在印度长大,现工作于德里与伊斯坦布尔。作为一位非西方艺术家,他嗅到了身份认同陷阱的危险,从而使用他的童年外号取代他的真实姓名,因为它带来了一种不透明性——在邮件中摩楚如此解释:“我喜欢这个名字所提供的不确定性(性别、物种、人种、集体/个人),什么都不清楚。”本世纪初,摩楚在德里国立设计学院学习动画与传播设计,此时正是胶片式微、整个电影工业开始向非线性数码剪辑转向之际。通过排除法,摩楚最终选择了实验电影。“我对广告业不感兴趣”,他在Skype里解释——尽管他从未接受过正式的艺术教育。随后,在Sarai学院(由 Raqs 媒体小组在德里设立,现已关闭)和Ashkal Alwan’s Homeworks项目(位于贝鲁特)的工作则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批评理论【克丽丝·克劳斯(Chris Kraus)、Kodwo Eshun、雷萨•内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Jalal Toufic】与科技的兴趣。

摩楚 导演,《遥远神明的酷炫记忆》,2017,数字视频,14分48秒
不过,艺术伴随了摩楚的成长: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他们全家则在金奈(Chennai)外围的柯拉曼达尔艺术家村(Cholamandal Artists’ Village)待过一段时间。作为印度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地,这里诞生了马德拉斯艺术运动(Madras Movement of Art)。与著名的印度现代主义先锋——孟买进步主义(Bombay Progressives)——不同,这一运动拒斥欧洲的大师叙事而偏好本地艺术运动与本土工艺形式。几十年后,摩楚才会制作《嘉年华商店里的一次聚会》这样的关于柯拉曼达尔艺术家的作品。电影围绕着神秘的外围艺术家K.Ramanujam在1973 年的离奇失踪展开——电影中的解释是,他可能变成了一只黑狗或是一顶帽子。这部电影同时也是对此地的描述。它回避了纪录片的俗套,采用一种探索性和对话性的语调,流连于档案图像、艺术作品与Ramanujam的艺术家同僚之间。这些人已是耄耋之年,而他们的追忆被完整地保留在电影中。
在摩楚的实践中,有一种观念贯穿始终:艺术史从地形拓扑学展开。早期的短片作品《一次未来航行的图画表(谁相信镜头呢?)》(Painted Diagram of a Future Voyage [Who Believes the Lens?],2013)假定了一种可能的印度景观,后者从殖民画家托马斯(Thomas)与威廉·丹尼尔(William Daniells)的腐蚀凹版画中衍生而来。这里,建筑被选中、扭曲,好像是从银河系里绕了一个时空变换的圈。形变被重构为帝国的扭曲凝视,从而制造了一种科幻电影般的异星景观,和现实脱节得仿佛殖民画家们的东方幻想。另一部短片《水星》(Mercury, 2016)同样通过剪裁粘贴、业余动画的方法介入并改造了艺术史景观:莫卧儿王室画家乌思达·万舍(Ustad Mansur)的小动植物画。

摩楚 导演,《嘉年华商店中的一次聚会》,2015,数字视频,35分
摩楚早期受到印度实验电影传统、阿密特·杜塔(Amit Dutta)和卡马尔·斯瓦鲁普(Kamal Swaroop)的影响。摩楚认为这两人都扩充了他对作为学生所能具备的可能性的理解。至于维尔托夫,摩楚认为自己从这位前苏联导演的同辈们那里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包括乔治·梅里埃(Georges Méliès)、塞冈多·德·乔蒙(Segundo de Chomón)、其后的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拼贴电影,也包括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与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大卫·布莱尔(D**id Blair)和戈达尔的一些散文电影。这些都拓展了维尔托夫的传统,并“保持一种记录性,同时加入了很明显的特殊图像与效果。”摩楚也对科幻电影情有独钟,例如俄国艺术家斯特魯格斯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和波兰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ław Lem)的作品。摩楚在他们的这些抽象的东西中发现一种美,他注意到这一类型在“马克思主义书店的儿童区”里广泛可寻。“那是一种对事物本体论的困惑,”他说,“你不知道一个东西是一个物件还是一个人。我认为这种基础困惑在东欧语境下要比在美国或者法国语境下处理得更好。”这一本体论困惑也同样弥漫在摩楚的实践中——那个变成了黑狗或是帽子的艺术家Ramanujam 就是一个例子。

有趣的是,科技进步通常会与民族叙事紧密绑定在一起,以至于一个国家的科幻叙事不可避免折射出它的民族神秘学,哪怕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批判。举例来说,美国科幻叙事中的那种个人主义、技术乌托邦冲动的唯一作用,就是给太空探索活动重制了“昭昭天命” (Manifest Destiny)的观念。与此相反,摩楚却意识到了弥漫在苏维埃小说中的存在危机以及当时特定的文学手法——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回避铁幕时代后期对此种文字的限制与审查。考虑到印度当今对于个人与出版自由的前所未有的压迫状况——从切断广播媒体、监禁发布批评执政党故事的记者,到种姓制度下的性别暴力的集中爆发——是否更多印度艺术家会开始发现前苏联科幻作品的启示意义,这也令人好奇。
与此同时,摩楚对于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技术虚构作品(technofiction)持审慎态度。他解释道:“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在处理技术而不是科学:技术装置、技术哲学——不管它如何被误解——以及有关科技的意象。”他苦恼于几乎无法在印度找到本土的技术哲学,除了那些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机场书店买到的“上师土法通灵大全”垃圾。在这里,他提到了许煜近期关于中国的文章作为一种类比。某种程度上,摩楚本人的实践可以被理解为指出这种“本土的技术哲学”可能为何的过程。当人们投入巨大努力来要求科技巨头为它们滥用用户数据与对政治广告与错误信息的松懈管理负起责任时,“加州形态”(California Ideology)仿佛已越发暗淡,却仍在某些地方发光发热——在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科技城这样的 IT中心;在“印度世纪”的迷思里。摩楚近期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意图探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与他们对“黑暗启蒙”运动(Dark Enlightenment)的成功接受——此运动的非主流右翼策略旨在操控公众情绪。

这种转换当然有其两面性。“在印度,我们已经兜售通灵学说几个世纪了。”艺术家如是说。《遥远神明们的酷炫记忆》(Cool Memories of Remote Gods, 2017)是一次让人目眩神迷的夜行——你难以确定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通过对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仔细分析,电影追踪了嬉皮士运动对远古印度神秘主义的挪用与个人计算机发展之间的联系。摩楚在这里很小心地强调了灵性(spirituality)而非宗教(religion),也因此决定不在瓦腊纳西(Varanasi)拍摄,转而选择了对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都显得神圣且遥远的沙漠小城普什卡尔(Pushkar)。即便旧日海报、致幻用具和老嬉皮士们似乎已成定局的落魄都标志着这次运动的破产,经由精密设计合成的毒品却更像是一种个人技术加成——还是说反过来?——此作品由 2017 年沙迦双年展委任创作,并且在一座形同飞碟的建筑内部的昏暗房间里首次展出。我当时没有获得自己的灵性顿悟,不过这种状态特别完美 。
翻译/张瀚文
编校/任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