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陆兴华
陆兴华:当代艺术的2020生死劫
——让市场还是生命先胜出?
一、死
Dr.李之死,掀开了这个多事的2020年的第一重面纱。那天晚上,他的似真似假的死讯的到来,到底向我们打开了什么?

记得当时本人在朋友圈贴了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葬礼进行曲》来表达悲痛。但那是怎样的一种悲痛?还是瓦格纳所能表达?这死和我的悲痛里,到底带了哪种例外性,值得我格外注目呢?你我分别在他的死和我们的悲痛上押了什么赌注?哪个押对了呢?都年底了,我们好结算了吧?
作家方方也轻浮地来押她的赌注了,害得我与几个多年好友决裂。她的这一次的象征自杀,证明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公知界在后真相时代的艺术界、学术界已经有多么地流寇化。证明:你我不光并不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我们在当前也根本形成不了一个时代,而是生活在大流散和真正的大疫区之中,都各自仓皇地奔突着,急急如最后落在被抽干的池塘底里的鱼和虾,只好短兵相接了。疫情是早就发生了,这一次只是一个回访式提醒。这个思想界,这个学术界,这个艺术界,这个文学界,你看,在疫情中,终于底朝天了,错乱的表面之下,真的就只有一堆像方方那样的枯枝。
我们甚至对防疫装置上瘾了。我们这个有病的社会的抗生素到底在哪里啊?
--Gerald Moore
同时,Dr.李的死也揭开了我自己的那种满是自欺的活的真相。是啊,不先对自己设下一层层的欺骗,让自己上钩,还怎么活在这个流沙般的当代之中啊?掩耳盗铃,此地无银三百两,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但转身还是继续守株待兔。忧郁是因为我已知道该做什么,但仍什么也没做,才造成。出手,后果将不可收拾,不出手,自己就先忧郁,然后抑郁,最后就走向疯狂。

这是今年8月去世的斯蒂格勒老师对身处灾难时代的我们的拖延症的诊断,他在《扰乱》里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当前活着的三代人都将是孤儿!第一次读到他这么说,我的脑子被震麻了。知道了必然的后果和未来,但仍什么都没做,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准备好遭受来自我们自己身上的疯狂,这是一种由熵带来的疯狂。勇敢地出手,改变原来的概率,成为生物圈中的技术人,才能终止那一恶性循环。至少,我们手握着死这一最后武器,我仿佛听出了斯蒂格勒的这样一种教导。
--Lynn Margulis
没过完夏天就抽身离开的,还有我的几个好友和同学。一直独立照料我的派金森氏症同学、成了我的好友的那位优秀丈夫,自己也因血液病而入院。人生第一次,在医院,与他说话时,我一边对他说话一边一大颗一大颗地掉泪。
那一刻,就感到沉入了我的2020年的谷底。感到老对手这次是铁了心要清算我了,远不只是吃掉我几个子割肉一下就够。就感到自己的整个阵地都在抽动而摇晃。这个城是没法守了……。
之后又读到翠西·艾敏(Tracey Emin)在癌症手术后说:“我得的是已辐射全身的鳞状细胞癌,有透袭性,医生们也无法直接切除肿瘤”。三周之内,“他们切除了我的膀胱、尿道、淋巴结,完整地切掉了子宫,只给我留了半个阴道——那就是我的夏天。”春天被诊断,夏天做手术。现在,她每天的活的状态,据她在Instagram账户上分享,那是在3月26日,是要依赖运气了:“只要那一种压倒性的恐惧感和黑暗没有满格到来,那么,我在那一天就会很开心,就会庆祝自己的孤独。不过,也是这种恐惧和黑暗,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想活下去。”

Tracey Emin
在近期的《Artnet》采访中,她表示已决定彻底改变生活,抛下长居的伦敦,卖掉迈阿密的房子,搬到海边的马尔盖特,过一种极简的生活,停止喝酒和社交一段时间,优先考虑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找一个 “纯净 ”的地方,用于思考和创作,尽管她还不能做最喜欢的事情:绘画。但她一直在为自己的身体拍照,开启了一个有关“存在主义”的项目。她的处境特别让我联想到自己在这个大疫区里的劫后余生的余下情节。

--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
在搞不清我此时是在疫区之内还是之外的时段里,生就是一种被死时刻围攻着而成长起来的局面。生,是像被清兵围攻的袁崇焕的自立更生的兵团的粮区那样的一种暂时的繁荣。赫斯特的《生对于死的冷漠或死对于生的冷漠》里的鲨鱼的将要腐烂还未腐烂的肉的状态,代表了生命最接近死亡区时的那种自决的样貌,那是靠着一种根子里的顽固在坚持,而露出了一点生命的鲜亮。福柯很喜欢引用19世纪的Bichat医生的那句话:生命是被死亡时时包围的那一块活区,是顶住死的进攻而保存下来的那一点点活的东西。每天早上看在昨天换下来的衣服的里子上,我们会发现上面粘着很多死亡的进攻的痕迹:我们的死皮。而生命也是要主动迎着死亡来找到它自己的挣扎的边界和极限的,像《白鲸》里的阿哈伯船长,不去明确地与死亡扛上,就发现没法往下活。
而艺术家自诩是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他仿佛已先有了对死的经验。他们回来,做展,想告诉我们活着是什么。而他们创伤的艺术作品,就是供我们死时抱着离开的,有钱人是抱着玉走,穷人有时就抱着一把破雨伞出发了。
艺术家是围着死来做文章的人。巴塔耶在“艺术是对残酷的练习”中说:人身上有一头动物,所以能神圣,会做艺(魔法)术。做艺术是:既然不能在欢畅中死去,那至少也要在最幸福的那一刻与死打成平手。这是什么意思呢?做艺术,成为艺术家,是在与死亡玩互猎游戏。谁将在最后成为猎人呢?在疫情中,不也正有做艺术家的机会了?
做艺术是想要秀艺术家自己的能够无限地接近于死的那种经验?沃霍尔也向我们示范:去正面遭遇那种亲密的恐怖:被开*,被捅掉半个右胸,后半生被这个伤口限定。做艺术展览,就是主动摆出死的陷阱,害我们自己踏进去,再从中挣扎出来。而平时,我们总是用各种假死,来应付这种真正的挑战。2020年的病毒是来对我们以往的这种种假死作了清算。
而就算活到九十岁以上,难道你不也就是在被动等待某个灾难的突然到来,最后毫无准备地被凶暴地终结,还一路恐慌着,最后还是吃了一记当头闷棍,才一命呜呼?斯蒂格勒选择了主动。他要用这种主动的死为他的写的立场和语气撑腰。
夏天的时候,艺术家肖雄扒在了自己的工作台上,最后以一座雕塑的姿态向我们告别。秋天时,艺术家黄小鹏在柏林突然离去。说实在的,我羡慕他们的这种死。悼念过他们后,我甚至也生出一丝庆幸:艺术界毕竟是一个能让我们不做安排就能够好好死在其中的“界”,不用付按揭,不用订购墓地,也没有来争抢位置,一人总有一人的坑。在艺术界内的悼念中,死者被壮严地安排进了一种文学式的历史(布朗肖)之中,比大数据库和那个莫须有的艺术史,是要靠谱很多了。
在2020年,故人们还教给我关于做艺术的另一条理由:既然最后总能够好好地死在这个艺术界之中,如此没有后顾之忧,劳保和退休金也就是不事儿,那么,此时就不妨活得猛一点儿。活着而不猛,那就要被病毒笑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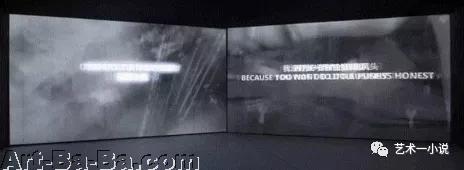
黄小鹏作品现场

肖雄
二、回光
今年的横滨三年展艺术总监由印度的Raqs Media Collective担任。非常不祥地,展览主题就是“Afterglow– 抓住光的碎片”。Afterglow也就是回光返照啊。这题目已为这个2020年定了调!
这个小组的Jeebesh是学天体物理的,所以会取这么个名字:我们总活在回光返照之中,想纠着它不放,来活下去。“Afterglow”(回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觉要接触到的来自宇宙大爆炸瞬间发出的那些光,早于太阳!它能扶慰当代人类的的“破坏/毒性”和“恢复/治愈”的药性命运?这次的三年展在疫情前就要带领我们讨论如何实现与负面事物共存的生活方式。
哪想到,正这样说着时,更不祥的东西已经到来。一种可怕的前知前觉。
疫情出现后,组委会仍然发布了展览的几个关键词──“独学”、“发光”、“友情”、“关爱”、“毒性”,要大家用它们来共思考。疫情发生但展览还未开始时,三年展联系人木村绘理子这样重述展览主题,“新冠病毒在全球的传播后,对信息的不信任和过度信任、对不确定的未来和他人的恐惧的相信,似乎比病毒的毒性更强。”“眼前的危机过去后,可怕的记忆可能会沉淀在人们心中和社会的各处。为了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存,就应不光认识到人类社会,也应认识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面向未来的不确定,就更需要当代艺术。因为,做艺术,是做着来知道,康德因此说,艺术不能教,因为艺术是我们对自己动用控制论的过程,一开始是系统先占,之后我们必须逆转,来先占(be preemptive)。许煜提醒我们,康德努力将艺术与自然、技术与科学分开。他顺着克兰纳尔说,艺术是那些哪怕你对它们具备了充分的相关知识,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有做它的技巧的事儿。技术出问题的地方,才有科学亮相的机会(许煜,《递归与偶然》,第201页)。
许煜还说,与技术、与控制论共处时,我们必须知道,艺术是给我们带来问题,更好地提出问题,而不是来直接解决问题的。技术引起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到场,使我们必须返身自我激活,施拖刀计,杀回马*,才能从系统的逻辑里分枝。许煜强调,斯蒂格勒告诉我们的是,偶然性更接近艺术实践。对斯蒂格勒而言,艺术家的任务是要调节自己个体化过程,以建构具有一贯性的规划:使意外成为必然,预料到意外之物也是对我起关键作用的。这种个体化是:(1)成为艺术家,(2)在创作中遭遇意外之物。许煜认为,艺术家通过她的作品敞开了她自己的一段短暂的超个体化过程,也就是展示她自己的一段心理-集体个体化,给观众看,鼓励他们也与自己一样走向技术、心智、心理、社会性的个体化。如果艺术作品是感性技术的成果,如果这种感性技术能把认识着的灵魂引入社会的循环,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艺术家是在促进观众自已的个体化(同上,第259-62页)。
三、线上展览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疫情下,本来,线上展览应该来大显身手了,结果,我们看到,连艺博会都对之三心二意。
会不会是因为,线上展览和线上收藏的方式将是对于线下收藏和买卖的重大打击?
许多种媒介的艺术作品实际上已很不适合线下收藏了,但是,一到线上,各方就都觉得自己将要被架空。
到这一步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线上展览的如何到场,到今年,已是关于占有权和冠名权之争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突现出来了:到线上还能占有一个艺术作品吗?
既然吃不定,于是,艺术的线上展览大多演变成线上讨论。“Trigger 触发”了很进步的线上行动。它原来是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的学生发起的独立艺术平台,如今已由多个艺术院校的学生来共同运营。由于疫情限制了人员聚集,Trigger 将原本在线下校园内举行的“critique马拉松”活动搬到了zoom上,以公开投稿的形式召集身处各地的年轻艺术家,通过软件内“共享屏幕”的功能,只向观众展示作品的照片和影像。每个月Trigger 的某一个周末会在这两天内分别举办一场在线马拉松,每场达六个小时。但之后,遍地的zoom会议或腾讯会议淹没了这种创举。
Vanguard画廊推出了线上单元:务虚会。“务虚会”自成一章,以在线等“非实体”形式为载体,只呈现艺术家架设的观念构想和形式创造。
这个全球当代艺术责任有限公司,今年是终于有限了一回。
--本文作者
艺术走向数字平台的步伐实在有点慢,到今年,我们看到,几乎是不走了,而这恰恰是最应该走的时刻。线上展表面是欣赏艺术的一种新方式,实质是要建立网上的艺术作品新“本体”,使艺术作品能在网上被占有,但这违背网下的普遍的艺术作品交易准则。
如何才能在网上无边界地分享艺术作品?这对业界而言至今仍是一个只在嘴上应付的问题。
这需要我们探索出一条艺术作品占有的新体制:铺设网上冠名权。
建立网上冠名权体制,藏家才会委托线上展览机构来展出自己的藏品,才会有真实的网上交易。网上机构才能为线下收藏家托管作品。实际上,网上交易的过手登记是更可靠的,而收藏作品的增值,就是要靠这种过手资料登记的,这方面,今天的画廊和拍卖行远没有网上数据库做得好。
叫大画廊来做线上展览也是遇到了狼外婆了:巴塞尔艺术展“城艺之旅”展区将艺术带入瑞士巴塞尔的各个角落。策展人Samuel Leuenberger将透过Zoom带大家参观网上展厅,分享他最中意的作品。许多参展艺廊在这个6月都为观众精心准备了一个线上节目,从艺术家访谈、线上表演、到艺廊收藏探索,又或是艺术家的工作室访谈等。当全球依旧被跨地域性所受限的时刻,数字平台拉近了我们与艺术的距离。坐下边享受零食的乐趣,边感受艺术的魔力。

大画廊也只会这样来做线上买卖:疫情期间,《杰作》作为卓纳线上展厅展出了经典的单幅作品,仅凭邀请函对画廊现有的藏家独家开放。这符合二级市场一贯的交易规则,“《杰作》是连接传统私洽与线上空间的桥梁。一方面是通过有选择地将大师作品呈现给可以信任的熟客来维持私洽的谨慎,另一方面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将丰富的作品内涵、重要性与出处呈现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卓纳线上销售总监埃琳娜·索博列娃(Elena Soboleva)说。开发自有线上平台的大画廊们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现有的藏家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卓纳的的《工作室》将从艺术家工作室中新出的作品直接呈现在买家面前,取消了实体空间的限制,无论是在特殊时期还是当艺术世界恢复常态,这无疑可以促进画廊在一级市场的交易速度。
四、那么,展览有好坏吗?
由展览提出而被观众接过去而成为社会议题的那些“问题”,是由当前的社会政治语境和艺术圈、媒体圈的共同感受决定的。是借了这个展览提出来,不是由这个展览的“质量”来决定的?展览在生产这样一个问题、思想和眼光吗?
如何称一个艺术展览的斤量?
我的回答反而是:称不出的,所以不要去称,所以也不要用任何标准去称。因为,艺术是在艺术家自己身上被结算的。
下半年,周婉京的一篇《“好上加好”的艺术圈,为何成为平庸的制造机?》中对于一些展览的打分,对于当前当代艺术这架制造平庸的机器的诊断,搞得大家都懵了,不敢正面回应。本人认为,这是大家对于什么是展览这一点的认识不够深。

本人认为,艺术展览是不能比哪个好哪个不好的。这违反了展览伦理。展览是一个策展人做的个人祭式。正如你不能够说穷人的祭桌不如富人的好,你也不能也没必要说这个策展人做的很差,那个做得就很好;不能说这一个展览比那一个展好,更不能说,我手里掌握着衡量一个艺术展览的标准,能来评判出什么样的展览才是合格,怎样了才是好的,这做不得,也没必要。尤其不应该让一个“我”跳进来做定夺。这不合理,也不应该。
通常,这种问题是如何来被回答的呢?
我亲眼见到年青人逼问过格罗伊斯上面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只要你自己认识的三个你感到是在艺术界混的人,无论是谁,无论他们自己的艺术水平怎么样,如果他们建议或鼓励你不妨一展,那你就尽管自信地去展好了。这又碍着谁,害着谁了呢?展就是祭啊。祭还要有区分及格和优秀的标准?我们的批评难道是在做奥运会体操比赛打分?
更重要者,祭,也是设下一个死亡圈套,一种向观众敞开的死亡游戏。艺术家最擅长玩这个。艺术家替观众做这个。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有权来当自己的别人的策展人,可以兼做,也可以独做。
从这个角度说,2020年的新冠疫情,我认为也是一个艺术展览,因为它是一次祭。
它是某个无名艺术家设置的一个生死圈套。不踏进去,生活不精彩,踏进去,出不出得来,那就要看你的机运了。而这就是艺术家天天在过的生活啊!!没有这种激烈,做艺术家做个什么劲呢!!但你看看自称是或自称不是的艺术家们中间,太多的人是像这个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系统,到处要去关闭,要到处去封闭,还封闭自己,关押自己。
这一统治我们的系统已经是一种反-艺术,似乎在不顾一切地粗暴地帮助生命,还给我们努力找疫苗,但它保护我们,使我们免疫,其实却是要将生命圈养到进一步的市场开发之中。
但是,做艺术,做展览,是要获得生命的尊严、体面和优雅。
五、为什么徐震会来做策展?
因为,也许是,自己做展自己来策展,就少些被莫名其妙地侮辱。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我混入了艺术家徐震的一些策展中,目睹了艺术圈内这个生对于死的无动于衷时的鲨鱼柜里的种种情况。倒不是我对其中的残酷和暴力和压榨吃惊,而是对于艺术机构管理方面的心不在焉感到了震惊。
我想我也终于看清楚了为什么徐震会用这么多的精力和资源来自己做一些策展。也许也是因他自己很有名,对展览要求太高,就不大愿意被组织混乱、计划乱变的展览玩弄,就想还不如麻烦一下自己去插手一下,好少失去一点尊严。
在过程中,我的确进一步观察到,在他和本人插手的展览中,应该是没有一个参展艺术家感到委屈的,尽管我们的资金也很紧张。我想,这是因为,艺术家们看到我们张罗者是自己就真的想要认真搞艺术的,他们于是感觉到自己是在与认真的同行一起做事,所以他们也就放心,或不与我们计较了,因为有些感到是与我们一起在做艺术,共同地让自己的身体发光,使生命发光。因为,我的理解,做艺术,就为了能够这样啊。这也是本人在2020年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做艺术家,做艺术这件事,就是这样地当场在艺术家的身体上可被结算的。做完了,感到无畏,感到放下,感到了下一次的上场前的必要的轻松,感到某种犀利。这就是做艺术的感觉了。

金莉萍朋友圈:金鹰美术馆远观
反观今天的艺术家参展经历,我观察到,由于机构的预算不到位、人员的不稳定、业主的过去逐利的倾向,名字吓人的美术馆和展览空间,也经常带艺术家一种“逗你玩”的感觉。市场成为洪水的地方,会这样,是不奇怪的!
所以,这是我在这个多事的2020年的当代艺术界内的长进,发现也是很多同道在这方面的长进:必须先让生命胜出,市场是福尔马林,因为它只作用于一时,之后是连绵的毒性。
让生命胜在,还是让市场胜出,在做和展艺术时,一次抖擞之后,即见分晓。做艺术展览,就是要先让生命胜出。
我看到,从202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圈中人懂这个道理了,尽管市场的大潮仍是衡量我们每一个人的乐观和悲观的尺子。
就这一点说,当代艺术在中国已进入深度时间层。
市场装置更完备了,但是艺术家的生命时间和生命形式也须得到更多亮相和反光的机会。
市场是像赫斯特的《生对于死的无动于衷或死对于生的无动于衷》中的福尔马林溶液。被浸泡在其中的,是艺术家的生命形式。艺术家做艺术,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壮大,就是在与这一福尔马林液对阵。在艺术的二级和一级市场完备化的过程中,在中国,在我们眼前,也一次次发生着这样的一次次的生对于死的无动于衷或死对于生的无动于衷。这使很多艺术悲观起来。但这是考验。
在这个像赫斯特的鲨鱼肉展示柜一样的当代艺术的场地上,我们要求的不是市场对艺术家的生命的慈善,而是要求它留出一点儿给艺术家的生命发光的机会,给它们一次以上的发光机会。它不留,不给,就需要我们的出击,去先让生命胜出,像在这一次的疫情中一样。而要知道,当代艺术是长期处于这一疫情中的,尽管买卖使我们得了自己的风光。但当代艺术本身是先让生命胜出的手段。
六、先让生命胜出
为什么在这篇文章里我老要说先让生命胜出、让我们的生命发光呢?因为,也是一直在当代艺术界混到2020年,本人才自己摸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做艺术、展艺术、说和写艺术,完事后,是得到一种全身通透的感觉,好像抖擞过一次了,将身上的死皮都甩掉了。是真能在身上感到某种自由的。,这时,仿佛我身上获得了某种新的自由。我想这也是推动我一次又一次地涉身另一个艺术项目的能量溢值。通过写而介入了艺术界,也许就是在接近这种将艺术当做对个人生命形式的雕刻的风度。我在自己的写之外,也在艺术界体会到了这种使自己的生命发光的感觉,转而也将它当作了我自己的工作的燃料。
正因此,更总体地,我看到了,在2020年,中国当代艺术界在走向进一步的成熟。主要表现在艺术家这一方面。我在接触中看到了2020年的当代艺术家们更深地感到做艺术是与自己的个人生命的垂直时间有关,是艺术个体在挖一口自己的深井,是要让它自己出水,不出来,跟别人急也没用。在他们的当前的工作的坐标系中,所谓1979年星星展,1985年的什么运动,1993年的什么开放或国际化,都听着是越来越然并卵了。这我认为是大好事。我们不需要这种傻逼的当代艺术史。疫情我们自己的工作目标更清晰。
“如果你有耐心,和勇气,来读我的这本书,你就会看到,里面的研究是根据不打折扣的理性的规则来进行的。…但你也会在书中发现这样一种肯定:时间中的性行为,就是空间中的虎。这是从能量经济的角度来作出比较的,而能量经济里是不会给诗性的幻想留出余地的,而是要求你在这样的层次上去思考:必须对抗着各种平常的算计地来促进各种力量之间的游戏,使各种力量之间的游戏符合我们的那些法则。总之,我们必须更一般、普遍地来看问题,提出:不是必然性,而是“奢侈”,才给活物质和人类带来了那些纠缠它们的根本问题。
--巴塔耶,《被诅咒的共享》
这种倾向我理解成是艺术家的普遍的个体成熟在加速,也就是说,更少用批判、抵抗、身份政治和生态关怀来包装自己,更正视自己在这个鲨鱼柜里的处境了。
艺术家的身体在2020年普遍看去越来越是一个自己充电的电池,而不是一个到处寻找电源的插线板了。这看得我很受安慰。要知道,我们就是生活在一种资本主义加社会主义的混合福尔马林液中,我们的生命自己不发光,身边就会蔓延出更大片的幽暗和死寂。做艺术,就是要跺跺脚,击退这一福尔马林液对我们的进一步的侵蚀。艺术家式的生命存在和主体斗争,应冲向生与死之间的直接对抗,不应该只是布阵和玩招术。

Lynn Margulis
Margulis,96。细菌如不能与其它细菌搭桥,就有同质体sex,它们的性别于是就互相传染。男性能把女性传给另外一个男性。在紫外线照射下,细菌爆炸,就变成无数个病毒。细菌每秒可转15000圈。它不停地交易着基因,造成了生命的复杂。你身上的基因只是暂时借你用一下的,不久就被细菌们回收。the bacterial biosphere,细菌打底的生物圈。Margulis,81。在过去的30亿年中,我们从未死过。死时,我们成为叙述的细菌和病毒,来为人类和其它物种跑腿。
金锋工作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