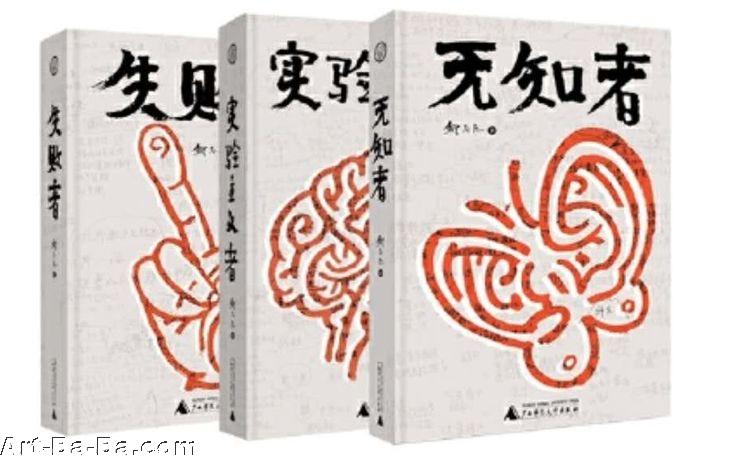来源:新京报
“自古以来的艺术家,就算不在大学里面教书,他也总是带徒弟带学生的,人们也是喊他老师的。对我来说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不同时是一个教师。因为他要去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主要是改变人。用作品去改变世界的时候是艺术家,用语言去改变世界的时候就是教师。”
整合丨杨司奇
4月18日下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世界·观与新京报文化云客厅联合主办的“别来无恙——邱志杰新书线上发布会”在北京虚苑美术馆举行,当代艺术家邱志杰的四本新书《剧透》《无知者》《失败者》《实验主义者》首次与读者见面,同时,哲学、历史、文学等不同领域学者陈嘉映、范迪安、范景中、杨念群、李敬泽等人的参与,也让这次网络直播活动像古代文人墨客的雅集一样,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跨界意义。在活动结束后,我们针对活动中的问题对邱志杰进行了一次专访。
访谈主要围绕着做艺术和教艺术的话题展开。在邱志杰看来,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不同时是一个教师。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邱志杰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学生,厚厚三大本《无知者》《失败者》《实验主义者》便是他十几年来的教学札记。他热爱教学,并罕见而成功地实现了艺术教学和创作之间的“互济”。邱志杰说,“如果不是因为教学需要逼着我做研究,在教学中向学生学习,我的艺术不可能走到今天。”

邱志杰,当代艺术家,199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其作品常常运用多种创作媒材和形式,将当代主题、新的表现手法及展示方式融入到传统艺术中,表达对社会的见解和感受。近年来致力于实验艺术教育体系尤其是社会性艺术、科技艺术方向的构建。
艺术是一种解药或者一种越狱的密道
新京报:为什么会邀请文史哲不同领域的学者来参加这次新书发布雅集呢?
邱志杰:今天雅集,群贤毕至。在座有三位是我的老师,范景中老师、范迪安老师、陈嘉映老师。历史学家杨念群先生和文学家李敬泽先生都是我的好友。文史哲艺齐全了,我们下次还应该请两位,一位科学家,一位经济学家。
文史哲和艺术,不但是坐在一起,在中国,他们经常就是同一个人。古代要做个县令,你起码考过科举,格律诗应该写的不错的,书法也不可能太烂的,就算书法学的是馆阁体。
中学时代,我本来想要读古典文学或考古,想成为敦煌学家。至今都不止一个人劝我改当文学家。我觉得这想法是多余的——潘天寿诗写得非常好,他是书法的名声为画名所淹,诗名为书法名声所淹的一个例子。苏轼也是大画家、大书法家。中国画的传统是文人画,画家同时就是文人。画家同时写艺术史、写艺术理论天经地义。事实上我们重要的一些画论都是画家本身写的,像石涛的《苦瓜和尚画语录》,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文史哲艺不分家,是中国传统。

《剧透》,邱志杰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新京报:既然不分家,为什么做艺术?
邱志杰:哲学、历史都更诉诸理性。艺术从感性的层面入手,这些层面比思想更容易被控制,也更容易模式化。我们是能够觉察和警惕到思想控制的,但是怎么看怎么听,这种感性层面的控制,更加难以觉察。要用艺术去解放感性。
新京报:那么,艺术是什么?
邱志杰:世界上有很多种艺术,或者说我们用这个艺术这个词,指的是很多种,有时候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实践。我只能说说我相信的这种。我的模型大概是这样:现实世界是有毒的,让我们习以为常,天天照着套路来做事情而不知不觉。艺术把我们弄醒,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囚犯这一事实。艺术是一种解药或者一种越狱的密道。弄醒之后,你觉得外面的旷野风险太大,还是呆在牢房里面好,也行。你决定逃出去,也行。
新京报:你这个说法,除了艺术,还有别的词代入也适用吗?比如“xx把我们弄醒,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个囚犯这一事实。xx是一种解药或者一种越狱的密道。”
邱志杰:你太聪明了! 这里的XX可以是哲学和科学,但很难是经济学或政治学。
新京报:如果我不能比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更能反驳这个观点,我就不配拥有这个观点。这样,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每个理论,都有前提。
邱志杰:这个是批判性思维,基本上是哲学家的工作。艺术得在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再加上创造性思维。
新京报:你认为人们对艺术存在什么误解吗?
邱志杰:我认为大众对于艺术存在的最大的误解有三个。
第一,人们误以为艺术是自我表现。
自我表现的艺术理论会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为什他的自我不值得表现,而你的自我值得表现。第二,人们为什么要围观你的自我,你的自我有什么好看的?我比较相信人们看的是作品,而不是通过作品看你的自我。作品不是表达自我的工具,相反,有点意思的是,我是用来促成作品实现的工具。作品大于自我。在做出作品的同时,旧的自我变成了新的自我,小小的自我,变成了大的自我。自我本身是搞艺术的产品。所以我更愿意说艺术不是自我表现,但是是一种自我发展。我更愿意把先天倾向性解释成“迄今为止的塑造”。表现个性的艺术是二流的艺术。最好的艺术是展现世界的道理本身的。
第二个误解就是,人们误以为艺术家必须得是神经病。
这主要来自浪漫主义艺术理论的影响,浪漫主义塑造出一种波西米亚的艺术家形象,后来又经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在大众中形成了刻板印象。这想法也就300多年历史。艺术的历史,从法国南部西班牙北部那几个山洞算起,3万多年,最近在澳洲又找到了一个山洞,好像是44000年。三四万年来,艺术是个饭碗。艺术家得接订单干活,要么接教会的订单,要么接国王的订单,要么接艺术市场的订单。你想象一下,丢勒在巴塞尔的作坊里当学徒的时候,师傅来跟他说,有个富翁要订一张《圣母子》,他跟师傅说:不好意思师傅,我现在没有灵感----他肯定会被师傅暴打一顿开除的。那时候的艺术家并不疯疯癫癫。在中国,艺术家还是文人,几乎每个政治家,上至皇帝下到县令,在业余时间都会搞艺术,搞诗歌搞书法。他怎么能是神经病呢?
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和科学家是一样严谨的。要有想象力,都需要做实验,都需要好好的去认识世界。浪漫主义的艺术理论,把很多学艺术的同学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由于大众有这种误解,因此很多艺术圈里面的低端选手也因此模仿这种神经病形象,用来忽悠大众。看我也没有大胡子,也没有长头发,不是照样好好的搞艺术吗?
第三个误解和上面这个关系很近——人们误以为艺术要靠天才。
天才论也是浪漫主义搞出来的,当然之前就有萌芽。我们是根据一个人做出来的成果来判定他是否有天才的。如果一个号称有天才的人做不出东西来,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天才呢?------天才是对做出成就的人最后追加的命名。如果没做出成就来,所谓天才基本上是某种缺陷,比如《雨人》,对我来说近乎是骂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问。一个人如果是天才,就可以不接受教育吗?如果他要接受教育才能成为有成就的人,那么谈论天才不天才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人是有智力高下之分的,但是智力和创造力关系并不大。一个智商很高的人,很聪明的人,很可能没什么创造力,而一个并不很聪明的人,很可能很有创造力。毕加索、达芬奇这样的人肯定是聪明绝顶,但凡高就不太聪明吧。爱因斯坦的大脑也只被开发了一点点,就学艺术而言每个人的智力都是够用的,关键是你有没有好办法去用好你现有的智力。好艺术家工作的时候,靠的是方法。
艺术界里面被夸大的天才,意思是无师自通。那么他来美院,天才就被扼杀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我不能同意天才论,因为那样不民主。中央美术学院是好美院好,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总是能招收到天才学生。而是我们有好的教师,好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美术学院教的是正确的方法。他要确保和假设不是天才的人经过训练就能够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
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不同时是一个教师
新京报:你是实验艺术学院的院长,探索和实验在当下社会中有什么意义?
邱志杰:中国过去40年的成功是实验的成功。对我来说,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实验精神。不管黑猫白猫,就是卡尔·波普尔说的证伪。未来的成功,也只能依靠实验,我们要警惕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所以讲清楚实验艺术,对这个社会意义重大。
新京报:一个艺术家如何同时是一个教师?
邱志杰:自古以来的艺术家,就算不在大学里面教书,他也总是带徒弟带学生的,人们也是喊他叫老师的。对我来说一个艺术家不可能不同时是一个教师。因为他要去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主要是改变人。用作品去改变世界的时候是艺术家,用语言去改变世界的时候就是教师。
新京报:为什么要教书?
邱志杰:对我来说好好教书是一种义气。不仅是对信任我们、把未来托付给我们的孩子们和家长们的那种职业道德,更是对我自己的老师们的一种义气。知恩当图报,再没有任何别的方式可以报答他们所给过我的东西了。
新京报:听说你对教学非常投入。投入教学会不会影响创作?
邱志杰:年轻艺术家刚毕业的时候,通常都很愿意留校当老师,因为有身份,同时有寒暑假可以确保创作,还可以继续利用艺术学院的资源。但往往过了一些年,他们就开始觉得投入教学会影响创作,专注于创作,觉得教学是一种压力。而专注于教学的人,不得不放弃创作。我认为这是没有找到好办法。
我非常热爱教学,如果不是因为教学需要逼着我做研究,在教学中向学生学习,我的艺术不可能走到今天。我的每一张地图都是可以用来做教具的,而每一次教学,又都会产生出好几张新的地图。我是成功地做到了教学和创作之间的“互济”。这方面我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我总是去教自己不太懂的东西。
通常是我对某个领域非常感兴趣,并且预感到去研究这个领域能够有收获。然后我就会对学生说,我感觉这个领域值得研究,但我也不太懂,我们一起来做研究吧。于是分头去做研究,然后大家再互相来教。基本上,我认为教师应该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他要向学生示范他是如何学习的。这是一种学习如何学习的“元学习”。这样一轮课上下来,由于我的学习能力更强,经常我的收获比学生都更大,每次上一轮课,就冒出一批创作的想法。这样一来,我就会越来越喜欢上课。
新京报:教育角度,什么是你最想传下去的?
邱志杰:第一,勇气,自我要求和自我改造的勇气,和承担责任的勇气。今天的年轻人被资本主义和社会固化吓破胆了,吓出很多心理疾病来。所以首先要教会他们,相信自己,有勇气去坚持做研究和做实验。
第二,科学精神。说起来就是怀疑的勇气,和探索的理性,这是陈嘉映老师教我的。
第三,人文精神。具体来说就是看得到传统的美,知道珍惜该珍惜的东西,这是在座的范景中老师一再强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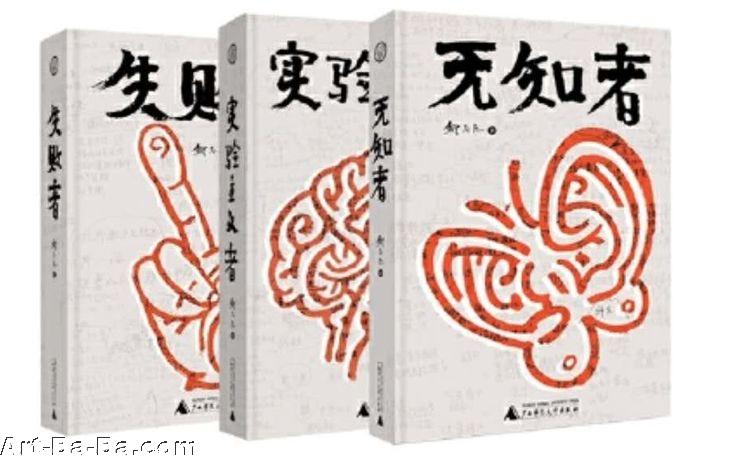
《失败者》《无知者》《实验主义者》,邱志杰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新京报:何为知?何谓“知见障”?
邱志杰:“知见障”往往是对“知”本身的认识出了问题。如果只是对具体领域和具体事务的知识,而缺乏自我审视就会造成“知见障”。对知识本身要有一种认识。知是批判发展的。有适用范围的。未来可能被证伪的。有了这种认识,就不会“知见障”。
新京报:如何开发孩子的创造力、想象力?
邱志杰:我觉得,首先是要提供出一种允许他们自由想象,奖励他们有创造力的行为的环境。我和女儿玩一种叫做胡说八道的游戏。当她胡说八道的时候,我是鼓励她的。很多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被大人一句“不许胡说”给扼杀掉的。
其次,有一整套的游戏可以玩。要培养游戏精神。培养游戏精神的方式就是艺术训练。
再次,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要深度融合。我正在写实验艺术史,就是把技术史和艺术史完全打通来写的。所以不能只谈创造力和想象力,应该是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的创造性思维。
新京报: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天生需要保护好,还是需要开发?
邱志杰:想象力和创造力,肯定是需要开发的。孩子和孩子之间有一些差异,但并没有那么大。成年之后的差异变得非常大,主要是后天教育开发培养,和社会文化环境是否鼓励想象和创造所决定的。
新京报:什么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如何培养面对未来世界的人才?
邱志杰:这当然取决于我们怎么判断未来以及人类还会不会有未来。我对未来的判读是:
一,今天传染病所表现出来的全球化暂停,是暂时现象,在更长远的眼光看来,全球化是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它的基础是技术。教育应该继续培养适应全球化环境的人才,培养世界公民的意识,反对种族主义,清算殖民主义的余毒。同时,如何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保持各种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是需要我们拿出智慧来的。
二,不要只看到今天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核武器、环境问题,传染病和今天的经济生活方式都决定了必须采取世界治理的模式。但是一战之后建立的国联体制和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体制,以及最近30年欧盟的实践看起来都失败了。所以在政治意识上,我们要为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储备人才。我们要做的艺术应该是全球治理时代的艺术。
三,迄今为止所有指责人们“迷信科学”的论证都不够强大。都多多少少采取了歪曲批判对象的稻草人论证的方式。科学和技术依然是人类理性最珍贵的成果,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是我们超越政治分裂的唯一机会。我们应该以道德感和社会意识去意识到技术本身的危险性,学会和技术发展并存,但并不需要倒退回前科学时代。因此,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真正的艺术精神的融合,应该是教育的核心。做的艺术,应该是具有社会意识的科技艺术。
新京报:如何看待娱乐至死的一代?
邱志杰:每一代人都有一部分人娱乐至死。娱乐至死这件事情,孔子在感叹礼崩乐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说罗马帝国为什么衰亡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同时总有一部分人在扛着历史往前走。

邱志杰(虚苑供图)。
技术本身就是人文的一部分
新京报:新技术在剥夺自由还是给予自由?
邱志杰:对我来说,综合来看是给予自由的。它剥夺了不能使用新技术的自由。天气预报剥夺了看云识天气的自由。GPS剥夺了迷路的自由。现代医学剥夺了短命的自由,现代农业除了饿死的自由。通信技术剥夺了在长城上点狼烟的自由。人类的平均寿命显然是在增长。农药和化肥发明之前,地球上到处都是古法种植农业和有机蔬菜,人们吃了,寿命却比现在短得多。
技术会被滥用,技术可能会被坏人掌握来害人,那是人性的坏,不能怪罪到新技术身上。自己不自由的人,不能怪罪到新技术身上。
新京报:人文精神和技术的关系,是矛盾还是推动?
邱志杰:技术本身就是人文的一部分。
新京报:能问一些更个人一点的问题吗?比如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持旺盛精力?听说你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邱志杰:旺盛精力、身心愉悦都是假象。平常还挺累的,是靠咬紧牙关,靠意志力在挺着。让人觉得我精力旺盛,身体巨好无比,都是假象。我只是善于抓住点滴时间休息,上个出租车都能睡着,一下车就满血复活了,整理磁盘碎片比较快。非常期待自动驾驶赶紧实现,我就可以在去学校上课的车上睡觉了。当然了,小时候家里苦,吃不到蔬菜,海边人天天只能吃生蚝和螃蟹,所以身体也还不错。
我更多地是出于责任感,以及对工作的热爱勉为其难的活着。我有点出世心态,小时候学书法就是在庙里边听老师和和尚们聊天,为他们磨墨,我们闽南有弘一法师的书法传统,算起来我是他几代之后的弟子。思想上也难免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后来我回归了儒家的思想。现在的信念基本上是用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支撑着我投入工作的很重要的动力,其实是愤怒。有太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在发生着,有太多东西需要去改变。
新京报: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平时如何使自己愉悦?你放松自我的方式是什么 ?
邱志杰:释迦摩尼佛说:“我为一大事因缘而来此世间”。能找到你想做的工作,并为之努力,是非常幸福的生活方式。如果还能做得有品质,那就更加有存在感和自我效能感。
工作就是最让我愉悦的事情。今天的艺术已经非常全球化了,因为艺术家这份工作的缘故,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成了一个旅行家,也喜欢美食,去过很多地方。旅行跟艺术是很接近的,都是在遭遇陌生事物。不管旅行还是美食,还是读书,都是跟工作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
我不需要所谓的放松自我,最让我感到放松的事情,就是工作,不管是画画教学还是写作。要是人们逼我去娱乐和休闲,从而影响了我的工作,这会让我非常焦虑和愤怒。
新京报:听说你每天能写1万字,为什么写作的速度这么快?
邱志杰:最高纪录是一天2万字。在电脑上写作的时候,我用科大讯飞鼠标,直接语音输入。非常愿意利用一切机会为他做广告。我能够迅速使用各种最新的技术。一边给学生讲课,一边一篇文章就写出来了。边开车边写文章的时候,我用石墨笔记。共享给我的研究生。手机和车里的语音系统互相连接,我边开车边说文章。个别识别错误的,那边的研究生同时就校对好了。遇到一个红绿灯,就能说个五六百字。从工作室开车到学校半小时,一篇3000字的文章也就写好了。
新京报:这个速度赶上网络小说写手了。
邱志杰:那是叙事性的文字,我写的基本上都是理论性的。先用语音输入把意思说清楚,把内容先铺出来,再修改,使文字凝练起来。要写文学性的诗意的文字的时候,我还是用打字的。但是我认为写理论文章用语音输入,人的逻辑性其实更强。人讲话是更讲逻辑的,写字的时候反而能够发散和跳跃。当我开始大量使用语音输入来写作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德里达要用书写中心主义来反对语音中心主义。语音似乎确实是比书写更有逻辑性。
而且我也认为,理论文章写得口水一点是一件好事。我给研究生们推荐乔治·奥威尔的《政治与英语语言》这篇文章。要求他们能写短句子,尽量不要写长句子。尽量不使用术语。搞理论是要把问题反复想明白,然后用平直浅显的话把它说出来就可以了。奥威尔举例讲到的那种坏英语,在我们今天的中文的理论文章里面也经常可以看到。“我家正在搞装修”这件简单的事,被他们那么一写,就变成了“此在的生存与栖息之所的物理形式在永劫回归的当下以人为设计的方式发生着景观与环境的嬗变与重构(搞装修)”。这种写作是骗稿费的,非常邪恶。这不是搞学术。
新京报:什么是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能亘古不变的?
邱志杰:狡猾的回答是,不变的只有易理。真诚一点的回答是:能量守恒和物质守恒。以及数学公理。
新京报:你的回答里只有能量守恒和物质守恒,没有人。就是说精神性、人性随着人类的消亡也消亡?
邱志杰:宇宙的某个黑暗角落,曾经萌生过繁荣过文明,即使后来熄灭了,会留下信息的。生命和文明都是非常精致,或许过于精致的形式,所以非常脆弱。但是它是最精巧的设计之一,这么美的东西,即使随着宇宙热寂而难免消亡,但也值得在消亡之前把它做出来。把它做出来的过程,本身就令人陶醉,令人着迷,我们并不因为一朵花迟早会凋谢而不去欣赏花,或者不去种花。
新京报:如果我们能握得住一把细沙,那可能是什么?
邱志杰:这是一个伪问题,所以没有答案。
新京报:为什么是一个伪问题?
邱志杰:因为你没有说明“我们”是谁?“能握住”假设了“不能握住的”是什么,”细沙“是什么东西的隐喻。所以这是一句诗歌,不是一个有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