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不周山 文:王鹏杰
最近发生了好些让我颇意外的事情,有些事也让大家意外,有时候思想和心智都乱乱的。可是回头一想,只要活过十几年以上的人,哪个年代没有出现过意外,哪个年代不特别呢?
就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一定是变的,不是恒稳的。既然总是变的,那现在发生了突发事件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惊讶不如冷静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自己的日子接下来要怎么过。
想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别总把自己幻想为君主或御用文人,动辄国家、民族、社会、全球,沃槽,你就是个屁民,你自己心里没点碧数吗。有的人显然不太适应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平凡人,那么疫情给你提供了一次机会,这是无数次机会的又一次,你努力想想自己其实真的是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生命,然后想想以这样的身份,接下来生活怎么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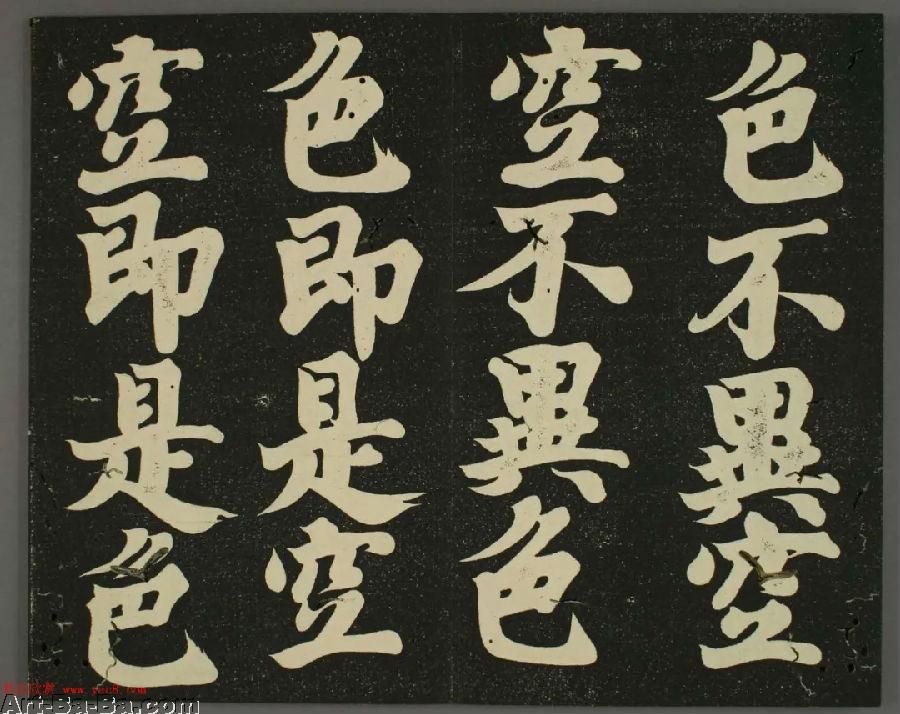
日本名僧空海的书法,写《心经》
关于族、国、球的事,你就别发表啥意见了,你确定你获得的信息是靠谱的吗,在后真相时代,所有媒体都像戏剧,都像艺术作品,除了审美体验,认知方面似乎助益不大。最近看到好多自信得像哈皮一样的人,拿着手机坚定的说,你看这条消息·········我都有生理反应了。
天天忧心锅事,这种还算比较淳朴的热心人。一些看了几本翻译的不阴不阳的哲学书的芝士粪纸,或者叫学者型艺术家,或叫文艺型学者,或叫新锐人文思想者,则更高级,忧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地域主义、生命政治、全球化、关系美学、结构语言学、后现代传播学在疫情时期的理论嬗变和话语结构,并对这些概念所表征的人类在各种群体、体制、情境、身份中的思想困境和革命契机阐发忧思。发表些让常人眩晕的宏论之后,总要时不时表达一下自己话语的正确,虽然他们口头上都反对各种正确。我其实想建议这些高人,可以先尝试在自己家里搞搞在地实践,把自己家人打造成他们理论话语中所描述的有理性、有前途、有可能性的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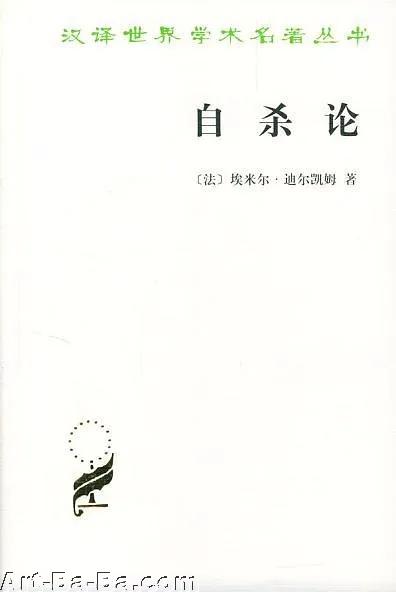
如果你喜欢研读理论,多想想自杀这个问题,其实挺有好处的。
提到这些高人,就容易联想到他们秀智商、刷优越感、亮存在感的理论话语。从话语的繁复性、精致性、体系性及其炫目感而言,无论西方的还是中国的知识左派,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新左派,也许自己不承认,都是这种典雅而富于理论美感的学术推崇者和制造者。这些人善于占据道德制高点和理论热点,用天花乱坠的方法与知识武装自己的表达,爱读书,爱写文章,爱吵架,喜欢车轱辘式的说话,说一大堆,塞进许多概念,但不清楚在说什么。这些理论大师几乎不太有能力面对具体、现实的问题,善于冷嘲热讽地批评他人在理论话语、身份背景、道德伦理方面的各种漏洞,善于做最体面的正义者和纯洁的聪明人。
这些人如果身在西方,大约一边倒地批评西方,为了证明批评的有理,还心安理得地通过无限抬高级泉国家治理模式来打击自身的文明,为威权、管控的政策辩护,罗列出所有关于个人自由、文化开放、理性思辨的弊端和隐患,上穷碧落下黄泉,收集材料之认真,不得不让人佩服,要不咋会有人说左派的学术做的就是精致。如果这些人身在国内,他们能动用所有的理论能力和素材为Z·f的任何行为作出最完整的解释,并证明其显然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要不怎么会有很多人说,还是左派的理论建设搞得明白,在结论已经给定的情况下,总是可以像猜谜破闷那样地转一大圈回到既定结论上,学术功力炉火纯青,照比西方同仁更上一层楼。

图片来自朋友圈
我其实想问一个小小的问题,放弃对现实主流体制批判功能的左派,是左派吗?如果读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问题应该挺好回答的。
谈到学术,我见识过很多搞学术的人,据我非常短浅的观察,发现真正把他们口中的概念搞清楚的人其实很少,真正身体力行进入现实去体验思考的人更少,不过他们的引用能力、编纂能力、改写能力、将表述学术化的能力确实惊人,不得不承认,近几十年来核心期刊机制和高等科研教学机构的成果评价机制确实完成了学术化的大跃进,我想一个猴子经受过这些学术训练,大概也能开始组织一篇专业论文了,当然它是靠刻板的经验,谁让这经验足够刻板呢。
猴子在阐发方面自然不如人类,阐发不是一门学问,但是一门维生的手艺,吃饭的家伙。拿学术过瘾、过学术瘾而又不学无术的职业学者,是我所了解的学术界主流。于是我知道,一味追求学术性、专业性、理论性的结果就是连正常人都不会做了。这样,我就越来越爱看“闲书”。最近看佛经、神学、小说、诗歌、传记看的一塌糊涂。

图片来自朋友圈
西方饱学之士,中土智囊学者,都从各种学科和理论的角度讨论新冠病毒,沾一点边就行。各种左,各种右,各种不左不右,各种类型都有。表达正义、表达愤慨,非常感人,非常适宜,非常积极,非常有意义,但基本上都是陈词滥调。表达歌颂、表达附会、表达非人观点,也是一种时髦,其中不乏读书读的话都说不清楚的高人,这些话语非常惊人、非常恨人、非常撞壁、非常煞笔,是一种更精致、更有美学创新的陈词滥调。这时,我觉得沉默真的是一种难得的能力。
世界变了,拿过去的标准思维去讲新的年代,不管出于什么立场,都不能避免成为哈啤的厄运。但也不必恐惧,因为即使你再明智、再机敏、再诚恳,也不能避免成为哈批的厄运,因为人这种东西永远在犯错、短视、自大、矫情中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能理解基督教、大乘空宗对人的局限性、劣根性的描述。而对于这种骨子里的,或者叫基因里的哈皮属性,虽然宗教说可以通过一定的办法来破除、拯救,但我想,这是一个安慰人类的慈悲之言,你若真觉得自己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而避免成为哈啤,那么估计彻底是没救了,神都懒得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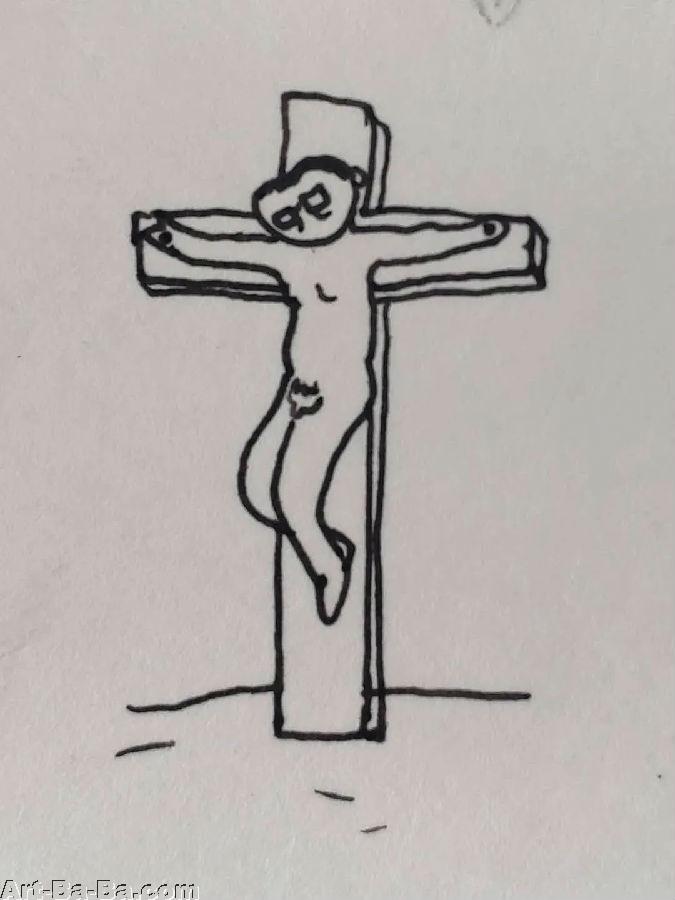
刘川画的,好像是画的我。
虽然我一直希望自己生活、工作的意义超越狭小的艺术圈,但我能力太有限,仍然深深地扎根在艺术圈。艺术圈的主体是由一帮智识狭隘、才能不济又喜欢舞风弄月者组成的,疫情来了,你说他们能放过疫情吗。当然不能。一批十分具有创造力、有胆魄、有情感的作品,围绕着疫情的种种,大批涌现来,规模堪比雨后墙角树下的小蘑菇,在很大的范围内获得了掌声。恭喜这些与时代脉搏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没有你们,艺术的星空将多么黯淡,那些因不幸失去生命的灵魂将多么寂寞。
文艺工作者,是吹~鼓~手,声响再大,也是边角料,弄不出多大动静。当然,如果是真正的艺术家,或许不是这样,不过当艺术家代价有点大,这倒不限于哪个时代和环境,大致来说,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异类,处处有面临对抗的契机,这也是真正艺术表达的机会。但文艺工作者,实质是工具人格,不仅不会遭遇对抗性张力,反而左右逢源,欢欢喜喜地闯作,作品最后都会涌向一个主旨:人间自有真情在。
感人肺腑,振聋发聩,正面能量无极限。就怕有时突然时势变迁,本来是正的,一下就成了负的,想转也难,倒不是转道怕丢人,主要是没那么敏感机智。真正的聪明人都削尖了脑袋要进入其他更接近资源核心层的圈子,即使要投资,也不会靠文艺这点小本钱。

最近因为疫情,出现了电子葬礼、祭拜代理的新业务,相当艺术。
疫情来,有人死,没挺到黎明的曙光到来,但至少可以说他们不是因为找死而死,可以肯定一点,很多人死了,其中一些人似乎本可以不死,或者说他们本可以挺到黎明的曙光到来,不过,黎明的曙光啥时候能到来啊?什么是黎明呢?虽然我们总被告知黎明已经来了。
疫情来了,很多之前掩盖或者说不太明确的问题出现了,大到庙堂玉宇,小至鸡毛蒜皮。说个中号的事吧,一些与捐款活动相关的流程数十年如一日的让人匪夷所思,灾难面前,迎来了慈善业危机。说个琐碎小事,疫情期间很多家庭出了或大或小的相处危机,据说有些地方不少夫妻因为疫情天天在一起而准备疫情后离婚,疫情让他们下了不想将就的决心。那如果疫情没来,他们还能将就下去又是因为什么?还有更小的事,比如小区被强行封闭管理后,很多居民买不到菜,社区表示帮着采购,结果不仅效率低,而且价格比居民自己联系的菜商还高。
这类事特别多,真正与我们这些不是各种二代的普通人息息相关,我最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怎么得到解决、这些危机如何得到具体的克服。用某些媒体的话讲,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但背后皆有深刻、宏大的渊源,怎么破?社会机制在突发困难面前运转不畅、有难处,人人都知道,造成这些难处的机制问题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有人偶尔提一提,有人偶尔回应一下,有点像双簧,但大部分没有解决。很多时候,很多相关者并不想解决,这个很多人也都心知肚明。不过,既然心知肚明,为何还要争当chao·yang·big`mother?即使不去试图改变、解决点什么,也不至于这么热切地呵护这肌体的病症。社会肌体病了是表面,人普遍性的病态化,或许更根本。但问题追究到人这里,基本就无解。

虎牙CNM
问题、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总是从胜利迈向胜利,这些永远得不到解决。我发现身边很多胜利主义战士,便觉得想解决普通人最切身的问题,几乎不可能了。知道不可能,再去面对甚至尝试解决,去尽量接近更好的生活目标,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个人道德。
比起那些胜利主义战士,我比他们聪明吗?当然没有,我甚至远没有他们高明。我大概明白,胜利主义之所以畅通无阻,是因为有红利,这红利倒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不过免于担惊受怕或许算一种精神红利吧,虽然是否真的能避免危险仍是未知的。毕竟,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能确定任何一件事的发展趋势,我们更不可能真的相信任何来自他者的保证。但即使这样,精神的安全感需要对胜利的认同感来支撑。
幻觉,有时就是生活中最真实的支柱,无论对于生活的管理者,还是生活中的被管理者,都依赖这精密非常的幻觉体系。我也生活在幻觉中,或许与有些人的幻觉不一样,但仍是幻觉。我有时会觉得看明白了一件事,有时觉得自己洞察了某一个空间,这是狂妄与愚蠢所致,也是由某种希望我可以保持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很高明的力量推波助澜形成的。我对于自己的责任要忏悔,事实上我最近也是这样做的;对于帮我获得幻觉的那个力量,我也要忏悔,因为我居然被它成功置入了幻觉装置,居然没有更有效的反抗。
毕竟我还相信自己是一个人,人都应该有自由意志,或者说人都应该保持对自由意志的追求,然而我追求自由的能力烂成这样,怎么好意思假设自己是一个真正精神健全的人呢。前面也说了,更内在的问题是人自己已经病入膏肓,这时呼喊什么高大的口号和理想的目标,不仅没有意义,而且简直是一个残酷的悲剧。如果可能,先从自我认知和自我批判开始,从自救开始。
我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幻觉中,在疫情期间我更明确了这个感受。很多人已经不想离开幻觉的怀抱,待在里头确实挺舒服的。有些人还想离开,其实比较简便的办法就是自己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被自己警醒之后,反思的程度会更深一些,实践的脚步会坚定一些。
但看的时候,别用镜子,镜子容易美化自己,可以在盆里尿一泡尿,自己从里面看自己,可能更客观真切一些。不过,很多时候想撒尿照己的时候,突然发现前列腺有些异样痛感,或许是自己病了,或许是自己老了,治一治,锻炼一下,还来得及吗,或许····此时可以再相信一次人可以得救,这点希望或多或少还是得有的,这大概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唯一希望。
写到这里,我走向厕所,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