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riggerFinger 触发
关小,1983年生于重庆,毕业于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电影专业,现生活、工作于北京。关小的艺术实践主要围绕雕塑和视频创作,她广泛引用包括了古代东西方传统以及当代流行文化的文化史。

幸存者的狩猎,展览现场,北京魔金石空间,2013
关小
2013年,我在北京魔金石空间做了自己的第一个个展《幸存者的狩猎》。展览借用了“核样”的概念来展现拼贴的内在工作方式,展览中的三屏录像《认知的形状》也是我的第一个录像作品。当时我很喜欢古代的雕塑和器具,站在审美的角度上,从形状出发,对它们的功能性进行合乎某种逻辑的揣测、改写和想象。

认知的形状,三屏录像,录像截图,北京魔金石空间,2013
板子上不同的形状是直接用树脂混合颜色捏的,不是泥稿翻模,所以细节非常多,不光有树脂材料的质感,也保留了我的指纹以及捏的过程中的各种碎屑和粉末,呈现出粗糙、凹凸不平的纹理,就像某种皮肤。观众进入展览后会最先看到板子上的形状,它们可以被解释为“把来自于生活中的各种残骸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展览的概念基础。

幸存者的狩猎,展览现场,北京魔金石空间,2013

博物馆方式,北京魔金石空间,2013

图谱,北京魔金石空间,2013
我一直很喜欢凹凸粗糙的、像壳、鳞片或皮肤等具生命感的物体,同时也喜欢作品里有一些幽默或反抗的成分。在第一个展览之后,我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比如,在2014年柏林ABC当代艺术博览会期间,柏林Kraupa-Tuskany Zeidler同时在画廊和博览会上做了我的两个个展:《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像从没发生过》(Something Happened Like Never Happened)和《一些事情发生了继续发生》(Something Always Happening Keeps Happening)。在展览中,我第一次做了树根的雕塑。

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像从没发生过,展览现场,柏林Kraupa-Tuskany Zeidler,2014

轻微的眩晕,柏林Kraupa-Tuskany Zeidler,2014
在很早的时候,我对于树根这种材料的使用其实是很怀疑的,担心它在雕塑语言以及文化符号上都过于强烈,不容易操作。但后来伴随着实践,我发现树根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在雕塑的定义中,我们总是需要去制作一个形体、一个与空间有关的物体。这是雕塑的基本特质。“树根”很好地承载了雕塑语言中“抽象形体”的功能,所以我不再需要去做一个抽象形体,在概念上它同时包含了经典雕塑语言以及拾来物(found objects)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当然,这些都是比较概念化的描述,而并非最直观、最贴近创作的描述。
这些年来,我在雕塑以及录像工作中做过许多不同的尝试,也许大家不是非常清楚,因此我在这里提及部分出现不同尝试的展览:
2014年,在安特卫普当代美术馆(M HKA)的群展“Don't you know who I am? - Art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中,我展出了我的第一组背景布作品;同年,在柏林Kraupa-Tuskany Zeidler个展上第一次展出了树根系列的雕塑。

纪录片:地心穿刺,安特卫普M HKA,2014
2015年,在纽约新美术馆三年展之后的里昂双年展上,我尝试做了一件十屏单通道录像的装置《一个和剩下的全部》;同年,在上海天线空间的个展《基本逻辑》上,我集中制作了四件树根雕塑,其中包括一件树根桌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茶桌)做的雕塑、一个三屏录像《隐藏曲目》和我的第一个墙上作品系列《调色板》。

一个和剩下的全部,第13届里昂双年展,2015

基本逻辑,展览现场,上海天线空间,2015
2016年,在伦敦ICA的个展“Flattened Metal”中,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使用半透明材料,并结合文字对话的概念做了五组全新的背景布;同年,在上海外滩美术馆HUGO BOSS提名展上,我展出了继2013年灯箱装置《日落》后的又一件大型灯箱装置《日出》,这件作品也在同年参加了第九届柏林双年展“The Present in Drag”。

小鼓,伦敦ICA,2016

大理石石板,伦敦ICA,2016

从单元3到单元7,伦敦ICA,2016
这之后,在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Jeu de Paume)的实验项目空间Satellite中,我做了第一件声音作品《如何消失》,其中包括LED字幕机、声音朗读与静止图片,并展出了受他们委任而做的新录像《天气预报》,这个展览在同年巡回到了法国南部波尔多的CAPC艺术中心;紧接着,我在上海K11美术馆的个展里对之前的部分作品做了一次小型的汇总,并再次做了《调色板》系列。

如何消失,上海chi K11美术馆,2016
2017年,在柏林画廊Kraupa-Tuskany Zeidler的第二次个展上,我首次展出了汽车龙骨与树根相结合的墙上作品,以及以模拟人类身份为出发点的柱状雕塑作品;随后在巴塞尔艺博会的“艺创宣言”(Statements)中,天线空间展出了我的个人项目,我再次做了一件大型灯箱装置。

活着的科幻,在红色的星星下,展览现场,柏林Kraupa-Tuskany Zeidler,2017

蹦极,柏林Kraupa-Tuskany Zeidler,2017

空气清新剂,喷,巴塞尔艺术博览会,2017

日出,第九届柏林双年展,The Feuerle Collection,2016

日落,柏林Daimler Contemporary,2015
接着,我受安特卫普当代美术馆(M HKA)的委任,创作了全新的三屏录像《登革热,登革热,登革热》,并第一次在录像作品中尝试政治讽刺风格;同年,我受纽约高线公园委任创作了一组由多件树根组成的雕塑装置。
今年年初,在波恩Bonner Kunstverein的个展《产品养殖》(Products Farming)中,我进行了各种大量新的尝试,如一组将现代主义的语言与拼贴结合而产生的悬挂雕塑系列(“Things that I Couldn’t Forget”),以及一组借由窗户与窗台的形式,试图将正在进行的当下、过去的回忆和刚刚失去的瞬间相结合的雕塑装置。另外还包括数件结合极简主义雕塑语言创作的全新树根雕塑和两件大尺幅背景布作品。同时,在今年上半年美国圣路易斯CAM的个人项目中,我通过空间的转换做了一件影像装置作品。


Fiction Archive Project,展览现场,圣路易斯CAM,2019
做雕塑需要一个简单的出发点,越简单越好。但恰巧这一点最难。因为这种简单要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其实是一种根源性,一开始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它是一个伴随着实践与反思逐渐舍弃与调整,然后慢慢浮出水面的东西。
从2013年到今年波恩的个展之后,我才经历到创作过程中第一个比较彻底的反思节点。所谓的反思不是指什么深刻的东西,也丝毫不理论或学术。它不外乎是在数量到了一定程度时,突然意识到有一些事情真的做不了、不擅长,也没必要花时间去尝试。大量的工作让我终于不得不接受我精力的有限,而这非但不让我感到挫败,反而帮了个大忙,让我终于认清或者说是接受了最适合自己的未来工作方向,变得不那么贪心。

慢波,波恩Bonner Kunstverein,2019
我开始意识到,使用故意制造的不和谐及幽默感来作为一种反抗对我来说的重要性。对我目前而言,似乎创作才刚刚开始。虽然我现在还远不到那个程度,但我知道,雕塑的工作一旦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系统,就可以尝试把这个系统做得更纯粹、更准确,甚至站在这个系统的反面用看似质疑或推翻的方式去做同样的工作,展现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一个艺术家一辈子的工作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阶段,而准确性就是在不断推翻和建立中产生的。
当然,艺术家不需要一开始就去想这个问题,想了也是错的。一开始艺术家只需要真实地按照喜好去做,不光在电脑上,而是在工作室中去做。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尽量扩大和全面化你的系统,包括建立很多不同的线索和系列,或舍弃不适合发展的线索,继而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指南针,展览现场,上海复星艺术中心,2018
蔡星洋
关小
我从第一个展览开始就一直在做影像,但现在做的影像相比以前的更抽象一点。很多人会问,我的影像和雕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一直试图想要去回答或不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回答不了,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影像和雕塑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它们能够实现的和自身的局限性不一样,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微妙一些。
有一些艺术家的影像和雕塑结合得特别好,比如说Michael E. Smith。他的雕塑都是拾来物(found objects),保留了原始的痕迹;而他的录像通常也是found footage,画质粗糙,通常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固定镜头,比如一个机械的持续运转或一条鱼。那种时间的长度和画面的简单程度让他把影像做成了雕塑,所以他的雕塑和影像在一起是一种非常和谐与成立的关系,是可以划等号的。

Untitled,Michael E. Smith,2017

而我的雕塑和影像不追求这种形式的和谐性,它们更像是冬天泡一个热水澡与冬天穿上厚重的羽绒服、棉鞋再带上帽子围巾之间的关系。两者的途径不一样,但意图类似。在工作了六年之后,我觉得现在可以试着回答一下,我的雕塑和影像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拼贴的手法;其次是在不同媒介中,对时间的延续性以及身份的单一性的疑问。


在对时间的讨论中,以影像作为例子,我不试图去构建严密的叙事或清楚的逻辑关系,而更愿意去尝试一种片断性的表达,用无数个瞬间来形成一种感官上时间延续的错觉。我觉得这种方式更接近真实,因为生活其实只有片段。对我来说,这种时间上的片段性在影像和雕塑中的体现,都是对一种“瞬间”的表达,只不过影像是在时间中的表达,而雕塑是在空间中的表达。因此,我的雕塑总是想要从雕塑语言上给出一种动势暂停或时间暂停的姿态。
同时,由于影像里使用了大量的片段式素材,把观众注意力的重点从对单个素材的读解中释放出来,转移到这种由无数个瞬间所形成的整体上,对我来说这便实现了身份的释放。而在雕塑的表达中,我的每一个雕塑都是拟人的,或者基于某种身份而存在的物体,装置则是对一种环境的描述。

我越来越将我的雕塑工作理解为以童话为理想模式的工作。在童话的语境里,任何看起来不可能的事物,都可能是本质上和我们一样的东西。在那里,我们可以超越外表的限制,很容易接受“差异”,不会去怀疑那些不可能之事的可能。
Guanqi
关小

可享受关系,柏林Kraupa-Tuskany Zeidler,2017
所以,我的作品一定会在一个稳固的结构上有一些节外生枝的东西。别人可能觉得这是多余的部分,但它们在我这里就会变成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语言。有一个策展人朋友后来提到,我的作品里幽默是很重要的一个语言,而我自己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Guanqi
关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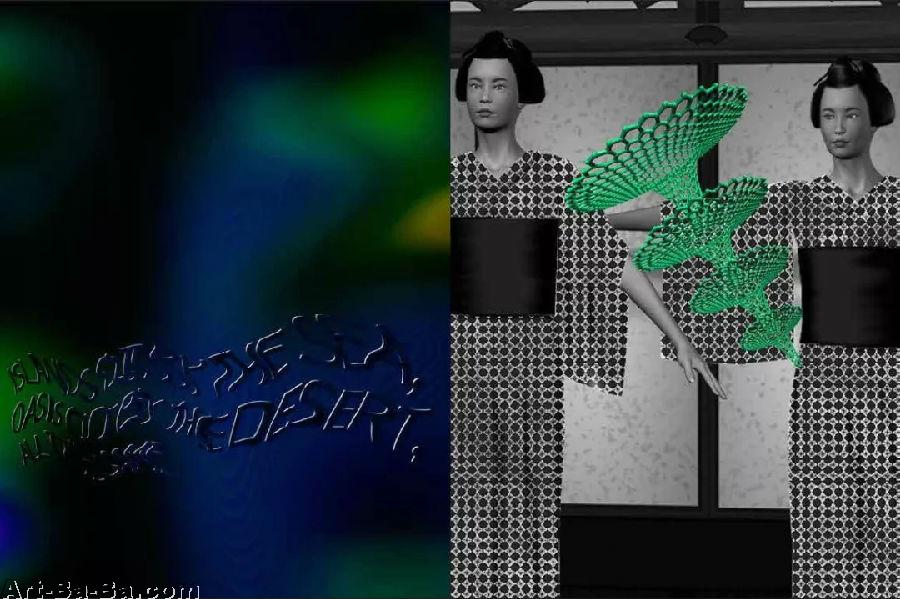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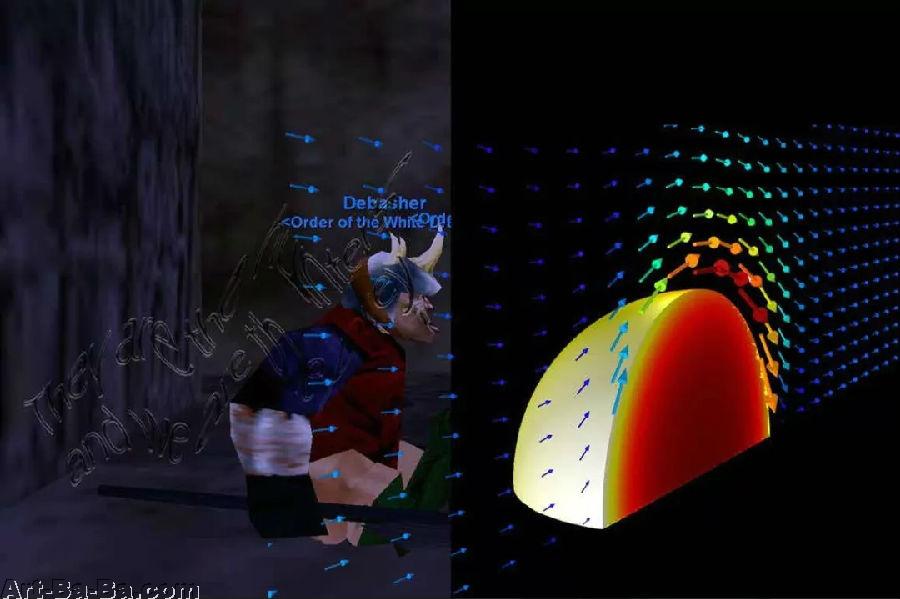

蔡星洋
关小
“系统”就是事物以某种规则组合在一起,并可以在其中产生无数种变化。然而,这里的规则是绝非逻辑性的,更像是一种物理的性质。我自己系统的基础就是“拼贴”,不过在拼贴的基础上又有一些不同的实践方向(线索)。
我认为在做东西的过程中,虽然说不用在开始就受到 “系统”的限制,但还是需要去知道系统是什么,这会对创作有帮助,尤其是在所谓的“合理性”上不会经常纠结。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系统,一旦你诞生了一个可以成为系统的工作语言之后,第一,你能意识到它可以成为系统,第二,你其实获得了某种自由的权利,可以集中精力在这个系统中尽可能丰富地去实践,而不会把精力花费在不同的系统之间,不断尝试却不能真的进入与深入。

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历史原因。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你很难在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教育背景中,从系统和根源上完全了解现代性、极简主义或抽象主义等等。就算你在国外读书,但你的生长环境、家庭环境和整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是不具备这种训练。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一些问题,即使我知道问题所在也解决不了。对我而言,这倒也谈不上是缺陷,它是一种事实,但对一些西方观众来说,这也许能够成为一种可能性。
蔡星洋
关小
我不认为存在感性和理性的平衡。感性和理性在根本上来说是一回事,绝对准确的感性表达等于绝对理智的表达。我觉得观众也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工作当中,如何让作品更准确和纯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艺术家是唯一决定自己作品是否准确和纯粹的人,也只有艺术家可以决定何时算是“做完”。
在构思创作的时候,我会优先考虑在已有的系统内工作,这样可以节省精力,把时间花在深入工作上。一个成熟系统的容纳力是很强的,理论上来说,它能够容纳足够多的内容供艺术家工作。

目前而言,我会把现有的所有实践中不同的板块分得更开,并且在每一个板块中继续深入和变化,比如在“童话”这一特征上做得更加明确。这都是自然而然诞生的一些想要去实践的点,是伴随着实践的深入慢慢产生的,不是计划出来的。但是,在工作初期还是要尽量呈现你当时在做的东西,不要想太多。除非你从一开始就带着很明确的观点去做作品(观念艺术),否则不要尝试硬要把雕塑往一个观点上靠。
如果做展览时你非要有一个观点,那就给一个,你觉得什么来劲给什么。“概念”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工作手法。文字也是创作的一部分,但文字不需要跟雕塑在一种逻辑严密的关系上去运作。现在的艺术家越来越被要求有阐述的能力,如果我们需要做这个工作,那么就把它当成创作去做。
蔡星洋
关小
因为学校把你们当成职业艺术家去培养,老师问那个问题没有错。然而,在一个观念建立之前,你需要非常多的实践经验,可能差不多十年的工作才可以产生成熟的系统,不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就有系统,那都是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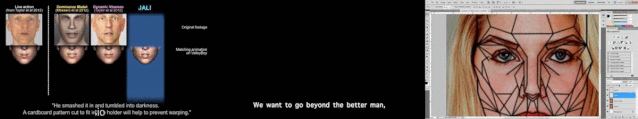
我们伴随着实践必须要对自己的创作很清楚,能够很准确地说出你在做什么,也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直接的问题:你在做什么?然而,在创作初期,我们往往都在自己读解自己的作品,给作品一个解释,就像自己是一个观众在很想象化地读解翻译自己的作品,这恰巧是很大的对可能性的限制。对于作品的阐述,你需要真实地说出自己的创作原因和出发点,而不是站在观众的角度去给出一个看似最“好”的解释。
蔡星洋
关小

Rest In,纽约高线公园,2017
摄影:Timothy Schenck
蔡星洋
关小
为什么很多艺术家会在职业生涯后期再去美国画廊?因为一开始去美国的话,你没有能力建立成熟的系统,让自己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产出如此多的数量。如果你的经济价值不够大,画廊不会做你的,即使做你也是当个装饰品。当然这都是市场的规则,不要在一开始考虑太多。系统这个东西以后会有的,如果单纯为了系统而去制造一个系统的话,那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不是在做艺术了。这就看你自己要什么了。

蔡星洋
关小
我接触过的策展人算不算大牌我不知道,但如果你跟他们谈理论,他们会跟你谈。你也可以完全不谈理论那一套,只谈工作上的一手经验,他们一样能明白,所以在他们面前真的不用焦虑这件事情。他们是旁观者,跟特别多形形色色的艺术家工作过,很快就能看出你的位置在哪里,以及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真正好的策展人会间接地帮助你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虽然不是所有的策展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但能够在欧洲机构里当主策展人的基本上能力都不差。我目前没有跟美国的策展人深入工作过,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但我觉得在美国,艺术家的角色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蔡星洋
关小
如果你不是一个艺术家,或一个艺术从业者都谈不上的话,是很难在美学的层面上去理论性地谈的。这个需要很多真正的实践,工作室的实践经验,或者需要大量的跟艺术家工作的经验。如果他没做过,就肯定不会知道。真正的美学理论只能在实践里产生。所以,很多策展人和评论家的工作很难,除非是接触了太多的艺术家样本,积累了职业经验。
而且,视觉艺术同样是可以批判的,太多这种例子了,艺术大师都是有反叛性和批判性的,当代雕塑艺术家中如Franz West、Isa Genzken、Phyllida Barlow等等。但是,当批判成为一种教育目的时,问题就出现了,很多时候大家就开始为了批判而批判。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不光只是美国。因此大家越来越会说,而不会做了,很遗憾。
蔡星洋
关小


Monday,Camille Henrot,罗马Fondazione Memmo,2016

A Cosmos,Rosemarie Trockel,纽约新美术馆,2013

What If It Barks?,Cosima von Bonin,纽约Petzel,2018
Isa Genzken,拼贴老母亲。她是从包豪斯极简主义里走出来的艺术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在拼贴的语境里工作。她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完全推翻自己以前的系统,她的艺术生命可能也因此延长了三十年。当然,她能这么做的前提是因为她之前的系统非常清晰,而且她胆子大。

左:Bild (Painting),Isa Genzken,1989
右:Schauspieler (Actors),Isa Genzken,2013
很多时候我有那种特别少女、难以迈过的恶趣味,Lily van der Stokker就是其中之一。Marisa Merz是一个意大利的贫穷主义艺术家,对于材料的使用以及如何去保持作品中的脆弱性,她做得非常好。


Michael Dean的工作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跟我的有很相似的部分,水泥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我的树根。他特别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虽然他是雕塑艺术家,而且并不过多地使用拼贴材料,但在我看来他的作品体现了当下拼贴的可能性。
我特别喜欢Richard Tuttle,他是百分之百观念性的艺术家,但你不一定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他是做观念的。去年在佩斯画廊,他非常清楚地讲了自己的几种不同工作系统,以及如何去反对系统,他拥有自己的雕塑方程式。
Peter Buggenhout也是我蛮喜欢的艺术家,他把所有东西都做得跟垃圾一样。他很清楚如何在看起来千篇一律的东西里做出不一样的层次,他的很多手段可以学习。

Sic Glyphs,Michael Dean,伦敦South London画廊,2017

On Hold #5,Peter Buggenhout,巴黎Laurent Godin,2017

双拐角与有色木,Richard Tuttle,北京佩斯画廊,2019
Robert Rauschenberg已经把所有拼贴的结构都做了,也许很多人觉得他太老了,审美上不太能接受。但如果看一下他的作品,尤其早期的作品,真的会对如何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另外还有近期我喜欢的非常”野蛮“的Phyllida Barlow 。

Untitled (Spread),Robert Rauschenberg ,1982

蔡星洋
关小
Simon Denny把自己限定得太窄了,这样的艺术家常见的现象是一夜成名,因为他们的工作模式太有特点,很独特。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艺术形式语言这种根本的工作,到底是不能长久的。只靠观念去做作品是很痛苦的。你的人生很长,可以靠观念做作品做十年,但二十年或五十年之后,你还可以吗? 很疲倦。

The Personal Effects of Kim Dotcom,Simon Denny,2013
摄影:David Bebber
蔡星洋

Fixed Sky Situation,Helen Marten,柏林König Galerie,2019
早期喜欢过。但看过她最近的展览现场后觉得特别悲伤。她的激情完全花在了制作过程里,让人觉得难以企及。我有一个朋友是她的邻居,以前他们共用一个很大的厨房。Helen Marten可以用一整天在厨房里做一顿饭,把各种东西切成丝丝、切成丁、更小的丁,切成片、更小的片,然后切满满一个厨房。看Helen Marten的作品感觉似乎能看到很多可以用的招,但是没有一个是能让人感觉到她在那儿的。就算她把整个房间都占满了,你依然很难感觉到艺术家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