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泼先生PULSASIR

图为2016年于巴黎举办的“创意之夜”活动上,拉图尔(Bruno Latour)与库哈斯(Rem Koolhaas)对话。本文原载于《今日建筑》2005年11-12月刊(Architecture d’aujourd’hui,n°361 pp. 70-79.),经授权转载自“集(BeinGeneration)”。
用盲杖轻敲库哈斯的建筑
作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译:Lilas;校:张凤鸣
众所周知,建筑师们每顿早餐都要吞下一套基本理论,因此跟他们同桌而坐的哲学家处境就像小拇指(Petit Poucet):对于主人家罗戈尔(Ogre,食人魔)来说,他永远不过是一块鲜肉。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超出自己能力之外去写一部宏大的颂歌(也完全用不着),而是宁愿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不会被生吞……我要做的只是简单说明为什么在我看来,雷姆·库哈斯的知识分子态度,跟我本人的哲学城市规划(urbanisme)里的一些纸上小模型有相似之处——因为一个哲学家毕竟总是妄想着让“理想之城”(Cité Idéale)更像个城市(urbaine),也因此,除了误解之外,建筑中总是有那么一点的哲学,哲学中却包含很多建筑成分。

《小拇指》(1697年)是法国作家夏尔·佩罗创作的童话
一个小故事会让你们明白我打算怎样"敲打"库哈斯。九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喜歌剧院(Opéra Comique),一群音乐家——“声音装修队”小组(Décor Sonore),有了一个可以说荒诞的主意,他们要把整栋古迹变成鼓和打击乐器![注释1]在用超灵敏传感器包围了花岗岩柱子、石头阳台及第二帝国的青铜器之后,(扮成了盲人的)打击乐手终于用他们的白手杖使整座建筑物发出了鸣响(通常只有在华美的Favart大厅里才有管弦乐队和音乐),却没使用任何乐器……我没有“声音装修队”的技能,但是我也想——可能不太恰当地——用我的手杖尖敲一敲库哈斯的作品,恐怕它们发出声响会让这本杂志的读者感到陌生。[注释2]


“声音装修队”小组(Décor Sonore)在世界各地建筑上的演奏项目
我的传感器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装上了,是用来录下现代过程所产生的震动的。在我眼里,库哈斯在努力走出20世纪,而这个世纪里的许多批评家都想让他回去。如果说人们已经说了很久(而且说错了)“愚蠢的19世纪”,那用什么词来形容20世纪呢?或许“卑鄙的20世纪”差不多。
我问莫里齐奥·拉扎雷托(Maurizio Lazzarato),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读一大帮死去的白人所写的书——塔尔德(Tarde)、詹姆斯(James)、怀特海(Whitehead)、杜威(Dewey),好像他们昨天还是大活人似的。而相比于20世纪的其他思想家,他们其实埋藏在被遗忘的时空的更深处。他理智地回答我,这些人都属于“第一次全球化”;他大体上认为在“1914年后,我们又成为了白痴;我们又陷入了辩证法,老黑格尔强势回归,而直到1989年后,我们才又开始思考”。[注释3]换句话说,结束了从14年8月到89年秋天这漫长的地狱之旅,第二次全球化复兴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智慧。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是什么让我们和所有这些曾被“辩证论者”活埋的伟大作者联系起来。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都是因为现代主义(modernisme)这个讨厌的问题。我用这个词既非指大体从波德莱尔开始的艺术分期,也不是指从勒·柯布西耶开始的建筑分期,我说的是一段更长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非常明确的两大特色来接收其波段:理性(la Raison)的进步运动,对人类学的否定。[注释4]
其一:对于现代人来说,时间从混合了理性与激情的过去而来,去往一个二者界线必然更加分明的未来。对一个现代主义者来说,前进,就是从蒙昧(obscurantisme)走向光明。我们可以怀疑光明的程度,标记出昏暗的阶段,但是最终,就像游荡在沙漠的以色列人、沙漠里的孤烟,从激情中释放出来的理性总是先于行进中的现代主义者。其二:从西方历史的开端以来,尽管所有实践就是将价值和事实混合起来,每一天都更深入一些,更密切一些,但是不顾经验的种种反驳,这将成为正式版本:只有“他人”——那些前现代人,才需要人类学。我们现代人是解放的产物。这就是为何我们能够研究他人,但我们其实没有人类学(就算有时会有,那也是因为我们“不管已经相当过时”,还是以某种反观式的异国情调,把我们的"边缘群体"当做客体来研究)。

“启蒙与光”展览海报及展览现场,2005
这两大特色为何可以引导我们让库哈斯这样的建筑师产生“鸣响”?首先让我们用一个实际状况来试试我们的传感器。让-皮埃尔·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知识渊博的现代主义者,此时正在南锡(Nancy)举办一场以“启蒙与光”(Lumières et de la lumière)为主题的精彩展览[注释5]。关于整个17和18世纪,这位开放、灵通、精细的策展人、艺术爱好者,呈现了建筑、生理学、绘画、光学、神学、雕刻、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啊?这么说,多亏了他的回溯,我们才成了有情众生?我们,我们这些现代人,启蒙的发明者,终于有一部人类学了?完全不是。实际上,到了20世纪,到了知识终于理性到懂得逃出我们的前辈曾趋之若鹜的火炉之时,所有这些联系就消失了。策展人——也是懂得在橱窗前汇集能证明过去的科学和文化之间有联系的惊人证据的人——用各种精彩的舞台术,让每个展厅里又脏又模糊的屏幕上浮动着关于精确科学的短片,无中生有,没头没尾,没来由、没计划;用画外音做“解释”,这些画外音的目的是证明这些“切实的发现”。在20世纪,别再利用神学、建筑、雕刻、政治和粗陋的技术进行追溯了。我们知道。我们无所依附了。我们走出了彼得·斯洛特戴克所说的包裹(enveloppes):我们生活在“外部”,也就是不生活在任何地方。橱窗里收集的华丽旧物与漂浮着不相干的科学事实的可怜屏幕之间的对比,揭示了现代人的无能,无能去思考自身的光明程度。否认历史,否认人类学,我们便无法更清晰地揭露那些谈论启蒙之人的蒙昧。如果20世纪并非彻底“卑鄙”,总要承认它毕竟是“愚蠢”的吧?

在搞清楚库哈斯的言论和建筑到底什么地方——在我看来——让现代主义者如此震惊之前,让我们先排除传感器可能会受到的干扰。我刚才说过,传感器相当清晰地记录了我感兴趣的信号。建筑师们已经让我们饱览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说辞。不幸的是,他们不满足于说,他们还盖后现代的房子(这是哲学家相比于建筑师的微弱优势:谢天谢地,至少我们不盖房子……)。但是后现代主义不过是撕去商标的现代主义。我们在后现代主义中看到同样的时间之箭,只是我们开始怀疑时间是否在前进。前后矛盾和怀旧情绪纠缠不清。我们在后现代里也看到对人类学同样的否定,只是我们现在将异国情调应用在自己身上,在此之前我们是把它留给别人的。后现代主义终于兼顾了现代主义的所有缺点,却少了其优点:征服的能量和理性的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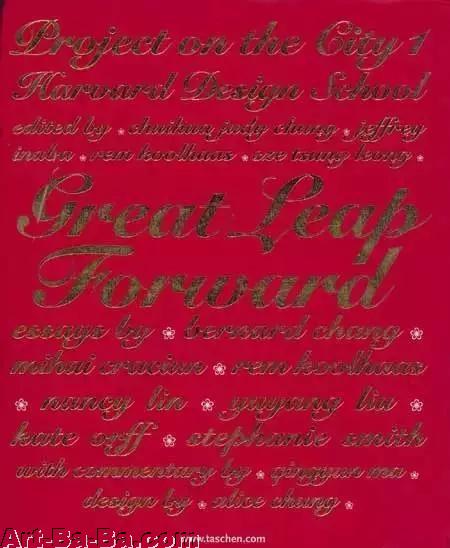
《大跃进》为库哈斯工作室与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合作的珠三角城市研究项目出版物,出版于2001年
现在让我们假设将现代主义的两大特色悬置:时间之箭不再从旧时飞向理性,而是从小程度的混杂飞往大程度的混杂。人类学不再是为别人准备的——也不是以反向异国情调为“我们”准备的:我们从未现代过,所以我们自身存在的各方各面之间的关联的本质——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lipe Descola)将其称为“认同模式”和“关系模式”——前提是一项结果无法预知的调研。[注释6]这种悬置一旦实施,如何记录60年代的纽约、90年代的拉各斯(Lagos),珠三角、上海、西雅图这些新现象呢?这些都不在现代主义的狭窄范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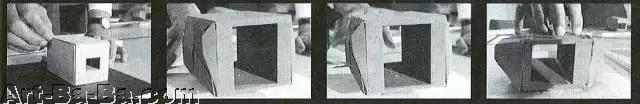



库哈斯在展览“实验室”(Laboratorium,比利时,1999,汉斯·奥布里斯特和范黛琳·范德林登策划)中的作品《转变》(Transformations)
在我看来,这就解释了阿尔贝那(Albena Yaneva)通过实地观察而明确提出的OMA工作的两大特点。[注释7]对模式的研究让人得以一步步追踪尺度变化的根本问题,我们看到的惊人一例来自“实验室”(Laboratorium),库哈斯将一座私人房屋改造成波尔图的一间音乐厅[注释8]。这也是“语境”(Context)与“内容”(Content)之间的论战,能够反证出现代主义为何是一个构架的问题,它精确分配了我们将内化的——建筑本身,和我们将外化的——仅仅是语境。不过如果我们走出现代主义,我们也就走出了语境——因此才有库哈斯那句不朽的“语境见鬼吧”(context stinks)。所以无论是建西雅图的图书馆,还是北京的摩天大楼,每一次都必须重新思考。现代主义本可以一边解放一边向前的。“非现代主义”(non-modernisme,其实没有这个词)强迫人拦腰抱住尺度变化这一关键问题,让这一问题变成必然的是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我们再没什么好外化的了。


波尔图城市音乐厅,OMA设计,建成于2005年
对库哈斯的批评总在指责他与人勾结:他在享受非理性,而没有履行揭露的义务![注释9]【人们也同样指责我的相对主义——本笃十六世(Benoît XVI)所说的相对主义……因为我乐于描述科学与文化之间数不胜数的联系,甚至到了21世纪还是这样,而不是像大家一样,去揭发“非理性的过分”】。
城市中心问题和勾结问题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行关系:现代主义者抱怨特大城市,就像地球中心说的信徒抱怨行星的行踪不定让他们不得不增加本轮(épicycle)一样。在他们看来,应该保持理性,以城市中心为思考起点,反对非理性,不能沉湎于赞美不可能的城市。而在我看来,库哈斯提出了另一套办法:改变范式(paradigme),颠倒为所有这些怪异现象所选择的源头,从不合理(déraison)出发(《癫狂的纽约》不是白白癫狂的),不再做现代主义者,改变尺度。我认为库哈斯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取决于这个尺度问题。

布鲁诺·拉图尔在展览“实验室”(Laboratorium,比利时,1999,汉斯·奥布里斯特和范黛琳·范德林登策划)中的作品:
《试验的剧场》(Theater of Proof)
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意识到拉扎雷托对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时的思想家的直觉。短暂的20世纪里的思想家们被现代主义范畴所困扰,不懂得衡量尺寸(dimensionnement)问题:他们虽然已经挣脱了混杂的力量和强烈的依附,却还在继续思考解放的模式。当事物超越了他们的范畴,当事物成为真正的怪兽,他们又诉诸批评和揭露——这基本上是今天的社会科学唯一还能做的了。[注释10]我们的人数从百万上升到数十亿,我们却不能再只是说城市中心的几百万人被郊区几十亿没理性的人包围了。现代主义,就像历史名城中那些中心步行区一样,不过是阿斯泰克斯(Astérix,法国漫画《高卢英雄传》里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0年,高卢地区的全境几乎都被罗马占领了。只有一个村庄里居住着顽强的高卢人一直在抵抗侵略。有相关动画电影《高卢勇士传》和《阿斯泰克斯历险记》等)的村庄。我们终于是时候借助“卑鄙的20世纪”之外的其他资源来思考21世纪了。这不就是库哈斯所做的吗?
[注释1] Dirigé par Michel Risse, decorsonore@free.fr.
[注释2] En fait surtout la série des Harvard Design School Guides et Koolhaas, R. and B. Mau (1995).Small, Medium, Large, Extra-Large. Rotterdam,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注释3] Il est notamment l’auteur de Lazzarato, M. (2002). Puissances de l'invention : La Psychologie économique de Gabriel Tarde contre l'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Les Empêcheurs.
[注释4] Latour, B. (1991).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Essai d'anthropologie symétr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注释5] Changeux, J.-P., Ed. (2005). La lumièr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et aujourd'hui (catalogue d'une exposition Nancy automne 2005). Paris, Odile Jacob.
[注释6] Descola, P. (2005). Par delà nature et culture. Paris, Gallimard.
[注释7] Yaneva, A. (2005). "Scaling Up and Down: Extraction Trial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5 (Albena Yaneva a consacré une analyse détaillée au projet du Whitney Museum à OMA)..
[注释8] Voir sa conférence dans Obrist, H. U. and B. Vanderlinden, Eds.(1999). Laboratorium. Antwerpen,Dumont.
[注释9] Koolhaas, R. and F. Chaslin (2001). Deux conversations avec Rem Koolhaas et autres textes de François Chaslin. Paris, Sens et Tonka.
[注释10]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