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典藏Artcoco 王慰慰
从荒原到钢铁丛林
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대안공간)于1999年左右正式在韩国兴起。早期韩国替代空间的创立者和参与者们很多是家境较为富裕的留学派,他们在西方接受当代艺术潮流的洗礼,回国后怀有着拓荒者的心态,在基本没有什么当代艺术系统或制度的荒原里构建起理想的艺术世界。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生产媒材、城市现代化建设等的急速发展都是相对应的。对于当代艺术在韩国的发展,推动韩国当代艺术家走向国际舞台,韩国政府对文化艺术制度的建立、修缮等方面都是起到作用的。
韩国早期的替代空间,如Alternative Space Loop、Art space Pool、Project space Sarubiadabang、Insa Art Space、Ssamzie ArtSpace等等,都显示出强烈的“机构性质”和与政府基金或企业赞助之间的紧密联系(注2)。然而,对政府基金和企业资金的依赖也成为韩国替代空间无法维持其独立性的最大束缚,也为后来诸多的危机埋下伏笔。
2006—2008年前后,韩国的艺术市场出现短暂蓬勃,大量复合型艺术空间,包括很多同时开设着咖啡馆的小型商业画廊纷纷出现,大型的国立艺术机构也开始开设驻留项目,举办非传统形态的展示活动,企业型美术馆或奖项纷纷出现。替代空间的功能被逐渐取代。整个艺术生态的层次逐渐显见,然而,这种包括思维、观念在内的生态层次显示出强烈的上下型结构特点。这样的生态结构也导致了展览艺术家的重复度很高,以及这些艺术机构在本质上的趋同性越来越强,替代空间成为这种上下型结构中的一个环节,为更高阶的机构或空间输送艺术家。商业画廊也在此时大举挖掘年轻艺术家,代理销售从替代空间里走出来的艺术家们。
在这些背景下,替代空间的发展余地越来越紧缩,所遭受的批判也越来越多。很快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量企业的资金紧缩,艺术市场同时崩溃。2008年9月Ssamzie Art Space由于母公司的经济危机而结束,也标志着韩国替代空间潮流的结束。发展到后期的韩国各替代空间,已经建立起相当规模的系统和交流网络,也逐渐形成当时当代艺术的主流群体,但也不知不觉地对“当代艺术”本身作出了权威性的定义,这种定义到了后期也慢慢成为一种保护,保护他们的价值评判权和既得利益。曾经的拓荒者成为权力的持有者,这些大大小小的“空间”组成了系统和制度,而制度成为权威,系统成了围栏。

Ssamzie Art Space
我们可以同时反观一下中国的情况,上海的比翼艺术中心(BizArt Art Center),成立于1998年末左右,由意大利策展人乐大豆(David Quadrio)与中国艺术家徐震及其他数位合作者共同运营,部分的资金来源为上海的数家欧美领馆的项目资助。围绕BizArt的,是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10年间上海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先锋艺术实践、国际交流和当代艺术生态建设。

比翼艺术中心的“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展览场景
BizArt在发展后期,战略调整极为明确和具有针对性,组织的展览和发生的事件也与商业画廊之间越发相互促进加深,几乎就是一流国际性画廊的艺术家输送站。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是,上海乃至中国各地的独立艺术空间、画廊的创办人、藏家、艺术资助人很多是外籍人士,他们先天地与西方艺术世界的牵连,为中国当代艺术向西方世界输出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然而,这些背景条件也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与商业艺术市场的密切联系。BizArt一词本身就饶有意味,代表商业与艺术的结合。BizArt之后于2010年结束,并变更为没顶艺术空间,归并到艺术家徐震的没顶文化有限公司旗下,正式成为商业画廊。除BizArt之外,2000年由从事设计行业的郑为民创立的非营利机构“东大名创库DDM Warehouse”是同一时间上海重要的独立艺术空间,为很多非营利性的艺术项目和独立策展人提供了展示空间,但由于与上海红坊创意园区的空间租赁纠纷问题而于2012年关闭。

比翼艺术中心的“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展览场景
除了上海之外,在广州的维他命空间(Vitamin Creative Space)创建于2002年,从一开始的非营利艺术空间也逐渐转变为商业画廊形态。中国这些独立艺术空间的转型或关闭,一方面是受到不稳定的资金来源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各种艺术空间的增多,分散了艺术家资源,空间功能的独特性和动力也逐渐消失。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但由于中国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仍处于上升阶段,2006—2008的泡沫期被冲击过后,艺术市场得以迅速恢复,并成为另一股强大的外因,刺激着中国的一部分独立艺术机构向商业画廊转型,以寻求新的活力和沟通欲望。然而,与商业市场过度密切的关系,也成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圈以及中国年轻艺术家发展过程中潜藏的巨大危机。

广州维他命空间外景
回顾中韩两国早期独立艺术平台发展的这段历史并加以对比,现在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早期的独立艺术空间在创始之初即确定下来的非西方化、非殖民化,即寻找本土文化艺术价值的这一主旨,在两国的独立艺术平台推动本土当代艺术发展上起到指向性作用,而这种对身份的认同、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挖掘,对于现在和未来亚洲艺术家的发展也一样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亚洲独立艺术平台的交流网络的形成,不仅帮助本土艺术家走向国际,也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一股亚洲力量,这种交流网络的延续和战略性合作将是未来亚洲当代艺术的关键性话题。通过与前首尔市立美术馆馆长,也是韩国Ssamzie Art Space的创始总监Kim Honghee的访谈得知,韩国的Ssamzie Art Space曾设立艺术家工作室、驻留项目,对国内外艺术家交流成长带来帮助,在展览之外常设表演等活动,对当时保守的韩国艺术圈起到撼动的作用。这种早期替代空间灵活多样的运营模式和实验创新的精神后来被部分美术馆吸纳,使美术馆得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与活化。这对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未来的新型美术馆的建设也具有借鉴价值。Project Space Sarubiadabang 以及Art Space Pool以多名艺术家、策展人和艺评人组成委员会制度运营,尽量避免形成权力中心,保持公正性和单纯性,同时引入多方资源的方式从某种角度上或许也是他们依然能维持至今的一个原因。
现在重读当年的一些文献,不难发现,韩国早期替代空间的不少运营者和参与者所提出的反思对今天的艺术空间(不仅是独立艺术平台)运营来说,依然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而中国部分独立艺术平台的商业化转型,则是在艺术生态层次逐渐增加之后寻找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动力来打开学术研究与商业运作之间的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市场的繁荣,曾经的荒原都生长出盘根错节的生态网络,却也在新一代艺术家面前建造起一片钢铁丛林。当艺术教育越来越普及时,希望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则和上一代截然不同,即如何在这个“千人过独木桥”的时代里寻找生存之地?

Art Space Pool
一场自下而上的演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韩国政府及私人对当代艺术的资金支持减少,而最先感受到危机冲击的正是年轻的韩国艺术家们。一如在访谈中一些年轻艺术家对我说的:“曾经在校园里看到前辈艺术家的发展前景很好,但是当我们毕业的时候,一切突然都坍塌了。”原有的很多政府基金、奖项资助等纷纷减缩,虽然有一些私人机构开设年轻艺术家奖项,但对僧多粥少的局面并不能起到很大帮助;同时,长久以来自上而下的文化艺术认证观念,也使得有限的资金资助系统往往分流在上层集团而和年轻的艺术家们群体没有很大的关系。原来由替代空间链接起的上层艺术阶层以及商业艺术市场也都同样遭受着经济危机,曾经的“进阶系统”陷入一种死循环。之后发生的包括关于“artist fee”“在美术馆等权威性空间里展览是否还有必要”等话题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年轻艺术家生存问题的讨论、活动、集会纷纷发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种主要由艺术家自主运营的、之后被统称为“新生空间 sinsangkongkan”(注3)的小型艺术空间开始在首尔遍地开花。年轻的艺术家们需要空间来练习、展示、交流,而在韩国这样一个竞争激烈、众人拥有相同想象共同体并认可单一价值标准的社会环境里,新生空间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且迫不得已的方式。
新生空间其实从2009年就已悄然开始,一些艺术家在城市的偏远地带租借小型空间,既作为工作室,也作为展示和活动的空间。这些空间的兴起与2009年后智能手机、社交网络SNS的兴盛直接相关,信息传播快速、宣传成本廉价、地理位置要求不高,使这些小型空间悄然散布首尔全城各个角落。必须要指出的是,韩国首尔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社交网络的定位信息,坐着地铁或公交车,就可以轻松到达位于即使较为偏僻地区的空间。新生空间大量涌现的主要时间段集中在2013年至2016年。这些空间中的一部分延续至今,但有的则由于资金和空间租约到期的问题,在运营2—3年之后就陆续关闭。
从各种访谈和资料阅读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与早期“替代空间”那代人的“拓荒者”和“建设者”心态截然不同的是,“新生空间”的年轻一代人面对的是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顽固腐朽、充满不公平的世界。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改变现有的文化艺术政策、制度并不抱有祈愿,也无意在例如GOODS(注4)这样艺术家们自发集合进行的博览会形态的买卖活动中建立新的艺术市场。他们并没有预先设定好要攻克某座堡垒,他们更多的是在缝隙中实验着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以及可以让年轻艺术家持续进行创作发展的良性系统。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演化过程,恰恰也是对艺术圈由来已久的自上而下的价值认证思维模式,以及对固有的文化阶级制度的反叛。
在纷杂的资料中,关于Gyoyokso空间的一些记录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从一开始,Gyoyokso空间的艺术家们就以集合体、平等交流的姿态出现,对项目的发展路线和时间规划不作特别的规定。虽然就展览外在形态和规模来看,似乎和一般展览没有区别,但内核很不一样。与将年轻艺术家从马赛克图景般的集合全景中剥离出来、单个地呈现给观者这种办展方式有所不同的是,Gyoyokso更关心的是艺术家群体间产生的互动关系。他们参考棋盘游戏的形式设计Gyoyokso Playbook,制定游戏规则,之后发起的“Dungeon”项目则以连续展览的形式,让艺术家们以游戏方式参与,又在展览过程中产生新的游戏规则,相互影响,环环相扣,最终让参展艺术家、观众都参与进来。这种独特的方式正是年轻艺术家们尝试脱离固有思维模式进行的一种“生态”实验。
GOODS的举办,则是另一种形态的实验,将创作初期的“类作品”视作“创作进行时”这一动态过程里的产物,将它们呈现出来并产生价值交换。承载艺术家创作观念的灵感、起点、实验、挫折甚至生活的物品可否被以“艺术品”的方式看待并产生价值,让艺术家自给自足?这并非简单的一次对年轻艺术家作品销售市场的摸索,而是一种对价值观和艺术信仰的测试。
还有,以艺术家Kang Jeongsuk为首的一批新媒体艺术家们,在自己的作品和实践中,关注以网络游戏为出发点,结合线上虚拟世界和线下现实生活的思路,以“Instance Dungeon”来进行对新生空间的理解和发展,也是一种新世代的异次元思维,对新形态的集合体、生态系统的探索。而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即是对划定圈子、树立权威等传统社会活动里的惯性现象的警惕,保持网络时代开放、互通、平等的理念。
发生在首尔的这些活动,都让我回想起在上海近几年前发生过的年轻艺术家项目。BizArt至发展后期也形成了一定的隐形势力范围,对年轻的艺术家也产生了一种权威性的压迫,一些艺术家开始悄然远离并进行更为独立的创作,而艺术市场的膨胀也让很多艺术家开始反思,并渴望做出新的尝试。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名为“未知博物馆Museum of Unknown”(注5)的艺术家集合体。他们的出发点是基于对博物馆制度和对“未知”这一概念的反思,尝试跳脱出被西方文化系统或商业投机交易所左右的所谓权威价值系统,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标准,以试错的态度对未知之物抱有敬意地去探究,而不以权威答案去加以肯定或否定。
生长、变化、提问、讨论和行动是其核心内容。也因此,他们一开始便不依赖于某个实体的空间存在,而是以松散的团体出现,不定期地进行对艺术、历史、生活等等问题的讨论并举办一些展览活动。在BizArt关闭前,邀请“未知博物馆”的艺术家举办了BizArt的最后一场展览,这场名为“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以开放姿态讨论日常品、艺术品及艺术创作态度的展览,令“未知博物馆”受到中国艺术圈关注。随后,他们在北京的独立艺术空间箭厂空间举办的“Décor”项目,则以向观众出租艺术品的另类方式,展开对艺术、生活、价值等等问题的讨论。很快地,“未知博物馆”被多家美术馆、艺术空间甚至画廊邀约,在2011—2012年间参与了十多个展览。“未知博物馆”虽然没有固定的空间,但像一个流动的容器,让众多上海的年轻艺术家自发地卷入和互动,展开了大量关于年轻艺术家生存、生活、创作、销售等等问题的讨论,对当时上海当代艺术在知识的生产、实验方面起到很大的推动。

箭厂空间外景
然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演化从来都是漫长而艰难的,快速而过度的膨胀也往往会导致挫折。而有时,上层结构的介入,则可能带来一种内向摧毁的软暴力。GOODS的可行,在于其实验性、自发性、不可复制性以及“异次元性”(即不处于传统阶级体系中),但之后数个由美术馆主办的,邀请很多新生空间参与的大型展览(注6),虽然在机构策展人的角度上看是一种对“新生空间”浪潮的客观呈现,这对于梳理现有当代艺术体系并让美术馆进行自我更新方面固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是过早地将这群在努力建造“异次元”的年轻人置身于一个他们并不希望也并不应该俯首称臣的系统中,接受传统价值体系的评判。而这些展览,结合之前发生的对年轻艺术家状态争议的累积,形成一股风浪,在整个韩国艺术圈掀起了对于年轻艺术家价值观取向、其作品是否成熟,甚至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等等问题的诸多批判和讨论。而所有这些喧哗一方面加速了“新生空间”的挥发,另一方面也确实让一些年轻艺术家被主流艺术圈注意到并由此获得更多展示机会(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使部分“新生空间”再度成为传统系统层级里的一个环节),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让一些“新生空间”的参与者们更为冷静地面对未来的方向。
其实,这种现象是所有艺术圈内大机构与年轻艺术群体相遇时会遭遇的矛盾,前几年也普遍存在于中国的艺术圈。比如,2011年,我在上海当代艺术馆策划了名为“+Follow”的年轻艺术家群展,邀请了“未知博物馆”展出了他们的“珊瑚计划”项目,这也成为他们的首个美术馆展览。在“珊瑚计划”中,参与的艺术家们以类似“击鼓传花”的方式传递参展信息,由参与者寻找和决定下一个参与者,作品在双方的讨论和交流中产生和创造,每一个参与者都会参与整个展览思路的构建,但是并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全局。这种极为实验性的方式,打破了常规的策展人控制全局的金字塔式层级结构,从而形成了链式的平行结构或网状结构,使信息流向不是向心聚集而是扩散延伸。
然而,这种复杂的概念使它很难被观众在短时间内理解,且由于参展作品形成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而使得现场的呈现很难达到所谓美术馆级别展览的视觉品质,而一旦实验的内容没能被完全理解,则导致一系列的误解和批判。“未知博物馆”在之后大量参与全国各地的大小展览,于2014年左右正式停止活动,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如大量展览对艺术家精力的消耗。部分艺术家开始反思这种为大量展览生产作品的方式是否有必要性。部分艺术家在展览过程中受到关注,转而更多从事个人创作,有的也开始被画廊代理而进入商业市场系统。
作为策展人,不论是回顾与未知博物馆的合作还是考察新生空间与传统艺术机构的关系,留给我的教训和反思都是:这种充满实验性的年轻艺术家项目或者潮流(现象),是否一定应该被放入传统美术馆的框架中?这么做是否会消解实验的核心价值?是否有消费年轻艺术家之嫌?还有没有别的更恰当的方式让美术馆(即传统的艺术机构体系)与年轻艺术家群体发生关联?诸此种种。但在近期面对中国蓬勃的艺术市场发展的时候,这种思考似乎有必要转往另一个方向。以私人美术馆占大比例的中国艺术机构领域是否唯有与艺术家们共同卷入市场才是唯一出路?或者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以积极的态度自组空间来投入博览会、商场展示,或以私人藏家的资金来自组“实验性项目”,其背后更多的是艺术探索,还是另一种资本的共谋?当然,此乃题外话,暂不在此赘述。
近未来的平台实验:从平面壁垒进入立体网络
虽然不能一刀切地下定论,但至2017年为止,“新生空间”的浪潮对很多韩国年轻艺术家来说已经过去,而对其进行的反思在我看来是应该发生在整个韩国艺术世界的,应该是对固有的美术馆体系、画廊体系,直至整个文化阶级体系的反思和改变。随着网络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世界似乎趋于越来越扁平化,然而,扁平化的积极意义在于外在刺激可以被更多的主体接受,并由不同的主体激发出不同的反应。同时,世界被越来越拉到同一交流高度,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仰望或俯视,而是左右环顾,应对这种改变,人们需要学会立体网络思维。当然,这种对仰望或俯视关系的打破,也是对人们在这种上下关系中确认自我身份之传统思维方式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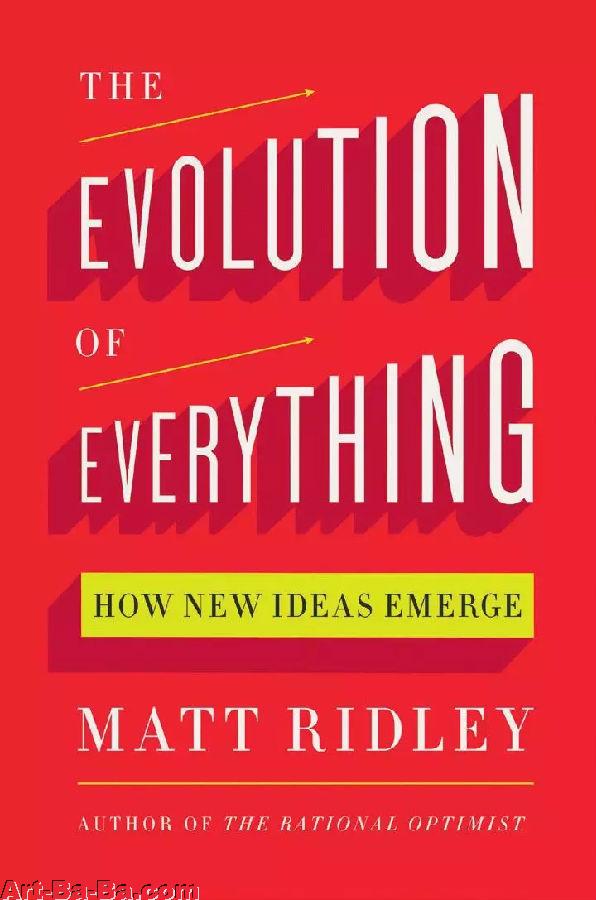
马特·里德利,《自下而上》
有些艺术家认为“新生空间”是一场失败的运动,且对未来似乎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不过在我看来,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那只是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一如马特·里德利在《自下而上》(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生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演变,并且是一场可以存盘的游戏。演化的过程往往是通过试错来完成的,但一如生物体本身会通过自然选择机制逐代修正遗传基因那样,那些错误会在游戏通关并存盘之后成为过去,而演化则会进入下一阶段。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演化过程目前依然存在于变化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里。

Doosan Art Center
目前,首尔的独立艺术平台之多是令我瞠目结舌的,几乎每天都有展览或活动开幕。我在首尔逗留的半年内,经常去的独立艺术平台就有近20家。在这些空间中,有的是“替代空间”时代存留下来的,有的是“新生空间”浪潮中存留下来的,有的则是新开的。其实,在我看来,韩国还有一些艺术空间,其项目设置和规划都具有灵活开放的“独立艺术平台式”思维。例如集中发掘韩国年轻艺术家,并开设海外驻留项目以推动年轻艺术家交流的 Doosan Art Center,以少量资金但大量活用外部资源、将项目扩展到除展览以外的旅行、出版、沙龙等多元形态的 Total Museum,以及致力于推广韩国中青年艺术家,对他们进行长期跟踪研究、合作并进行作品收藏的 SongEun Art Space。

SongEun Art Space1外景
纵观各种韩国的“独立艺术平台”,艺术家的自发性、反思性和深入性都非常令人钦佩,但最大的隐忧,或许还是资金来源,在“新生空间”浪潮发生时和之后,政府相应调整了基金支持制度,也让更多的独立艺术平台能够获得补助。于是,目前大量的独立艺术平台依然以政府基金为主要资金来源。如何自我开源以达到自给自足或许是这些独立艺术平台最大的课题。然而反观中国的状况则是,由于没有政府补助,独立艺术平台在资金来源上更为多元,但也导致资金的不稳定以及对商业市场的依赖。在各种本土及国际独立艺术平台之间如何彼此借鉴、沟通、合作,以达到互相引入活水和动力,我相信这是未来至关重要的课题。而作为当代艺术圈一分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铭记于心的是“独立艺术平台”所代表的那种自主意识、进击精神和努力保持独立性的态度以及寻找主流之外另一种可能性的开放思维。
文 | 王慰慰
【注释】
1.此文的初稿是我参与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 “MMCAinternational research fellowship 2017” 时所做的调查报告,之后经过几番修改和更新,最后完成此中文版。文中涉及少数对中国独立艺术平台的论述,亦是我近期对亚洲地区各国的独立艺术平台调研的一小部分内容,由于本文主体为对韩国独立艺术平台的发展概述,因此进行两国比较的论述部分被相应减少。
2.韩国在IMF之后,市场萎缩,很多原有的美术馆及文化财团预算减少甚至关门大吉,年轻艺术家们生存和创作都面临困难。带着自救的意识,由一批艺术家、策展人、评论人联合起来分别于1999年成立了Alternative Space Loop、 Art space Pool、Project space Sarubiadabang,除了Alternative SpaceLoop为Suh Jin-suk个人创办以外,另外两家都由多位艺术家、评论人以组成委员会的方式运作。成立于2000年的Insa Art Space虽然在功能上可以被归属为替代空间,但其实却是由政府设立的,而1998年就已成立Ssamzie Art Project,之后于2000年转型的Ssamzie Space则由呼吁以文化艺术软实力来克服经济危机的Ssamzie Ltd。
3.新生空间sinsangkongkan的浪潮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将其直接英译为“new art space”会产生歧义,因此在本文中直接按照韩语音译为sinsangkongkan及中文“新生空间”。
4.2015年10月,由15个Sinsangkongkan和80位艺术家们共同参与的具有销售形式的活动“GOODS”开幕,达到“Sinsangkongkan”运动的最高潮。
5.未知博物馆的主要成员有邱黯雄、李晓华、吴晓航、许晟、郑焕、吴鼎、廖斐等,但每场活动都有不同的艺术家加入或离开,是一种较为松散的状态。从2007年成立,至2014年不再活动。
6.2015年7—8月,由原CommonCenter运营者Ham Youngjun担任Ilmin Museum总策展人之后策划的展览“New Skin: Modeling and Attaching”,邀请了一批Sinsangkongkan及与之合作的艺术家们参展,第一次将Sinsangkongkan在美术馆的空间中呈现。2016年,在首尔市立
美术馆开幕“SeMA Blue 2016 <Seoul Babel>”展览的时候,部分Sinsangkongkan由于空间的租约到期等原因已经关门,同时前两年的热情也已经不在了。
【参考资料】
1.김장언, “미술과 정치적인것의 가장자리에서”, 현실문화, 2012(金章言,《艺术与政治的边缘地带》,现实新闻,2012 )
2.“메타유니버스: 2000년대 한국미술의 세대, 지역, 공간, 매체”, 미디어버스, 2015(《MetaUniverse: 关于2000年代韩国艺术的世代、地域、空间、媒体》,Media Bus, 2015 )
3.신혜영, “한국 미술생산장의구조 변동과행위자 전략연구- 2000년대 후반이후 신참자들의진입과 전략변화를 중심으로”,연세대학교 커뮤니케이션대학원 영상커뮤니케이션박사논문, 2017
(申慧英,《韩国艺术生产的构成变化与行动者的战略研究——以2000年代后半期艺术圈新晋者与战略变化为研究中心》,延世大学传播学系研究院影像传播博士论文,2017 )
4.윤원화, “1002번째 밤: 2010년대 서울의미술들”, 워크룸 프레스, 2016(允文化,《1002个夜晚:2010年首尔的艺术人们》,workroom press, 2016 )
5.Special Feature,「신생공간, 그 너머/다음의 이야기」, “미술세계”, 2016.2.Vol.385(特辑《新生空间,以及之后的故事》,《美术世界》,2016年2月刊,总第385期)
6.Special Feature 「대안공간에서꿈꾸는 대안적미술」, “월간미술”, 2004.2.Vol. 229(特辑《在替代空间里想象的替代性艺术》,《美术月刊》,2004年2月刊,总第229期)
7.Jeongyoon Choi, Case Records 2013-2015:Direction of Young Artists, SeMA Blue <Seoul Babel> exhibition catalogue,2016
8.굿즈 GOODS, GATALOG GOODS, 2015
(以上的韩文及英文书籍皆暂无中文版,作者姓名及书名的中文翻译皆非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