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托比·齐格勒(Toby Ziegler)
Toby Ziegler: Your Mother 慈母
展期:2018年10月31日至2019年1月4日
Simon Lee画廊(香港)
香港| 展览现场|| Toby Ziegler: Your Mother 慈母
托比·齐格勒(Toby Ziegler)生于1972年,于英国伦敦生活和工作。其作品在国际上广泛展出。托比经常探索 “数字技术和它与模拟世界之间发生的事情 ”。他的绘画,画在铝制金属上。作画过程十分奇特,首先经过技术再生(Technological Reproduction),他会找到自己喜欢的古典画,然后透过Google的图像搜索,去搜索相似的画像,一张找一张,渐渐变成了另一图像,托比再利用影像,投放在铝板上,开始作画。作画的第二个过程,作为物质侵蚀(Physical Erosion),当他在铝板上画了个大概,就使用磨砂机,开始把顏料磨去。完成品既抽象,又露出一半颜料、一半铝材,意象十分奇特。
Toby Ziegler的个展 “慈母 ”于10月31日在香港Simon Lee画廊开幕,这是他在香港的第二次个展。艺术家Toby Ziegler的新作取材自17世纪法国巴洛克画家Georges de la Tour的两幅画作,分别于1630年和1640年完成的Magdalene with the Smoking Flame和The Flea Catcher。Ziegler以此为轴心,发展出一套解构和象征的词汇。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1月4日。

托比齐格勒在他的伦敦工作室
摄影:Thierry Bal

展览现场:慈母,托比·齐格勒,Simon Lee画廊,香港
艺术碎片对话
托比·齐格勒
翻译:贺潇
Q:
通常你会将古典画作或历史性的图像,经过精心的数字化处理,重新再现一个你所理解的现实样貌。首先你是如何理解这些古典或历史性的图像,与数字化媒介之间的关系?
Toby Ziegler :
我想它们通常是我没看过的画作。我感兴趣的是,图像在当下如何被去语境化,它们是如何失去叙事、又重新获得新的叙事的,还有数码技术是以何种方式扭变图像的。也就是说,图像在被转变成JPEG格式的文件时,除了去语境化和与其他事物并置使之变形,这些技术手段还以一种类似于即兴的方式造成视觉失真。
此外,我还对计算机处理图像的方式感兴趣。这种输入/输出的过程创造了两种语言,我认为这恰好类似于我处理绘画的方式。我喜欢的很多绘画都是这样产生的,它们历经了完全抽象化的处理,但还能表现出具象性。有些画家能够娴熟地运用其中诀窍,他们使作品兼备抽象性和具象性。对我而言,计算机以相似的方式在屏幕上呈现出清晰的、可辨别的图像,但它已经被简化为数据,就像数据标准化的[0,1]区间那样,它掌握了其他语言。
最后,我认为数码技术还导致了信息的流失,也就是身体性或物质性的消失。这样的图像失去了重量。它们居于画板上的物质性被消磨殆尽,而这也是由图像转化的方式所引起的。
Q:
其次你的作品更像是你在当下媒体世界中对美术史、图像的重新观看和认识,那你是如何看待的?
Toby Ziegler :
我认为图像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运作。在选择需要处理的图像之前,我会将某个想法反复思考好几年。我电脑上存有很多很多文件,我总在收集图像,并不断地思考它们,并进行分类。事实上,我曾经几乎放弃了绘画。在刚离开艺术学院的时候,我停止了绘画,因为艺术史已经进入到让人难以绘画的阶段,你找不到任何一种毫无陈腐之气的方式来处理绘画。我想这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我刚从艺术学校毕业的时候,在后现代主义之后,你很难从绘画的角度对艺术史进行新的诠释。

左:Georges de La Tou, The Magdalen withthe Smoking Flame, c. 1635-37, 油画,145.4 × 120.7× 11.43 cm
右:Georges de La Tou, The Flea Cathcer, 1630s - 1640s, 油画,120 x 90 cm
在本次展览“慈母”中,我所特别处理的图像是两幅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的绘画。它们都是虚空绘画(Vanitas),即一种凝视和反思着“死亡”的艺术风格。这两件作品都出现了燃烧的蜡烛的意象,它们象征了生命的稍纵即逝。其中一件作品还出现了骷髅头。在我看来,它们恰好与我在思考的图像和物质性的消逝形成了互文。
我关注这些作品的形式,这些画中人物呈现出清晰的几何学结构;我也被更私密的表达方式所吸引,因为这些人物填满了画面。

Toby Ziegler, Four women, 2018, Oil on aluminium, 130 x 193 x 4 cm

Toby Ziegler, New forest, 2018, Oil on aluminium, 130 x 193 x 4 cm
这两幅绘画分别描绘了一位年老的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女性形象。在通常情况下,我会认为自己是以非常客观和理性的方式创作作品,但最终我总会发现,这些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种自传性,我想这组作品正是我对母亲的纪念。
Q:
往往你的绘画就像是用不同的媒介工序、材料、形式构建了一层艺术思考的“界面”,那你是如何看待这些材料的,赋予它们哪些不同的要求?随着材料方法的改变,艺术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比如纸板、木材、铝面、油漆、打磨等方法)
Toby Ziegler :
当然。我认为有很多内容都存在于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我处理作品的过程和选择的材料都是对某个问题的回应或解决它的方案。对于这两幅绘画,我的想法是要消解画家在绘画过程中的重要性。

Toby Ziegler, A certain depth, 2018, Oil on aluminium, 60 x 50 x 3 cm

Toby Ziegler, Retreat, 2018, Oil on aluminium, 72 x 68 x 3 cm

香港Simon Lee画廊:Toby Ziegler首个个人展,2014年

Installation view, Toby Ziegler: The Genesis Speech, Freud Museum, London, UK, 2017
我的雕塑作品也是如此。我想表现出模拟电子和数字电子技术之间的交合处。每个问题都有诸多解决方式,而这往往与制作的速度有关。对于这些绘画,它们必须使用铝板材料,因为我需要打磨它们,使之成为坚硬、平滑而光亮的表面。而对于雕塑作品,它们也与制作的速度息息有关。你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创作绘画,但打磨它们的过程却是快速的;而构建雕塑、创造几何形态的过程是漫长的,但制造表面褶皱的过程却很简单。因此,我总会以某种快速过程来扰乱精雕细琢的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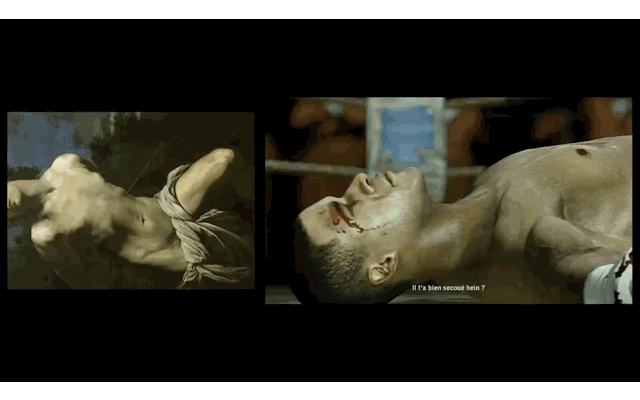
Toby Ziegler: It’ll soon be over (exquisite corpse), 2018,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Simon Lee Gallery.
我的影像作品也体现了不同的速度——一个屏幕上的图像以某一速度进行转换,另一个屏幕则速度更快。同时,我认为这也与观看速度有关,我们观看屏幕图像的方式与观看绘画的方式非常不同。就算是观看绘画也是一样,在观看某些绘画部分时我们的眼睛移动得更快。总之,它们与数字和模拟电子之间的关系有关,这在影像作品里表现得更为明确。
Q:
从你以前的绘画会看到很多类似像素的图像处理,但这一次展览的绘画作品好像改变了这种理性的图像处理方式,那你是如何考虑的?
Toby Ziegler :
是的。我想让网格成为图像的另一种图层,可能是让它浮现在图像最上层,让它接触到更多空气,并且制造更多波动。这或许指涉了现代主义中抽象艺术的网格,它们强化了绘画的表面。但同时,我想让它们多一些起伏波动、更加模糊化,使它们时而沉入图像内部,时而浮现出来。

Involuntary memory event, 2010, Oil on Canvas, 180.1 × 227.1 cm
Q:
有时候从你以艺术史的题材为切入点进行思考的动机,就已经引出了某种观念的有效性,但你在创作的结合中又特别强调一种绘画性,对此你是如何考虑的?
Toby Ziegler :
是的,肯定是。我同意格哈德·里希特的理论,也就是说,即使是把自己转化为机器、用机械化的手法来处理画面,还是会有某种人性化的东西渗透其中,内容也会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所以没错,我喜欢用手来创造它们,尽管有些时候,你需要以相当机械化的方式来展开工作。

Toby Ziegler, Surrogate, 2018, Oil on aluminium, 62 x 47 x 3 cm

Toby Ziegler, Laws of repetition, 2018, Oil on aluminium, 48 x 55 x 3 cm
这还是与速度有关。有时候,艺术家制作作品的速度也决定了观众观看作品的速度。人们会以不同的速度来观看以不同速度创作出来的作品局部。就像迭戈·委拉斯凯兹的绘画,你会意识到他用一种速度绘制人物的面孔,然后以另一种速度绘制背景,再以其他速度绘制服饰。在我的绘画中,这些图层的制作速度是相互关联和牵制的。
Q:
那你的绘画和雕塑都经过了数字化的过程,那彼此在观念表达上有什么不同?
Toby Ziegler :
在创作雕塑作品时,我通常以3D建模的方式开始工作。之前的3D模型总表现出一种多边形的特征,这在雕塑里尤为明显。而在新的雕塑中,我把它更进一步。通过使用模型,我模拟了3D打印的逻辑。因此,我认为制作多边形模型就像是在空间里安排点的位置。这是最简单的在空间中创造物体的方式——这些几何点在空间内创造出一层“皮肤”。而3D打印则以另一种方式在空间内确定点的位置,这和图层的概念有关。

Installation View, Enter Desire, Chisenhale Gallery, London, 2005

Installation View, The Alienation of Object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Kiasma, Helsinki, 2012
在制作这些新雕塑作品时,我会先构建虚拟模型,然后制作一系列模版,再以泥条由底部螺旋向上盘绕的方式制作陶土雕塑。这就像是把自己转化为人工的3D打印机。
这时,它们不再是多变形的。它们的原始模型是多变形,但在此之后我会采用泥条盘筑法来制陶,这是一种颇为古老的制陶方式,会生成类似于螺旋盘绕的器皿,但所应用的是新技术,也就是3D打印。盘绕泥条的过程是缓慢的,但我会刻意地打断这个节奏,留下一些手工的痕迹。



Slave, 2017
在这之后,我使用雷射扫描器扫描这些陶土雕塑。你必须从每个角度进行扫描,然后我再把它们重新输入计算机,并把它们重新转化为空间内的点,最后我把它们制作成3D打印的雕塑。
这一次,还是以螺旋盘旋的方式进行打印,只不过使用的是塑料材料——每一条都更细一些,像是意大利面。当然,现在这些雕塑要大得多,你需要画费很多时间打印这些大型雕塑。我在塔斯马尼亚展出的这件作品,用时一个月、甚至超过一个月时间,而且打印机每天24小时连续工作。然而,我感兴趣的是当这些打印机失效的时候,因为当它在盘绕这些热塑料时,有时会出现失败的状况。这些干扰因素正是我制作原始陶塑过程的缩影。

Installation views | Toby Ziegler: Your shadow rising | MONA, Tasmania
最后,我们把这些塑料模型浇铸成铝雕塑。这是因为我想让物体再次转化为液体,再把液体转化回固体,让它们再经历另一种速度。从盘旋的陶塑,到经历干扰形成的塑料盘绕雕塑,最后再从液体过渡至固体,直到所有这些以不同速制作的工序被压缩为一个独立物件。这个最终呈现的物体呈现出清晰的几何形态,它就像一块石头,你会想它是一层一层构建出来的,但你无法确定它究竟是沉积岩,还是火山岩。
Q:
从你的雕塑作品《Slave》(2017)等类似系列来看,都带有某种兼于具体事物之中的流动型,仿佛对一种传统雕塑的坚固性和持久性表现出了怀疑态度,对此你怎么想?
Toby Ziegler :
我不太确定,但我认为是。我想我早期的雕塑并不必然表现出暂时性,它们更像是一种“皮肤”,你能感觉到它们非常轻薄,就像是被充气然后膨胀起来的物体。我不想展现那种破碎的质感,但我想让观众感受到它们的内部空洞感。

Toby Ziegler, The human engine, 2018, Petg plastic and aluminium rivets, 280 x 176 x 79 cm, from the exhibition Your shadow rising, Museum of Old and New Art (MONA), Hobart, Australia. Photograph by Jesse Hunniford. © Toby Ziegler
在MONA新旧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中,我还呈现了另一件雕塑作品,我想把这两件作品相互并置,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一件作品表现出轻盈的质感,它用塑料制作而成,内部中空,并被悬挂在空中,你能感受到它是透明的,并且很轻。而另一件作品则是厚重的,让人感觉其制作过程非常漫长。我想展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悬浮着、几乎失去了物质性,另一个则是沉重的。
本次展览由三个雕塑元素构成——一件塑料的手,一件厚重的物体,以及一块我在塔斯马尼亚找到巨型火山石。我试图寻找塔斯马尼亚的采石场,然后找到了这块石头。由于它是火山石,所以它体现了熔岩冷却的速度——如果它以某种特定的速度冷却,就会形成这样的几何形态的石块。我觉得在展览里放一些有时间感的东西会很有趣。

Installation views | Toby Ziegler: Your shadow rising | MONA, Tasmania
Q:
为什么你在创作所有作品的过程中,都如此地强调制作的时间性?
Toby Ziegler :
我喜欢将对比强烈的事物并置呈现。我从12、13年前第一次在画廊举办展览开始,就把制作时间长、过程复杂的作品和简单的作品并置陈列。当时,我制作了一件巨型纸质十二面体,其木质框架也异常繁复,我还在这些日式糊纸表面上细心地用墨水绘制了细节复杂的几何形态画。而与此同时,我还在展览中展出了一件用半小时制作的小型纸质十二面体,它几乎完全不费力。对于绘画也是一样,我会用一个月来绘制原始绘画,然后用三分钟把它磨平。总之,我喜欢对这种悬殊的差距予以呈现。
在MONA新旧艺术博物馆中展出的一件两分钟长的影像作品中,我使用了自己打鼓的录音作为配乐。它是我上星期来这里之前才去录音室录制的。总是,我特别兴奋,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把表演的元素实时呈现出来,并使表演和绘画以这种对位的方式展开。
此外,这件录像还使用了反向图片搜索引擎,谷歌、必应、百度等等搜索引擎都有这个功能。搜索时,你不必输入文字,而是把图像拖进搜索框,然后搜索引擎会帮你找到相似的图像。如果这张图像在网络上还不存在,那么它会试图帮你检索看似相同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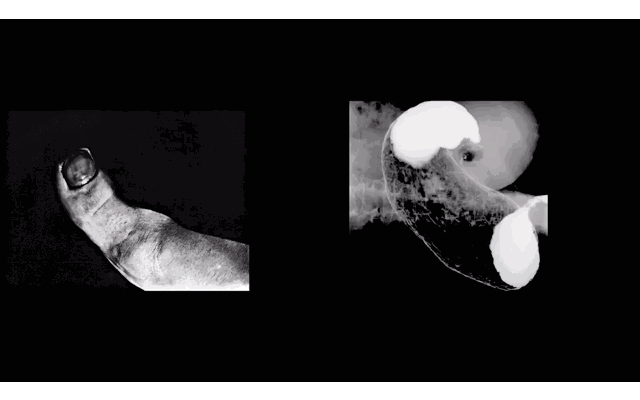
Toby Ziegler: It’ll soon be over (exquisite corpse), 2018,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Simon Lee Gallery.
这种名为“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人工智能操作使此类搜索成为可能。该技术还在不断发展,我制作这些视频已经有五年左右,而这种技术也变得越来越精细,它们开始像人类一样思考。卷积神经网络就像大脑神经元那样创造神经网络,它首先是识别图像的色彩,然后开始判断图像的结构,再对形状和不同物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试图辨认标志,比如鸟、树、车辆、脸庞。如今,这种搜索引擎能够识别出更加复杂的图像,它一直处于不断改进之中。
我还有很多作品想要展示…比如这件旧作,我使用了一幅马蒂斯的绘画,然后使它模糊化,再进行锐化处理。还有另一件作品,你能看出它是由单色画转化而来的。
Q:
这是不是还是在探讨今天在信息同质化功能下呈现出来的感受和结果?
Toby Ziegler :
这还是与认知、以及抽象和具象的观念有关,计算机试图将色彩和色调转化为具象的事物。

Toby Ziegler, VWV, 2018, Oil on aluminium, 125 x 95 x 3 cm
Q:
此次在Simon Lee Gallery 香港空间的个展,为什么为选取“慈母”这个标题,能整体谈谈它的叙事背景和线索吗?
Toby Ziegler :
我认为作品总是由普遍的经验出发,再转化为更加个人化的体验。比如,我的作品起源于互联网上的图像;这些图像经由我的处理,才从公共空间转入个人空间。因此,我不想称它为我的母亲,我更愿意说这是你的母亲。此外,英国小孩子在玩耍时如果想要辱骂对方,会先侮辱对方的妈妈——“你妈妈是肥婆”什么的…美国人对此好像有特定的称谓…总之,这件作品是对我母亲的纪念,同时也包含了更普遍的经验,甚至还带有某种戏谑感。

Toby Ziegler, The Grand Cause (2nd version), 2018, Oil on aluminium, 49 x 33.5 x 3 cm

Toby Ziegler, Scar tissue, 2018, Oil on aluminium, 73.5 x 62 x 3 cm
Q:
我们也知道这次展览的新作的主线索是取材自17世纪法国巴洛克画家Georges de la Tour的两幅画作,那引用这两张画后的你的两张作品,与展览中其他身体局部的画作有怎样的关联?
Toby Ziegler:
我想它表达了一定的抽象性,因为你需要处理这些形态。此外,这个短片名为《美艳僵尸,很快就好》,它源自于一种儿童游戏——一个小朋友画头,然后把纸折起来,其他小孩画出躯干和下肢。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也经常采用这种游戏,并把它称为“美艳僵尸”。我认为这件作品处理一些非常私密的体验,因为你需要想象一双脚、一对膝盖、或是某人的脖颈。而想象一个人的身体部位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当那个人离开时,你很难再回想起他们的膝盖。通过并置这些部位,我赋予了作品某种抽象性。
我认为失败是绘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