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保马 文:刘窗、陈玺安
Roger Zelazny在其小说《Lord of Light》(1967)中把一群试图通过改变对技术的态度进而改变社会的革命者称为“加速主义者”。这大概是“加速主义”此词的第一次露面。加速主义者把现代技术看作一股强大的力量,高度重视技术的价值,希望通过加速这种技术的发展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这种单纯对技术的推崇也导致了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并不是那么明确。加速主义也是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冲动”,自2010年起“加速主义”这个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并由此也衍生了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本文通过论述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实例,把“加速主义”这个概念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思考改革开放与加速主义的关系以及加速主义中国化的未来应当如何去做。
特区:一个改革加速主义的案例
1978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社会动员的最终结论,奠定了科技作为生产力的叙述。

对未来的热情
1978年,在为时两周的全国科学大会闭幕之前,播音员宣读了诗人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这场闭幕谈话实际上是由中宣部起草,带有浓厚的官方定调色彩,呼吁“科学家不应当把想象力让诗人独占了”。我们或可以将这看作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少有的科幻宣言。但除了短暂几年的复兴之外,改革开放后的科幻小说浪潮仍经常因不稳定的反右政治风向而起伏。近期的中国科幻热亦远非政治上的宽松所致,它伴随着对于中国的科技基础建设的速度以及对此的乐观主义而来。而今天的这种科技所强调的时间观,特别是近几年在中国兴起的对于人工智能及尖端科技等相关议题的热情,无非是对未来趋势的投资。在这个官方和大众的“共同事业”中,未来开始成为一个必要的计算对象,关乎未来的决定必须在此刻下手。
加速主义者对时间伦理的问题抱持着类似的肯定态度。用瑞伊·布雷西耶尔(Ray Brassier)的话来说,作为“物种共同体”的我们“应该要面对未来做些什么”[1]。加速主义这种技术至上的想法是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在二战后受人文思潮束缚的压抑后反弹(return of the repressed)。它体现为一种如下的欲望:将纯粹抽象的资本鬼舞重新编成一场锐舞狂欢,甚至成为机器种族的祖先[2]。这种加速主义和上述当代中国的“对未来的热情”两者的汇聚的早期文本也许是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还在华威大学哲学系时的表演讲座《熔毁》(1994):此一加速主义的早期文本描绘“远东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段富有启发性的突变:它“透过经济特区,将自身的唯物辩证主义的否定性咒语破除,并投入了脱缰的资本流动中”。当代中国“从未来而至”。相较之下,他反而认为西方传统左翼“沦落到保守主义的位置”[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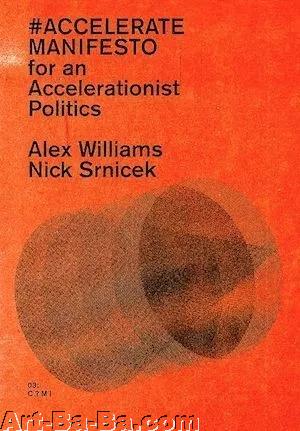
左翼加速主义的宣言书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要将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转译成赛博朋克式的修辞,牵涉到一系列简化的过程,用带有科技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视角将当代中国书写为一个“未来”的投射。尽管近期备受争议地卷入了极右运动,然而,这些理论和实践背后隐含的一种集体冲动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协商:在中国出现的这种非理论化的对未来热情,两者是否真有一种认识论上的相关性?
改革开放=加速主义?
加速主义者对技术保持着怎么样的本体论看法?布雷西耶尔在收录于《加速:加速主义读本》中的 “普罗米修斯主义及其批评者”一文中,借回应对于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评而回答了这个问题。普罗米修斯主义主张人为的工程可以改造人类的自然本性,同时,他们也不相信人和自然之间有什么既定的平衡关系。布雷西耶尔的看法是,西方现代性的时间轴线本身就是一种失衡的结构,我们不可能从局部进行修补,或接受“本体论意义上的有限性”(ontological finitude)的束缚。布雷西耶尔在这篇文章中对工程师及哲学家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对纳米伦理提出的疑问进行逐行细读。迪皮伊的论述认为,新的技术领域(即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科学)对认识论思辨(speculation)的追求已经失衡,进一步说,这个领域并没有分清楚思辨和存有学两者的差别。布雷西耶尔对此就哲学史的角度反驳道:存有学来自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先验(神的)范畴具体化(reification)为关于人的存有思考。布雷西耶尔为启蒙理性的遗产辩护,基于 “马克思对人类以自由意识重谱自身及世界的认同”,他主张道,这种尝试同样也是将先验问题具体化的实践。[4]
马克思要求哲学必须推动实践,当代中国本身正是这个信条的具体化。在20世纪的下半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被于光远等马克思主义者引介成为当代中国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参考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劳动通过科学认识和技术改造自然,来揭示自然界的整体性质以及自然历史的规律[5]。“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在执政之前便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促使他参与创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他被许多论者回顾式地视为加速主义者,其实质的形上学归因便是在于他的现代化方案具体化了技术的形上学基础,另一个加速主义征兆则源于改革开放“加速发展进程”的解疆域化事实。后者体现在其合资和特区等政策,它们提供了资本方廉价的自然资源和低廉劳动力等生产资料,以换取技术和资本进入中国。某种程度上,特区不仅仅是中国的“世界之窗”,而且还是世界各处资本的自然资源窗口。用布雷西耶的话来说,这种将自然与劳动力视为资源的特区,同样也是一种德勒兹和加塔里所说的“解疆域”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也许可以被我们诠释成一种哲学方案的修正,将神学修改成为人学,将形上学修改成资本政策的工具。

改革开放时期技术及认识论的转型案例
历史性地看,也许加速主义正是修正主义的压抑回返。在共产主义的改革主义星群中,铁托自50年代起以强人政治的风格实行工人自治,将南斯拉夫带离苏维埃式的计划经济;而赫鲁晓夫在苏联,则同步从政治体制上与生产力上进行改革,但在大型的危机中宣告失败。计划经济在转型时面对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将无产阶级革命能量安全转化为群众的生产冲动。修正主义是当时调动社会和政治动能的一则咒语:反修、防修。反过来说,各种修正主义的政治体制,不能说没有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治理方向:既不能落于赫鲁晓夫的政变结局,或者铁托的一人当政的局面。这意味者军事冷战和政治斗争的热力学积累,需要由下而上地导向通过追求科学技术和经济而带动发展的政治愿景里面。
在今天也许很难想象:转型最初的制度转变从农业开始。农民的生产冲动甚至值得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效仿军人立下生死状。1978年解除公社制度,并要求各自承包村内土地的政策,算是触碰了政治禁忌。运用责任制度的试点实验,并在成功以后扩大实施——这种弹性的政策强调法令和意识形态之外的特例。特区的规划则是另一种不均地理发展的政治建筑。从今天的角度看起来,划区一般被视为新自由主义为跨国资金解疆域的非地方,而在邓小平那里则源于1937年的陕甘宁特区。在国共合作的情势下,G。C。D的行政根据地被划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特区。邓小平在1978年开创这个制度外的空间,这和他1992年在没有任何官职下到上海、深圳等城市游击式地进行南巡讲话,并最终巩固了改革政策的延续,两者都是传统中国G。C。D擅长的不对称战争。若做个比较,1934年的长征最终走到了延安,战略上大后方的薄弱地带,而1980年的深圳,则是相对于将重工业设置在内陆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策逻辑之外找到的一片意识形态斗争的边疆。那也是改革开放之前,闲置劳动力逃港的路径。这个边缘地带让局部的试点免于被攻击为改革主义,并得以将市场经济写入红色长城星球之上。这个不均发展实际上也是种军事复合体,其实质手段是工程兵的基建和武装的关口。这些军事部署将基建对速度的追求,以及为换取外国资金和技术所进行的生产资料垄断进行了图绘。换句话说,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随处可被观察到的。[6]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1979年设立蛇口工业区的招商局起源于1872年的洋务运动,80年代初的舆论认为,这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的洋务运动。不同之处在于,中体西用的体系将技术的思考(体)和使用(用)拆开来本身就是个问题[7]。换句话说,单单注重军事武器硬件的改革,而不触及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技术的举措——合资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中体西用的创造性修正。当时的合资以技术及资金的引进为主,搁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问题(体),并着重在其实用层面(用)。改革开放时代的技术官僚必须小心处理合资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冲击,而不落入被批评为修正主义者。他们的内在目的和工具的论证体现在这样的想法上:共产主义若是目标,就要先忘掉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事实上,一些改革开放早期的技术官僚,也谈到计划经济之于技术创新的困局[8]。当时透过合资产业实际引进的技术,更多指的是民生工业的产业链。例如中德合资的大众汽车,便在80年代中于江浙沪一带,几乎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上百家标准化的零部件配套厂。[9]

何煌友,《深圳夏巴汽车装配厂》,1979
2004年出现的山寨手机浪潮在几年之间激起了晶片市场的重力转移。这股浪潮也许最佳地诠释了许煜所称的“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在这个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所主导的技术变革之前,中国的技术改革也许仅处在60年代起开始垂直整合的全球技术生产链末端,而没有跃升的契机。上述所谓垂直整合的技术,通常是指高科技产业运用自身不断更新的商业和生产模式,以及产品的升级做筹码,并支配全球各处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让它们的产品能在最有效生产的几个不同的地点进行模块化的组合。特区的出现,正如Silicon Valley Toxic Coalition的创办人Ted Smith所描述的那样,“其规划提供了促进及加速科技扩散进程的基础设施,并在地化了半导体公司间的垂直分工。”[10]

2008年,一名中国女工的在生产线上的照片不慎存入未销售的iPhone手机中,迅速在网上走红。当时iPhone主要由深圳的富士康代工厂生产,生产线上的工人大多为女性。
在这场劳力密集,并且是由硅谷(上)至深圳(下)的一场全球整合的技术革命中,核心技术一直是被各种政治和商业权力所垄断的。当然,这一现状还没有被山寨经济所改变,但可以说后者确实暂时打乱了技术原有的治理规则。将这种在技术上大量进行拟仿(technological mimicry)的经济用中文拼音的“shanzhai”命名,是将无监管、无核心技术的加速生产过程污名化为一个没有文化本质的生产无意识, 而这一污名化的现象源起于文化本体论的缺失,或许更值得我们讨论的是山寨经济为技术提出了什么不同的参考点[11]。
套用阿克巴·阿巴斯(Akbar Abbas)的说法,这场山寨变革可以说是“技术分工的底层对全球化过程的一种从技术、经济和文化角度发出的回应。”[12]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技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点。可以说,这次的技术和市场的竞争可以被称为是典型的“降维打击”[13]。在2004年之前,智能手机晶片设计的技术门槛及采购成本基本上被大型的国际IC设计公司所垄断。台湾的晶片公司联发科在台湾开始试验的一套一站式解决方案,则将芯片研发、软件设计及生产制程以整合的方式提供下游厂商采购,为深圳华强北为主的手机装配链提供了以少量、短周期的产品制作的可能性。即便2008年之后,深圳的产业政策引导了一次高科技的转型,让山寨文化过度到品牌文化。但在这里最重要的仍是技术的速度和经济成本。它体现在周边的生产车间的链条,让新创产品的研发能够一站式到位。这一对全球市占率的降维打击,关键在于劳力密集的末端装配链,以及配合智能手机普及化的人口消费需求。可以说,消费和生产的人口基数其实仍是能够改变技术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案例不断试图回答的也许并非人和技术的关系,而是如下的一个角度:技术和人的关系其实是由人口基数——作为消费力或者产能——所定义的。[14]我们也许可以暂时总结性的说,中国体现了其他非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典型案例:对速度的追求,同时更重要的也许是这种速度的追求同时是对规模的热情。尽管实际存在的加速主义基本上是枯燥无味的,好像是种没有文化的幻想,然而,对于规模的非人类幻想——将人抽象成为人口——则又在现存的各种当代中国的文化文本中随处可见。譬如近期以德国在2013年工业4.0模型的智能化制程作为蓝图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便声明工业制造是“国之重器”。这是一个将核电、大型基建的产能拓殖到其它国家的举措,同时也看得出来当代中国对规模的想象——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方式——是其思考工具和时间关系的切入点。
规模和同步的美学

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前历史展厅一处陈设,2017年。
一场改革开放常设展的典型叙事方式往往从改革开放前劳动力大逃港的景象开始;自80年代起,一整排流水线的场景也是很好复原的对象;三天盖出一层楼的国贸大厦施工场景图则占有最大的一个展厅空间。人口规模的指涉不仅仅是技术的参照点,还是博物馆展示的参照点。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其中一组2004年的复原场景,则是个对照性的装置。在展厅中,你会先看到八十年代工厂女工宿舍,外观看起来非常的简朴,几乎算是贫困。而一旁边展出的领导人的室内陈设也与此没有差别。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东西少的可怜。
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宣传,号召人民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这样一种展览很容易被来自对立的资本主义叙述模式所攻击,被说成是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悲惨写照。这在当时有关深圳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下,两种对立的解释都可以有效的激发出一种晦涩的爱国情操和牺牲精神。作为一种现代献祭,争论的最终结果就是把物质成就作为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深圳变成来一个激进改革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各种差异化极大的工业化模式在这里并行不悖,从19世纪可怕的工厂模式到后工业模式,同时,本地的宗祠活动依然活跃。不同时期的历史片断在这座特区城市被混合在一起。这里是一个活着的人类遗址,市民随着时间进步所脱下的残骸,即刻就在博物馆上新。而为历史贡献材料的人们,如果还没回乡的话,也都还生活在城市中。
失向
(dis-orientation)
中国未来的图景是什么?简单勾勒近年在中国的视觉文化领域发生的景象:许多自中国本土的科幻热开始的亚洲未来主义讨论以及展览,正无意间和新闻和投资领域内对AI以及科技奇点的期待组成一个带有技术乐观以及文化扩张倾向的声音。这些来自于中国的技术乐观论的未来探索声音会不会是一种单手击掌——亦即反思的缺席?
观察未来几年加速主义和中国知识圈的互动之所以重要,在于中国的体制本身就蕴含了加速主义那种脱离人道主义管束,以最大化资本和技术发展的议程若合符节。如果说,加速主义这种笔直穿越资本主义建制的提倡,在西方还有一种反思的论述将其左翼化,那么,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如何理解加速主义以及当代的失向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
这种失去参照方向的问题,不无谬误地体现在认为当代中国“从未来而至”,而让西方传统左翼看似沦落到保守主义位置这样的论调。[17]事实上,这种言论在当代中国不难获得广大的回响。传统政治光谱中的所谓自由派、代表“西方”的“政治正确”的一类价值观在近几年便经常被这种逆向全球化的影响力所挑战。
就技术哲学的角度而言,许煜如此描绘这种方向错乱(dis-orientation)之于东西文化、技术的原因:
同质化的过程带来了技术的汇聚和同步。过去三十余年,中国的技术哲学是对技术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成长的积极回应,然而,中国对技术的观点开始和西方同步,甚至让后者覆盖过前者,其实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症状[……]和西方(the Occident)的情况不同,东方(the Orient)被否定而不再作为东方。其结果是,东方也不再是西方可供参照的对象。〔文句顺序经过编排以适合上下文〕[18]
如果用第三章所列举的案例进一步阐述这种技术的全球同步观点,我们可以看到,2004年在深圳兴起的山寨手机浪潮,实际上是1960年代起硅谷硅晶片全球垂直生产链的某种黑暗版本的同步:它们共享相同的技术产业链,其存在都需要速度来维持。它们的差别仅仅在于被分配到不同的阶层上。而正是这种不同的阶层之间在规模和速度之间的竞争,进一步解构了原先的疆域,并形成同一技术产业链的亚文化,或者说是一种“修正”。
和颠覆传统政治的光谱的加速主义看似是政治论述领域中的亚文化不无相关——一般而言,亚文化意味着被主导的符号秩序压制的文化实体,而其突变的频率更为捉摸不定。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被压制的事物不会成为亚文化,它们会成为改革主义。改革主义和加速主义不无相似的一点在于其政治光谱难以被定义:比起与之竞逐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这些倡议往往表达了主流之外的另类选项,并带有一定程度的激进性质,反而在话语斗争中被指导性的话语划为右派。正是因为用既有的疆域来描绘这种突变中的情景,让我们无法清楚描述特区的政治和产业对既有事物秩序所进行的修正,导致了方向的混淆。在这个解疆域化之后的失向中重新寻找一种反思性(reflexivity)的提案,我们称之为改革加速主义。思考加速主义的重点也许不在于描绘技术奇点之后的景象;如果改革主义是加速主义的过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修正加速主义的方向。从这个视角看来,这种文化的失向并不是没有其方向性,它的坐标只是不断被资本所重新导向:在改革开放的渐增式回路中,资本的加速反馈端刚好都是政治斗争的边陲地带:深圳、上海。而它所激起的补偿效应,即其地缘政治和人文危机则在这个中心幅奏的外围区被引爆,例如计划经济的工业重镇如山西、东北,就在90年代遭到重挫。
这个将改革开放视为一场对于未来积极投资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工程的提案,并不是倡导一种中国的特殊性:这个提案应能在垂直整合的全球技术生产链的各个末端节点中找到不同的技术和美学的反思契机。并且,这些节点随着特区在全球范围的创设,而蔓延到全球超过3,500个特区之中[19]。
[1] Ray Brassier, “Promethea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R. Mackay and A. Avanessian, (Falmouth and Berlin: Urbanomic/Merve, 2014), 467-488.
[2] 二战的原子弹是技术至上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高点,最具有代表性的批评见:Günther Anders and Claude Eatherly, “Commandments in the Atomic Age”, in Burning Conscience: The case of the Hiroshima Pilot, Claude Eatherly, told in his letters to Günther Anders, (New York: Paragon, 1961), p. 11<https://aphelis.net/wp-content/uploads/2013/04/ANDERS_1957_Commandments_in_The_Atomic_Age.pdf>
[3] Nick Land, Fanged Noumena: Collected Writings 1987-2007, eds. Robin Mackay and Ray Brassier, Falmouth: Urbanomic & Sequence, 2011.
[4] Ray Brassier, “Promethea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s R. Mackay and A. Avanessian, (Falmouth and Berlin: Urbanomic/Merve, 2014), 477.
[5] 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193.
[6] 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
[7] 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8]见:傅家骥,《技术创新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孙冶方,《孙冶方选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9]见:马丁·波斯特,《上海1000天: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2008
[10] See: Ted Smith, “Preface to the Chinese readers”, Challenging the Chip: Labo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Industry, trans. Citizen of the Earth Foundation, Taipei: Socio. 36.。
[11]韩裔德国哲学家韓炳哲从文化–历史潜意识层面对此进行辩解。他将山寨视为古典中国的临摹传统的当代延伸。但本文更着重以唯物角度思考这个现象的技术本质。见:Byung-Chul Han, Shanzhai: D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Trans. Philippa Hurd, Cambridge: MIT, 2017.
[12] Ackbar Abbas, “Theory of the fake,” in HK Lab, Laurent Gutierrez, Ezio Manzini, and Valérie Portefaix (eds.) (Hong Kong: Map Book Publishers, 2002), 312–23.
[13]降维打击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描述太阳系遭受二向箔攻击化为二维世界的毁灭性外星技术:“如果人类适应了三维,去掉一个维度,进入了二维世界,那么人类就会因为缺少了原来所适应的一个维度,而无法生存。”而用“降维打击”的说法描述企业竞争改变游戏规则的案例,则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开始大量流通。
[14]实际上,包括改革开放当时启用的技术官僚中,也有抱持从人口规模的角度理解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认为传统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西方现代化的技术,在于前现代的技术发展以经验为基础,因此主要决定因素在于人口规模,而缺乏以科学和实验为主导的工具理性精神。见吴敬琏文集
[15]在1988年开馆时就有了“今日深圳”的常设展。
[16] Xin Wang, “Asian Futurism and the Non-Other”, in e-flux Journal #81, New York: e-flux, 2017.
[17] Nick Land, Fanged Noumena: Collected Writings 1987-2007, eds. Robin Mackay and Ray Brassier, Falmouth: Urbanomic & Sequence, 2011.
[18] Yuk Hui,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 Falmouth: Urbanomic, 2016. 许煜在这本著作中试图为今天的“对未来的热情”提出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想要为当代的全球社会中高度同质化的技术–时间思维找到一个矛盾点,就必须要有一个与这种技术只是对未来资源的掠夺这种高科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技术想象。他用寻找一种“宇宙技术”来概括这种差异技术哲学的探索。即各个文化中以有机的态度面对技术与自然之间平衡关系的不同哲学历史。他的论述着重这种对于技术的思考被整合成“全球同步”之前的技术想象,而本文的视角则着重于:如何描绘这种当代中国的“对速度的热情”背后实际上抱持的意识形态:即一种加速主义热情。
[19]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截至2006年位置,130个国家中就有超过3,500个特区。转引自:Keller Easterling, 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 London: Verso,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