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王家北
碎片化的事件潮流——2017年度盘点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
种种事件快速地产生、发酵
又迅速地被人忘却
2017年,中国与西方的艺术问题仍然彼此隔离与滞后
而此时此地的中国艺术
又有何浮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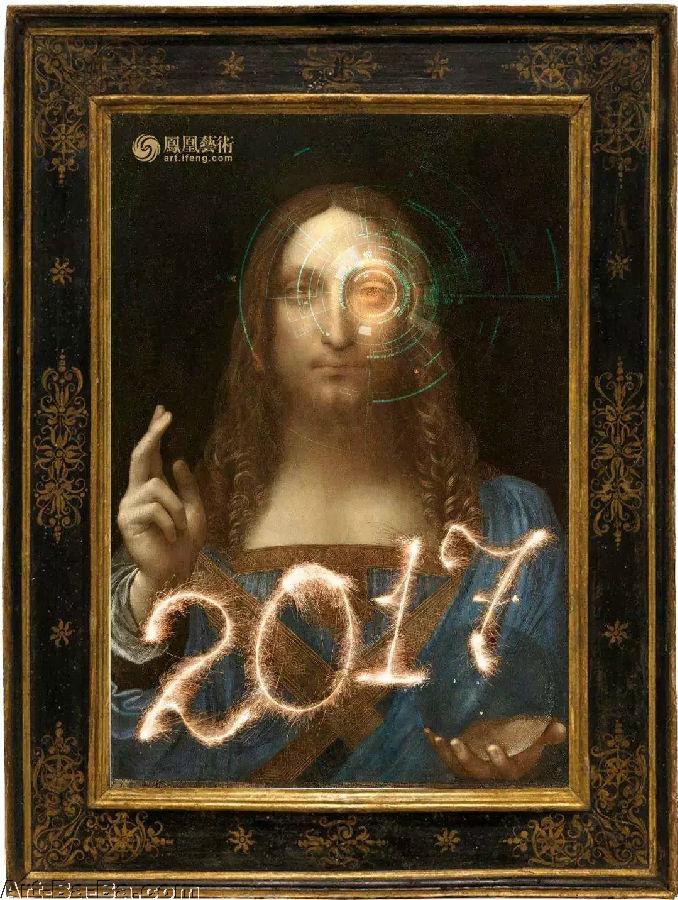
啊!媒介!
媒介即信息。这位提出了“地球村”概念,在今年七月刚刚被谷歌选入Doodle纪念的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或许不会想到,数十年前他所写下的这句话,在当下中国开始近乎无限地发酵。继被称为“VR元年”的2016年后,以“新媒介”、“超媒介”、“新媒体”、“多媒体”等词语所命名的展览在2017年遍布全国大小艺术机构,掀起全民媒介的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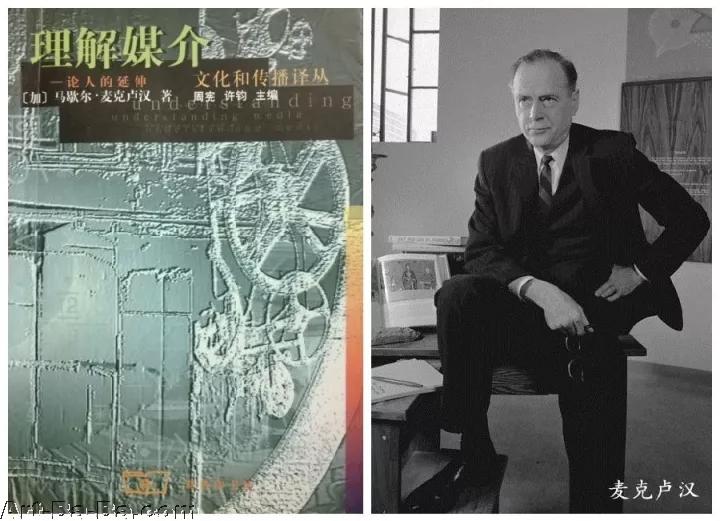
民营美术馆和商业画廊,独立艺术机构和购物商场,国营美术馆和大大小小的博览会,学院和企业......如果哪里在今年没有做过几场与新媒介有关的活动与展览,似乎就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浪潮中。而与过往较为纯粹的艺术家为作品主导不同的是,它们在新的一年中愈加呈现了商业性、娱乐性、大众性与参与性的特征,teamLab更是斩获了近3000万的门票收入,Zip展也随后斩获几百万的收入。
但大家都在试图“转型”的同时,是否所有以“新媒介”为名的展览与作品都具有艺术的“合法性”?它们是否真的“非此媒介不能呈现”?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科技和艺术的关系究竟如何?不同领域间的协作又面临着何种境遇?新型的“数字艺术”又具备哪些品质和特征?在“凤凰艺术”2017年终盘点系列中,本篇将对这些问题予以叙述与梳理。同时,在接下来的几天,“凤凰艺术”也将为您带来其它角度的中国艺术年终盘点。
无处不媒介,万物皆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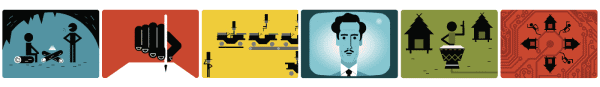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艺术与科学(新媒介)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容易,是因为新算法以及科学本身已经成为我们用来体验及描述现实的普遍手段和方法。手机、屏幕、网络与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被不断传播的跨学科知识已经成功地让我们步入“后人类”时代,而曾经过往的任何生产与组织模式,也都在被不断改变与背叛——冲突因此异常直观地出现在每个人的身边,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同夹着筷子等上菜一般唾手可得——于是,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们再一次扑入参与辨别谬误的浪潮中,在创造多元解决方案的同时,甚至试图成为一名伦理学家。
这一浪潮与如今完全的数字化生活密不可分,当下与以往产生本质差别并不是技术媒介更新迭代所直接导致,而是来源于因技术而改变的社会生产与认知交流模式,在经历了多年发酵后,终于以成熟的商业及交互机制构成了每个当代人的生活碎片。“互联网能够提供给艺术家的,并不仅仅是更新的数码多媒体技术,更是它所建造的这个遍及全球的互动信息网络(盛葳)”。而当创作媒介具备的能量超过其曾经被人习以为常的阈值,打破人的心理预期,并迫使创作者与接受者以一种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方式与观念面对艺术作品时,媒介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一种改变了人们的认识习惯与生活方式,从而再创造了一种独属于这一媒介的逻辑脉络。而在这一层面上,人作为主体延伸了媒介,媒介也同样延伸了人。

如开篇图片中救世主头部的虚拟眼镜所指,“虚拟与现实”成为新的一年中不断被提及的母题。其不只包含了现实之于虚拟,同样在提问虚拟之于现实。当跨越边界的技术媒介细无声地来到我们身边时,它同时对现实和虚拟、物质与精神这两大时空进行拷问:未来考古、网络信息与安全、主体性、虚拟生产、反媒介、现实转变、新算法,以及观看、数字伦理、技术政治与身份转变等成为作品中常常出现讨论对象。
认为虚拟现实是未来趋势的一个重要依据是:2017年几乎全部值得点赞的影片都属于虚拟世界——从高司令的后现代赛博世界到银河系星球大战;从外星异形到星际特工;包括两只著名的猩猩金刚和凯撒。人类想逃避现实的欲望填满了整整一年,从星际蔓延到原始丛林都不够空间装载。

▲ 银翼杀手2049
事实上,“新媒体艺术”自上世纪末起在全球范围内已兴起数十年,这甚至使得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了“旧词”。在这个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艺术”或“Science Art”成为了更加准确并经过“更新”的词语。而在今年,大量相关的展览、出版物与讲座沙龙等空前爆发,提供类似课程的大学似乎翻了一番。政治、经济为其提供了动力与目标——商业公司受资本驱动,需要更加敏感地寻求风口与创新;诸多国家也将高精尖技术及人工智能列为新的一年发展重地。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国家,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策略,具有强烈与新技术结合的需求。而就个体而言,愈来愈多进入生活的技术材料及其带来的可能性与特殊性加速推动着艺术家们的工作与思考。但在爆发的热闹背后,与“数字艺术”相关的当代批评却始终不温不火,学者们仍然还追随着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的脚步。同时,其作为一种“艺术流派”的概念仍然是不明确的,更多作为一种弥散的现象而产生,或是一种对于科技巨头们开发平台竞赛产物的迷恋与追随。

以“XX”(多媒体、新媒体、新媒介、超媒介、科技、高精尖...)+“艺术”进行命名,人们或许可能会认为它是这两个领域的某种总和,但其对于艺术的极大倾向和热情却明确地指向了某种不平衡。除此之外,即便这两个领域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丰富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对无形揭示的渴望)以及它们明显的原始统一性,但不可逾越的事实是,这两者代表了相当不同的认识论方法:一个渴望客观的知识,另一个的意义来自隐性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一方面,科学要求的准确性、精确性和推理性原则是不可或缺的,这也却往往会使协作变得僵化,而不是依靠某种本体力量的模糊性、多元性和内在矛盾。
于是,这两部分如何在综合中保持完整?“艺术与科技融合”的说法是否真的是两个领域的合成,还是更像是互补或对立关系?在艺术方面,收获是显而易见的:凭借其丰富的图像,科学(新技术和更多的幻想发现)作为无尽资源被艺术家们索取、呈现。但在另一方面,审美化的信息不是艺术,对于某些现象、定理的视觉化展示在某种程度上也略显肤浅——更不用说许多对于其它领域思索的转嫁是滞后的,而成为一种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轻易忽悠观者的套路。
而另一种风险在于,过于简单的思考和过于追求终极视觉效果的数字艺术作品同样容易陷入“炫技”和形式至上的境地,甚至仅仅成为简单的为视觉效果服务的小型工程技术。在某种程度上,自电子时代以降,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家们越来越难以通过个人思考担任引领时代的任务,而是不得不被科技裹挟,甚至常常落后于它者:商业技术与小说电影等。在此基础上,诸多仅仅是与所谓“新媒介”沾边的数字艺术,或是装腔作势的作品内核,并不足以让艺术家们仅仅将此进行简单加工就可以获得作品的“合法性”。

有意思的是,如果工业时代被看作是祛魅的时代,本雅明笔下的“灵光”或是“气息”因大规模集体生产消失殆尽;那么,数字时代似乎成为了赋魅的时代,在虚拟与现实生产的模糊中,灵光于此重新聚集,形而上的终极问题被重新提出与解答: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分解与重组,而当它与艺术这两个视角和实践上有所不同的学科形成伙伴关系时,它们的分歧却可以成为接近思想的力量。换句话说,并不是艺术与科技的融合,而是技术改变及其背后所改变的一整套系统成为背景,在痛感与矛盾中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艺术的形态与意识。
新的情感与思想结构

媒介的变化同时还产生了一种新情感与思想结构。2010年提莫休斯·佛牟伦(Timotheus Vermeulen)和罗宾·凡·登·埃克(Robin van den Akker)发表了《Metamodernism Notes》一文,认为由于诸多原因,后现代主义已然渐渐退却,一个新的情感与思想结构进入舞台:混沌现代主义(Metamodernism)。他们认为,再也不能用后现代主义范式来理解新趋势了,因为它们暗示了当今时代某种新的情感结构,其特点便是在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担当精神和后现代主义的超脱姿态之间摇摆不定,同时每个人也具有身份和生活方式的不确定性,在观看艺术创作中也可明显感受出这一趋势。7年过去,网络对于混沌现代主义的映射关系愈发明显,在改变认知与感知的过程中,甚至极大改变了“人”这一主体。
在线 & 无限
就数字化生存时代本质而言,“在线”与“无限”是描述它的最佳词汇,而愈加多元化、国际化的创作身份与创作风格,亦或是碎片化的知识结构与生存状况,则是其注脚与表现。无论何时何地,眼前的小小屏幕都会在为使用者便捷地提供神经感官“前往它时它地”的可能性。此时,人们在数字世界中“在线”并精神十足,但在屏幕外,却是迟缓又淡漠的“不在线”——这种淡漠是“混沌现代主义”下的情感本质,同时也是艺术“不再那么打动人”的心理基础。而在这一世界中,一切信息都在无始无终中存在,每个人都只是其中一个节点,“作者之死”在此时更加显得无比正确。
而体验性与娱乐性则是文化资本主义的最佳策略。当代艺术家通过当今数字化时代衍生、激活出的大众媒体、消费主义和前沿科技的热情与活力,无时无刻不向人们的五感渗透着讯息。而在同时,观者也似乎相信通过自己的观看与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作品——“互动性”和“沉浸式参与感”成为混沌现代中最为重要和流行的作品特征之一。雨屋、詹姆斯·特瑞尔、teamLab数字花园、【.zip未来的狂想】科技展和无限镜屋展览们,在聚集巨大人气的同时也因此获得了高昂的门票收入,同时作为巡回展在各个国家与城市间“攻城略地”。


▲ 火热的沉浸式艺术展
但在同时,正是由于这一消费主义时代对于视觉感官享受的趋向性,不但让艺术容易陷入精满足神感官抚慰与刺激的泥淖,还使得新技术产生、应用与未来的敏感性更多出现在科技与商业巨头企业的身上——三星手机的发布会可以被看作更加充满未来感的沉浸式展览,苹果与谷歌的种种超现实体验则是某种交互式的新媒体作品,更不用说社交媒体巨头们更加清楚人类的生存现状与需求——“数字艺术”在还未出生之时,就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所消化容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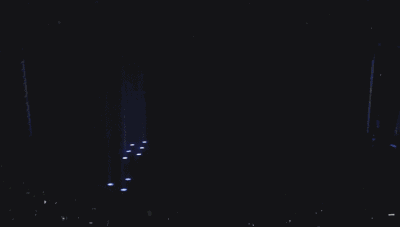

▲ 三星note8发布会
此外,信息和刺激过剩带来的迟缓和淡漠,以及饮鸩止渴般寻求刺激的情感状态——同样是如今沉浸式艺术展火热的共谋与补偿。这不仅是因为曾经的“虚拟”变得愈加具象化使人产生了某种刺激与焦虑,也同样也在喻示着当科技与人工智能不断地使人类产生着某种虚妄的挫败感时,感知及其所带来的乐趣——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再度被树立为那一根声明着人作为独立主体的“芦苇”。
新媒介的迭新在对旧媒介进行挑战的同时,也为其创造了新生命的可能性。在此语境下,过往的艺术形式从古典形态中走出,并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义。但此处需要厘清的是,数字时代的新型艺术并不意味着数字化技术是其必不可少的媒介。如同几年前火热的“互联网思维”一般,并不是简单地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企业运营便是具有了互联网思维。因此,在这个数字化生存时代,我们认为“媒体艺术”只是其表象,科学技术作为众多认识方式之一,形式应远远让位于内容。如果仅仅将新媒介作为展示工具的变化,而不是“非此媒介不能呈现”,形式上似乎成立的“新技术”并不能掩盖其新瓶装旧酒的本质。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是,即便我们处在某个浪潮的初期,但全心追求新事物、新媒介并不是完全的开放——这可能是另一种闭塞,它还应包含对旧事物的理解。而如文章开头所说,肤浅地追寻视觉表现有着故弄玄虚的嫌疑,在“猎奇”与“尝鲜”背后,如果在其中不产生对于本质问题的有效追问,所谓的“多媒体艺术”也只能如同商业行画一般毫无价值。数字时代的情绪与生存状态才应是“数字艺术”最为本质的表达要素,而文化的传统性与在地性同样也是在0和1中区分彼此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葛宇路的路牌作品可以被看作比一些肤浅的媒介作品更符合数字时代的特征。
同样不能忽视的还有虚拟状态下肉体的现实性以及对人性的关照——虚拟技术给予人们超脱现实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就此放弃关注人的现实处境——如今人们的肉体越来越不具备功能性、癌症愈加增多,而网络的无限自由也同时带来了世界各国愈加紧缩的政策状态。

麦克卢汉在1969年接受《花花公子》专访时曾如此说道:“我们盯着后视镜看现在,倒退着走向未来。”科技、艺术与肉体,成为了新时代的“三位一体”,在成为了一种潮流的同时,也在不断敲响着联结过去与未来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