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保马
什么是左翼?
作者: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译者:刘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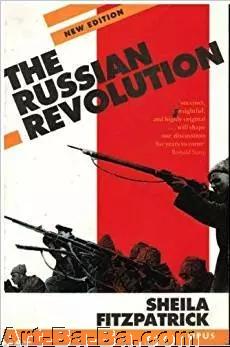
2017年是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对近年来关于十月革命的多篇著作给予了介绍,它们可以说是关于十月革命的最新研究成果。相比于冷战时期的研究,这些研究过于强调革命发生的偶然性,关注焦点也由工人阶级转向了女性、农民、帝国和“街头政治”等主题。去政治化的思维主导了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这也可以作为政治与学术关系的注脚。十月革命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这不仅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价和反思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还映射出我们对于今天资本主义的态度:是依然沉浸在它编织的神话中之中,还是去寻找新的道路?
原文标题为what is the left?, 作者为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首发《伦敦书评》2017年3月号。
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来说,在他出生那一年爆发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核心事件。它对于世界的实际影响,比一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更为深远,更具全球意义”:“在列宁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之后,仅仅用了三十到四十年,三分之一的人类便发现他们生活在由(革命)缔造的政权……以及列宁式的组织模式,共~产`主~义~政~党~之下”。在1991年以前,这曾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甚至在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学家们看来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和霍布斯鲍姆立场不同。然而在1990年代初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完成之时,他提醒我们,他为之立传的世纪是从1914年到1991年的“短”20世纪,这个经由俄国革命塑造的世界也就是“在1980年代末走向崩溃的世界”——简言之,是一个失却的世界,如今它已让位于一个我们再也无法辨识其轮廓的后20世纪的世界。俄国革命在新的时代中将被置于何处,这个二十年前困扰着霍布斯鲍姆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生活在苏维埃体系下的“三分之一的人类”,在1989-1991年以前就已经戏剧性地缩减了。到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的2017年,世界上共`产`主`义政权的数量不过屈指可数,中国的身份模糊难辨,只有朝鲜仍然坚持旧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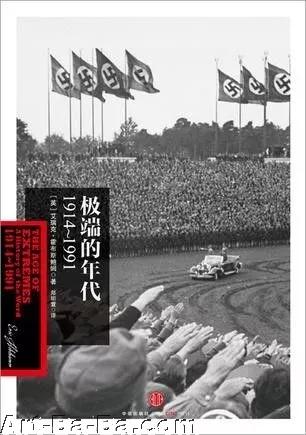
没有什么比失败更令人失望,对临近这场革命的百年纪念的历史学家们来说,苏联的消失给这场纪念投上了阴影。在一系列讨论这场革命的新书中,几乎没有著作去捍卫它那值得坚守的意义,大多数著作都染上了一种愧疚的腔调。托尼·布伦顿称它像印加帝国一样,是“历史”的伟大的死胡同中可能的一条:这代表了新的共识。此外,剥去了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宏大的历史必然性,这场革命看起来或多或少像是一场意外。工人们——记得人们曾激烈地争论这能否算是一场工人革命——被女人和帝国边陲的非俄国人推离了舞台。社会主义像极了一座海市蜃楼,以至于我们还是不提为妙。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俄国革命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最令人沮丧的教训就是革命通常会帮倒忙,特别是在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俄国。
尽管我在极大程度上赞同这一共识,但我对这种共识还是有着不同意见。拙作《俄国革命》(初版于1982年,修订版将于今年面世)总是严酷地对待工人革命和历史必然性,并且给出了超越政治斗争的观点(提醒读者,我在冷战时期写出了原始版本,那时仍然还有一场政治斗争等待被超越)。所以,我并非天生是一名革命狂热分子。但是,难道不该有人这样做吗?
这个人就是希纳·米耶维尔(China Miéville),他作为一名同情左翼的科幻小说家而广为人知,他称自己的小说是“古怪的”。米耶维尔不是一名历史学家,但是他做得不赖,并且他的《十月》(October)非但不“古怪”、反而构思精巧,出人意料地感动人心。他着手并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功的事,就是为那些同情一般的革命、尤其是同情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人们写作了一篇关于1917年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当然,米耶维尔像其他人一样,承认一切都以悲剧收场了,因为各国革命的失败和俄国革命的早熟,历史的结果是“斯大林主义:一个猜疑、暴行、谋杀和媚俗的警察国家”。但是这并未使他对革命绝望,哪怕他的希望是以极端有限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这个世界的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值得庆祝,他写道,因为“改变只要有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对真正少数派的诉求而言又是怎样呢?)。“自由”的曦光短暂地闪耀过,虽然它“本来将成为一场日出,[最终却变成了]一场日落。”但它本可以不同于俄国革命,“既然它尚未完成,那就由我们来完成。”
马克·斯坦伯格是唯一一位在书写这场革命时坦露留恋之情的专业历史学家。当然,革命的唯心主义和向着未知的大胆跃进易于导致硬着陆,但是,斯坦伯格写道,“我承认发现这一点令人相当难过。但我仍钦佩那些无论如何都仍要跃进的人。”然而即便是斯坦伯格——他对1917年的生活经验的研究大量基于同时代的大众印刷物和第一人称报告,是近来的书籍中最为新鲜的一本——也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他早先对工人的兴趣,转而偏向另一些社会“空间”:女性、农民、帝国和“街头政治”。
想了解当下关于俄国革命的学术共识,我们需要回顾一些旧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其必然性的部分。对斯坦伯格来说,必然性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的同时代的微观视角足以让这个故事充满惊喜。其他的作者则竭力告诉我们,革命的这些结果绝非注定,事情原本可能有不同的走向。“沙皇专制和临时政府的崩溃没有命定的因素,”斯蒂芬·史密斯在他那冷静的、深入又全面的历史研究中写道。西恩·麦克米金支持这一点,证明“1917年的一连串事件充满了其他的可能和错过的机遇”,与此同时,他恭敬地表明了谁是他知识上的敌人:这些事件绝非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可避免地联系着的末世论式的“阶级斗争”。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们,西方的和苏联的,全都错了。
《历史的必然?》这一文集通过直接提出一系列革命的关键时刻“如果……会怎样”的猜想,讨论了必然性的问题。在导言中托尼·布伦顿问:“事情本来会有不同的走向吗?会有这样一些时刻,某个决定被以另一种方式做出,一个随机发生的意外,一次本来打偏的射击打中了……会改变俄罗斯、欧洲以至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吗?”但当多米尼克·利芬写道“没有什么比坚信历史趋向不可避免更为致命了”时,他无疑表达了本书多数讨论者的心声。的确,那些讨论者认为偶然性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比在后十月革命朝向恐怖和独裁的道路上更为重要。奥兰多·菲格斯——著有流传广泛的革命研究著作《人民的悲剧》(1996)——提供了一篇生动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如果伪装后的列宁没有获准参加十月二十四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历史将会截然不同。”
关于苏维埃历史,有形形色色的政治论争。首先是关于旧制度的崩溃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必然性问题。这是一桩关于信仰的老问题,它曾在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俄国移民的历史学家那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他们在现代化和自由化的进程中看待沙皇制,这一进程被一战打断,进而将这个国家投入了混乱中,并且使得原本难以想象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成为可能(在本书一篇深刻的论文中,利芬将对1914年俄国社会状况的这一阐释描述为“极富智慧的思考”)。过去关于这场革命的苏联学论争的语境中,提出有关必然性的问题,不仅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被视为亲苏联的观点。因为这种问题相当于说苏维埃政权是“合法的”。相反,偶然性在冷战期间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除了一种情况,即成问题的偶然性令人费解地用在描述革命的斯大林主义结局、而不是用在其开端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中传统观点认为,极权主义的结局是必然的。菲格斯持有相同观点:尽管偶然性在1917年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十月起义和布尔什维克专政建立,到红色恐怖和内战,在苏维埃政权演变的所有结果中,贯穿着着一条历史必然性的线索。”
在对整个 “如果……会怎样”的史学体裁的一场抨击中,理查德 J.埃文斯指出,“事实上,……反设事实这一方式已经或多或少为右翼所垄断”,而他们的攻击目标正是马克思主义。尽管埃文斯的这一评价涵盖了一些右翼政治历史学家如理查德·派普斯,并且将所有研究1917年的重要的美国社会史学者——他们都曾在1970年代的怨毒的史学争论中反对派普斯——排除此列,但这一评价对布伦顿的书来说却未必正确。布伦顿是一名前外交官,《历史的必然?》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为了许多、许多[革命的]受害者,去追问我们是否曾有可能找到其它的路”——不失可爱地表明了外交官解决现实问题的癖好,这与专业历史学家分析问题的习惯恰恰相反。
派普斯曾于1980年代早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里根的苏联问题专家,1990年间他写过一本讨论十月革命的书,该书强硬地指摘布尔什维克统治得位不正。他的观点不止针对苏联,而且针对国内的修正主义者,尤其是一群年轻的美国学者,其中主要是对劳工史有着特殊兴趣的社会史学者,他们从1970年代起就反对将十月革命描述为一场“政变”,认为在1917年六月到十月这关键的几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党日益得到拥护,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拥护。由于新建立的美英学生官方交流活动,美国的修正主义者得以接触苏联档案馆的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帮助下,他们的著作对1917年的历史做出了详实的研究;这些著作得到了该领域多数研究的高度重视。但是派普斯实际上却将其视为苏联的傀儡,蔑视他们的著作,以至于甚至违反学术惯例,拒绝在他的参考文献中承认其存在。
1970年代,历史学家对俄国工人阶级这一研究对象有着浓厚兴趣。这不止因为社会史在当时的学界正值时髦,劳工史又是一个颇受欢迎的次领域,而且因为其政治意味:布尔什维克党真的得到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如其声称的那样代表无产阶级执政吗?派普斯所蔑视的众多研究俄国社会和劳工史的西方修正主义著作都关注工人的阶级意识,考察它是否是革命的;这些研究者只有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无视阶级意识,只写向上的阶级流动,对此我很反感。)
与此相关,这些百年纪念的书的作者,对这段历史都有着自己的历史书写。史密斯的第一部著作,《红色彼得格勒》(1983),迎合了劳工史的评价量规,尽管他作为一位英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美国的争斗,他的作品却总是过于小心谨慎,不允许任何含有政治偏见的暗示出现;他接着写出了一部杰出但未受重视的研究著作——《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与人民:一部比较史》(2008)。在本书中,工人和工人运动继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下一代的一位美国学者斯坦伯格,在2002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论工人阶级意识的书《无产阶级想象》,其时社会史已经发生了“文化转向”,新的重点落在了主体性上,对“硬”社会经济数据的兴趣减弱了。然而,这多少已是关于俄国革命的论著中为工人阶级所做的最后的欢呼了。派普斯彻底地拒绝了这一点,他主张革命可以只从政治层面解释。菲格斯在他广为流传的《人民的悲剧》中关注社会多于政治,但他却忽略“有意识的”工人的作用,反而强调失业的无产阶级在街头暴乱、搞破坏。在史密斯和斯坦伯格的最新著作中,他们都一反常态地对工人主题保持沉默,尽管街头犯罪已经进入了他们的研究视野。
麦克米金,是这些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开始写作一部“新的历史”,此处他是指一部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麦克米金追随派普斯,但有着他自己的偏移,他罗列了一个广泛的参考书目,包括“引用或有益参考”的作品,其中忽略了菲格斯以外的全部社会史学者。这个书目包括史密斯和斯坦伯格的早期著作,也包括我的《俄国革命》(尽管它在第12页中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影响下的作品例证被引用的)。或许可以说,麦克米金不必阅读社会史,因为正如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一样,他在《俄国革命》中关注的东西,是政治、外交、军事和国际经济等方面。他利用了多国档案馆的资源库,此书在细节上也饶有趣味,经济部分特别如此。但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最大限度派的社会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是当前真实的威胁,这种观念带有着一丝右翼的狂热。他并没有把整个革命——从1917年4月列宁的密封车厢到1922年拉帕洛条约——称作德国的阴谋,但这种观点或多或少暗含于他的叙述之中。
人们为他们的革命史选择的终点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他们对“革命真正是什么”的假设。拉帕洛对麦克米金来说是一个合适的终点。对米耶维尔来说,终点是1917年10月(革命的凯旋);对斯坦伯格来说,是1921年(不是内战的胜利,而是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作为一个开放性终结,此时革命事业尚未完成);对于史密斯,则是1928年。史密斯的观点从叙事剧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选择,因为它意味着史密斯的书要用两整章结束1920年代,在这一年代,革命在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暂停了,经济崩溃使俄国不得不采取这一政策,从国内战争时期的最大限度派目标中撤退。的确,类似于新经济政策之类的路线或许会成为俄国革命的结局,但它实际上没有,因为斯大林出现了。尽管这两个论新经济政策的章节和本书的其余部分一样,思考成熟并且研究扎实,但作为终章,它更像一声呜咽而不是一声巨响。
这将我们引向苏联历史上的另一个高度争议的问题:从俄国/列宁革命到斯大林,其间是否有着本质上的连续性,或者说在1928年前后,两者之间是否出现了一种根本上的断裂。拙作《俄国革命》列入了1930年代初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及这十年末期的大清洗,但许多反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可这一观点。(这并不奇怪,米耶维尔的注释文献认为这一观点“是有价值的……尽管它不具说服力地服务于一种由列宁走向斯大林主义的‘必然论’的视角”。)在研究1917年的社会历史学者中,史密斯的支持者采取了和米耶维尔大体相同的观点,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致力于使革命免受斯大林主义的污染;但在这本书中的许多问题上,史密斯都拒绝采取一种断然的立场。他指出,斯大林当然认为自己是一名列宁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列宁如果还活着,或许不会做得如此粗暴。斯大林1928-31年的“重大突破”“完全配得上‘革命’这个词,因为相比于十月革命,它更为深层地改变了经济的、社会关系的和文化的模式”,并且它证明了“革命的能量”尚未耗尽。尽管如此,在史密斯看来,它却是一个尾声,而不是俄国革命的一个内在部分。
公正是史密斯这本可靠、权威的著作的显著特征,我不安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公正地对待它的许多优良品质。事实上它唯一的问题——也是这场百年纪念中出版的诸多著作的问题——是没有交待清楚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写作,这也许要除开出版商的委托。在近期的一关于俄国革命的研讨会上,他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时代对革命的观念尤其地不友好……我是说尽管我们关于俄国革命和内战的知识大大地增长了,但在关键的方面,我们却很难理解——确切地说是感同身受——1917年的革命抱负了。”其他与会者也有着类似的悲观情绪,俄罗斯历 史学家鲍里斯·科洛尼茨基指出,在1970年代的列宁格勒,发现俄国革命的真相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人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趣“正在急剧下降”。“有时我在想,现在谁还会关心俄国革命呢?”斯坦伯格悲观地说,而史密斯却在他的《革命俄国》的第一页上写道,“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向全球资本主义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仍在回响着(虽然是微弱的回响)。”
*
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经过了1970年代由冷战煽动的论争的亢奋期,1917年革命在近几十年已经被搁置一旁了。曾有段时期,人们会给晚期帝国时代贴上“革命准备时期”的标签,有趣的是,人们只有在晚期帝国时代引发了革命后果时才会这样做。这样的日子已经远去了。改变始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当时俄罗斯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学者开始探寻一切有趣却与革命爆发没有必然关联的东西,从犯罪,通俗文学,到教会。随着1991年苏维埃联盟的解体,革命作为历史研究的主题萎缩了,这又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浮出水面。此前,这场战争对俄国的意义(与对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意义相反)显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同一场解体,又通过剔除苏维埃联盟中的非俄罗斯共和国,将帝国和边疆的问题放到了台面上(因而史密斯的副标题是“一个危机中的帝国”,而斯坦伯格著有章节“克服帝国”)。
在1960年代,俄国革命的重要性对于E.H.卡尔,以及他的对手伦纳德·夏皮罗来说,是不证自明的。对夏皮罗而言,这是因为俄国革命对俄国施加了一种新的暴政,这种暴政威胁到了自由世界。对于卡尔来说,这是因为俄国革命首创了中央集权国家计划经济,他将这一模式视为未来经济模式的先兆。1970年代的主题,我总结为:一边是托洛茨基和一干人等所指摘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数“背叛”,另一边是在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领域取得的大量成就,特别是1930年代国家支持下快速的工业化。霍布斯鲍姆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上持有相同观点,他注意到“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个根本上是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转换的规划。”现代化的观点对我来说仍然正确,但是面对如下的事实,它已经变得陈旧了:即从经济角度考量,它是一种看起来不再现代的现代化。除了在一个讨论环境污染的语境里,如今谁还关心着建造烟囱工厂的事?
布伦顿的自由市场必胜的自信结论,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样,也许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但它反映出当下众多著作对俄国革命的消极裁决:
它教育了我们什么是没用的。马克思主义挽救了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它受到了革命的检验,然后它失败了。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只是通向更强的专政。作为经济管控的药方它同样失败了。今天已经没有严肃的经济学家支持把国家全体所有制当做通向繁荣的道路……俄国革命最大的教训是,要实现大多数的经济目的,市场比国家更有用。1991年以后,社会主义土崩瓦解。
他补充道,如果俄国革命还有什么成就遗留下来的话,可能就是中国了。史密斯则用更为谨慎的措辞,给出了相似的评价:
苏联展现了推动工业生产粗放增长的能力以及建设国防部门的能力,但当资本主义朝向更为集约化的生产形式和“消费资本主义”转换时,它没有展现出与之竞争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中国G。C。D促使他们的国家跻身经济和政治世界的领先力量的行列,这一成就相比于它所广泛模仿的制度更为令人振奋。实际上,随着21世纪的发展,中国革命也许会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
现在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俄国革命”的招牌正岌岌可危,这个结论亟待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去面对,尽管还不清楚它如何定性、继而如何纪念这场革命。失去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一章,这样的风险是任何一个爱国的政权都不能忽视的。也许到了二百周年纪念时,俄罗斯就会找到抢救这块招牌的办法。而对于那时的西方(假定这种具有反常弹性的“俄国”和“西方”的二分法能幸存至下个世纪)来说,俄国革命看起来也一定会有所不同。历史学家们的判断,无论我们多么不乐意接受,它都反映着当下;而大量贬低俄国革命的声音,忏悔的和反对的,其实都反映了苏联解体合乎其地位的影响(或许是短期的影响?)。到了2117年,谁又知道人们是怎么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