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朋:《融化》展的新思路
圆桌讨论:交易场所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THE TRADING FLOOR

纽约的新美术馆
在应约《Flash Art》杂志的邀请下,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马希米里阿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和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在纽约的办公室见面。这次会议聊起了今天纽约艺术环境中的许多有意思的问题。谈话的录音被整理并发表在《Flash Art》为期两刊的专题“聚焦纽约”“ Focus New York”中。其中的大话题包括“艺术家是不是还需要住在纽约才会成功?”,《Flash Art》非常感谢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马希米里阿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和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感谢他们接受了邀请并对这次专题的投入,他们的精神对我们来说是最能代表《Flash Art》的。
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这怪你。我觉得策展人目前处于艺术链中的最低位置。很多大展看上去都差不多一样,拥有同样的55位艺术家,而这些展览同时也被同样的35位策展人策划、评判或推荐。艺术经纪人花那么多精力去寻找艺术家,然而策展人的行动却那么保守,显得像个大知识分子或只按照自己意愿行事。如果画商连续做了10个差劲的展览,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倒闭;然而,如果策展人连续做了10个差劲的展览——大部分的他们——都会被提拔的。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我不赞同。我认为策展分成两个不同的流派。分成非常欧洲的流派和非常美国的流派:美国流派基本上是比较学术的、细致的策展方式,这一般不需要在政治内容或社会层面上体现作者身份——这也说明了欧洲的策展方式,是多少有些需要体现作者身份的。我们大家都非常敬仰的,比如Harald Szeemann、 Kasper Koenig和其他人,他们都是从1990年代开始“策展就是信息特权交易”的一代。
在1990年代,策展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工作,那是个网络年代、是想法和需要很多收集信息工作的年代。我其实觉得我们近几年都生活在“后观点时代”“post-opinionism”中。近年来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做策展人了。他们想当拍卖商或画廊家,或者,如果有钱就直接当收藏家。很无聊…所以我认为“后观点时代”是一个能找到支持的情况,买的人、展出的人、收藏的人,还包括任何有点质量的作品。就像存在着一个非常饥饿的巨大市场,而作为策展人你必须努力与之对立。
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非常多的人拥有购买能力,但相关的艺术家却很少,因为藏家们都想要中国绘画,根本就生产不够。我认为这是对逐渐消失的艺术环境的一个很好的隐喻,但和策展人无关。艺术环境崩溃地解散成机构、策展、教育和内容的寻找、意义和差异,还有市场。我不认为策展处于最低位置,但我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策展人的地位在逐渐减弱。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当然,大家都对收藏家是21世纪的策展人抱有同样态度。双年展和策展人在1990年代是变化中的作用者,收藏家和艺博会界定了本世纪的前10年。所以,杰里,我理解你的挑衅,但我也觉得策展人处于链中的最低位置是因为权利在近几年已经转移到商业部门的手上,这让藏家和经纪人越来越有影响力,这在很多案例中都是无疑的。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我们的弱势因该导致更多具有实验性的展览和不寻常的姿态。部分策展人,还有更重要的,有些机构还是比较勇敢的,但,不幸地,很多时候策展人都被要求迎合特定的观众和民众。我觉得这就是问题,当你被要求为观众思考艺术。相反地,我认为机构和展览应该产生观众,而不是倒过来。
杰里.索特兹:虽然如此,看看比如像惠特尼双年展这样的拥有老式学院地位的展览,它认为绘画不好。展览中几乎没有绘画。我觉得策展人干脆就说他们认为绘画不好,他们打算做个“无画双年展”好了,这样比较老实而且更具争辩性。或者,看看最近一届的卡耐基国际作品展,展览中有40%的作品分别来自同样的5家画廊,这些画廊在切尔西(Chelsea)彼此就隔着一条街道。这是多么惊人的狭义和安全。展览的策展工作都不需要通过环游世界考察才能进行了,你只需要坐在桌前将名字写在信封背面就行。看看,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艺术世界正在缩小的过程中。我想纽约大概有100家画廊可以关门了。这个收缩大概在2年。同时,将会有更大的能量位于雷达低下。在接下去的3年里,那些患有疝气的新一代艺术家、经纪人、策展人和艺评,将会出现。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对于崭露头角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个最佳时期。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你怎么衡量策展人的作用?我因为可以赶在柏林还未完全膨胀和空洞前在那儿工作而感到庆幸。我可以在那儿工作很多年,由于某种巧合,或近似意外的,差不多每个新的展览都能在社会中产生影响,从我们的小报到当时的领导人。
比如说,当年圣地亚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将避难者放入硬纸板箱,这是对德国形势的隐喻,因为当时德国确实那么对待避难者的。这发生在国家当时那么多有关政治正确性的时候,都与共鸣有关。现在我们拥有一个模糊的柏林,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艺术家了。(笑)纽约的艺术环境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你会认为卡耐基国际作品展的目光只有5条街道那么远,这已经是个奇迹。这比你说得好,我认为市场拥有那么多的支配权力是因为太多人参与了艺术的商品化。艺术环境已经分成两批人:很多人参与的商品化和拍卖现象,还有我觉得这个分裂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有意思的环境和具有干涉性的作品。
杰里.索特兹:我认为拍卖世界是“很多很多” 的反面,我认为它是“很少很少”的。我觉得只有1%之1%之1% 人参与了拍卖,而且我不认为艺术家都从中牟利了,除了赚钱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但我不会认为它特别大或代表了任何部分,这只是个恶劣的行为,一个在公众面前为了引人注目而做的戏剧性的表演。艺术界的人都为钱着迷但钱证明不了质量。过去几年,买家都忘了什么是艺术,只知道迷信那些名为赫斯特、村上隆、理查德…的财神。这些人都把自己变成产品。晚近的Jim Dines。很无聊很悲哀,尤其对那些拥有好本质的艺术家来说。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回到我们的主题,那就是纽约,我想这是一个受到画廊驱使的城市。我的意思是受画廊驱使,而不是受市场驱使。在切尔西有很多画廊大概都不赚钱或赚得不够,无论如何,事实是在切尔西我们有400家画廊,然后每个月有相当于一个“卡塞尔文献展”在发生。我经常想——而这也是我、毛里左.卡特兰和阿里.舒伯尼克在第二期“Charley”想做的——那就是我们应该认为纽约是很精彩的,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展览,那么你就会获得一个很精彩的展览,一个连“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都无法与之竞争的展览。这种力量当然也对机构起到作用。
这是健康的因为它迫使机构改变思考方式,让机构更负责任。但,另一方面,也让机构更弱了。只要市场还好,经营一家画廊就像Richard Prince的卖淫玩笑:“多好的生意啊!你有,你卖,然后你还有。”我想在过去几年画廊一直都是纽约的主要动力。画廊不像美术馆,它们没有基金会的捐款,它们不需要太多内部的共鸣,它们会更小也更快,只要它们能卖,它们就有钱做更好的展览。而且当画廊好了,它们的兴趣也不会一直是赚钱而是生产更好的文化。我不认为市场都是邪恶的。这几年来我在画廊看到很多美术馆级别的展览,比如高古轩画廊做的培根和贾柯梅蒂的展览,或是几年前在Gavin Brown那儿看到的疯狂的Urs Fischer的展览,那个有个洞的展览。现在的事物必须面临转变:最终,市场慢下来了,机构恢复拥有新的话语权。但我们必须从经验中学习:机构必须变得更活泼、更快、更勇敢。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杰里,当你说拍卖市场只有“1%之1%之1% 的人参与”时,我反对你。我认为这是冰山一角,但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一角。它有更广泛的观众而且参与的层面更大。我同意它的直接参与者占少数,但人们钻研它。我经常在公共开放日参观艺博会…但谁会在公共开放日去?这不是冰山一角,这是产业的绝大部分拥护者,我想它看上去像个冰山一角。这点我同意它是1%之1%。当我在威尼斯参观双年展时,有位美术馆的总监在参观了Palazzo Grassi后对我说,“噢,我还没看艺博会呢,也许我在离开前应该去看看,”然后我才发现,他指的是双年展!所以在市场强大的时代下,艺博会和双年展互相较劲。就像马希米里阿诺回忆的,我们在一个谈论策展的小组讨论,我非常意外地发现,讨论会上有一半的策展人是…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画廊家!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对的。与Shafrazy及Barbara Gladstone做精彩的策展表演。我想画廊真的可以利用它们自己的独立性,这在纽约是很常见的。
杰里.索特兹:在柏林他们说纽约的一切都有关市场。在伦敦他们也说纽约只有市场。所有人都指控纽约只有市场。在柏林和纽约,我终于忍不住爆发说,“你们展同样的艺术家,你们卖给同样的收藏家,你们和同样的策展人合作然后赚很多很多的钱。纽约比起其它选择不是市场的太多还是太少而已。”。现在,没有人是有关市场了,谢天谢地。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纽约会更明显地把所有的画廊集中在同一个区,这很聪明。
杰里.索特兹:这是纽约一直拥有的一点。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记得在2000年,Andrea Rosen告诉我如果展览很棒,春天的星期六下午,参观者可以达到8千人,我觉得这在柏林或伦敦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画廊是免费入场的,所以会有那么多观众。但,这同样表示,就算他们不是在和MOMA比较,他们也确实在文化方面达到了令人留下深刻影响的效果。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你在说的是有关策展人的多变,整个系统就是在那儿开始崩溃的。你可以在一个私人的地方策展,你可以用非常吓人的方式,都可以很棒。然后,还有美术馆,它还得是个“矫正”,变化中的永恒不变,其他人的领头羊,寻找着某种原则,让人同意抑或不同意。这个论述还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现在都去当拍卖家了。其实,就像Lisa Dennison离开高古轩到苏富比去一样,这很有意思,是非常不同的观点。
杰里.索特兹:这是普遍上的观点,不是特定的。我认为Lisa Dennison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回到了自己的根源。她知道工作在哪儿,她可以很直接地和收藏家工作,用更快的方式,这样也没什么错。两者间我都希望拍卖界会掉下悬崖,最后只能和死去的艺术家合作。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杰里,你刚刚说了很重要的一点,Lisa Dennison现在可以用更快的方式工作。我想这也是私人单位和美术馆的差别。高古轩可以推出Roy Lichtenstein的展览“Girls”(2008年纽约的展览)——非常精彩——然后过了几个月后他们可以打电话给杰夫.昆斯,叫他出本画册,他们有钱支付一切。这是纽约的任何机构都无法达到的速度,而且也没有那个自由。
杰里.索特兹:你们为什么不做呢?作品都不是为了销售的,他们必须保证,你们也有保险,必须是借来的——你可以那么做。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认为一间美术馆,收藏还是不收藏,都必须要接受所有的标准。它经常会有很多相互联系,共同掌管美术馆的思想和简介。想一想那些不容易被收藏的作品…
杰里.索特兹:有什么事不能被收藏的?录像可以被收藏,一罐空气可以被收藏,一罐屎也可以被收藏。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们知道,一罐屎可以很容易地被收藏,但还是有很多作品不用说是非常商品化的,因为它们需要很多空间,而且没有交换价值。然后,你想想行为艺术,自从我们MOMA现在开始大规模地研究行为——我刚刚在洛杉矶见了Simone Forti,问她关于过去40年中创作的行为作品,她仍在思考如何保存这些作品。我认为她是重要的艺术家!这些事情应该是美术馆负责的,而不是将她拍卖成一位拥有一千七百万美元左右的蓝筹艺术家。我希望这是完全不同的过程。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最后,我同意如果美术馆的质量好,那么他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应该打破惯例地去思考,我们应该展示在其它地方展示不了的东西。
杰里.索特兹:我觉得在MOMA更困难,但大家都应该会欢迎它,如果你的建议很酷,没有人会反对你:董事或是收藏家,或是馆长都不会。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知道这也是你们想要的。P.S.1完全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起来,它应该是世界上最棒的另类空间。因此我每次去那儿时都很兴奋,但奇怪的是离开时又那么失望。MOMA和P.S.1的婚姻是还未被开发的婚姻。他们需要在公共场所进行狂野的性爱。目前。频繁地。或者P.S.1应该傍大款。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们在努力,但不是在傍大款那一方面。
杰里.索特兹:其实,Michael Govan开了Dia: Beacon然后又把Dia: New York关闭的举动让我感到悲哀和难忘。对我来说,这就像小布什攻打伊拉克一样。Govan和Dia之间的问题需要至少五年的时间才能解开。这是过去10年中,美术馆界内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现在洛杉矶的MoCA也因为馆长和董事的问题而烦恼。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新美术馆的好机会,但仍然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占领的。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记得为了奥莱佛.伊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我们把过道给封闭了,安装了单频的黄色灯管,将天井清空,安装了一个通风设备——将作品安置在艺术建筑内,没有人清楚这到底是件雕塑还是奇怪的灯型装置。我觉得这些步骤都是美术馆愿意踏出的,而且也的确踏出了。这是没有标签的展览,它看上去或许是很小的一步,但愿意这样做就意味着它是激进的。
杰里.索特兹:我同意。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觉得我们谈论市场和机构,这很有意思,但我们没有谈到艺术家。你们难道不觉得情况愈来愈不以艺术家为中心了?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不,我不那么认为。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那么,想想柏林的曾经和仍然保持的很多层面。我在那儿居住了两年,虽然我同意它的确改变了许多,但柏林仍然是由艺术家组成的非常与众不同的城市。也许这从特定的一代艺术家开始,奥莱佛.伊利亚松、汤姆斯.迪曼(Thomas Demand)等人…他们是柏林的“起点”,但后来融入了更多的艺术家。目前,仅仅邀请居住在柏林的艺术家就能组成一个国际级别的双年展。在纽约,你有很棒的艺术家以及丰富的艺术家历史:Lawrence Weiner, Dan Graham…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和Mary Heilman.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对,但我不认为你们的艺术家拥有和柏林一样的密度。我在纽约看见许多很好的艺术家,但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洛杉矶已经成为了艺术友好的城市。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想这也是观点的问题:就拿Terence Koh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他在美国只有很少的支持者——Shamim M. Momin和其他人——但在欧洲却得到很大的推崇,他们把他看作是James Lee Byars继承人。在艺术家Ryan McGingley, Dash Snow, Dan Colen 和Nate Lowman…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于背景的理解困难,在纽约他们拥有不同的背景。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当然有很多很棒的年轻艺术家,如Paul Chan或Sharon Hayes,就拿这些我最近合作的人来说。当然,还有其他人。但我觉得你再也不能将纽约描述成一个开放的工作室,他和你在柏林看到的不同。也许,我是夸张了,但我是那么想象纽约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当然,今天的纽约拥有了美术硕士课程的学府,但对我来说这不像一个你可以浪费时间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它太贵了。如果有人问该推荐年轻艺术家到什么地方去好,在纽约和柏林之间选择,我会说,去柏林。
杰里.索特兹:为什么?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不想将柏林神化,你可以在那儿过这纽约一样的生活,但没有金钱压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除非你在经济上非常独立富有。这里的社会游戏也许比较突出。
杰里.索特兹:纽约比柏林更为社会?比起伦敦或者洛杉矶?又来了。居住在艺术城市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穷得有型,这在纽约很困难,但很多艺术家都在寻找这种方式。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感觉洛杉矶或者柏林也许会让你更自由。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觉得柏林和洛杉矶拥有纽约所没有的。柏林有很多时间和空间,就算你不是明星艺术家,你不工作也好,你还是负担得起一间公寓或工作室。
杰里.索特兹:我觉得纽约和它的狂怒是相反的,是很亲密的。我觉得它会保持活跃的可能性很大。我们有时间有空间有艺术家。这个沼泽仍在冒出富有创造性的泡泡。是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但这因为我们是个岛文化,我们一直都是个岛文化。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这样说也许很庸俗,但千禧年却在这个城市开始。砰地一声从毁灭中开始,但纽约是独特的,因为它拥有重新来过的能力。很多方面都来它的神话。遗憾地,纽约最近的转变是将钱作为核心争议。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暂停揭露价格或谈论作品的价格。但,让杂志和主流文化更关注艺术的也是这些价格。
杰里.索特兹:美国正处于作为帝国的最后阶段。当帝国崩溃进入混乱后会衍生出巨大的东西。我觉得声称纽约结束了是非常错误的。它或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是交易场所。也许依然真实的是,没有事情发生就没有重大的事业,这至少在纽约是那么一回事儿。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而如果没有,这个事业就无法完成。我认识一些在自己国家获得极高尊敬的艺术家,但在这里他们还并未获得承认,他们对此拥有巨大的愿望。最近,我在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花费了许多时间,我也常去以色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成为人们离开的地方,从Mona Hatoum谈到Emily Jacir,从Sigalit Landau到Yael Bartana,从Guy Ben-Ner到Keren Cytter,有那么多艺术家来自那么小的地方。
杰里.索特兹:因为动荡的社会产生很多的艺术家。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因为P.S.1的项目,所以我和Yael Bartana的对话很频繁,她正尝试将争论转换到波兰或荷兰,她是经常旅行的艺术家,她将自己的信仰和审美转换成地方性的举动对我来说很震撼。我刚去了南非,发现那儿正在改变,从性别和方式上讲,对于发生在那么小的环境来说很令人兴奋。无论如何,他们很想和纽约有所联系,他们希望到那儿展出。当我在泰国时,我有幸和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Surasi Kusolwong以及Navin Rawanchaikul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见面。能看见他们如何实际地建造了非常活跃和真实的场景是非常有意思的,无论如何,我们所想要讨论的,指明了纽约就是个交易场所。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不想听上去像个火药,但没有纽约我们就不能做到吗?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觉得不行。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觉得如果纽约休息一下会有好处。
杰里.索特兹:对的,纽约——这也许是个秘密也许不——它是世界上最守旧的,而且非常自恋,这很糟糕。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最近我们在MoMA有个会议,我和达喀尔的一个双年展的策展人聊起,每个人都在谈论展览没有反映当地艺术环境的话题。我说,“没问题的,这就像纽约!”看看惠特尼双年展,每个人都说它很有争议性,是本土的、是守旧的而且它就是个美国的双年展,就像达喀尔它就是个非洲的双年展。那么你到底要什么?无论如何,纽约是不会承认的,这很好笑。我觉得其中一个对机构的观点是,它们太强大了,然后曲解它。我觉得对于纽约有可能会失败的怀疑反而对纽约会有好处的。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某种程度上说,失败往往像个策展的经典台词:“我们必须失败。”。但是,纽约完全不鼓励失败。纽约鼓励主流和共鸣,有时候还用很有问题的方式。这不是一个欢迎例外的城市,作为一名艺评你经常会喜欢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但当他们做到时,你会说,“你的另一种方式不正确”。
杰里.索特兹:对的,是这样。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你最后一次看见的失败是什么?
杰里.索特兹:我看见很多。Urs Fischer和Gavin Brown在非常有野心的Shafrazi画廊的展览,这个展览的混乱让人视觉疲劳,一方面来说它对我们很不敬,但也是个巨大的成功,呈现了另一种不同的空间,不是死的,它像个咒语抵消掉了很多艺术。在纽约有很多建筑都抵消了艺术。对于下一代的艺术经纪人来说,制造一个冲击不因该只会学习成为Barbara Gladstones,他们应该探讨不同的方式。如果你成为切尔西的一个迷你画廊,你永远只能呆在儿童桌上。是时候让新的一代取代了。尤其现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艺术已经快死了。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觉得纽约不知道空间的多样性。也许是因为我在米兰的Trussardi基金会工作的缘故才会对此产生这样的印象,Trussardi基金会像个守候活动,但我和卡特兰及阿里一起做的柏林双年展也一样,和过去的历史有关,那些被历史化身的建筑。当然,像Creative Time、Art Production Fund 和 Public Art Fund创造的移动机构非常好,这是别人所提供不了的。我总是觉得艺术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而感到很享受,有时候这也可能是纽约的问题。
杰里.索特兹:是的,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权利,也许这也是艺术家想要的。如果他们不想要,这也就不会发生了。也许将来,我们只剩下一间画廊,那就是高古轩。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或者David Zwirner。(不是开玩笑)
(完)
翻译:嘿乐乐
《Flash Art》杂志,264期,2009年1月-2月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刚刚成为P.S.1艺术中心的总监。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是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特别展览总监/米兰Trussardi基金会的总监。他和艺术家卡特兰及阿里.舒伯尼克创办了“错误画廊”(wrong gall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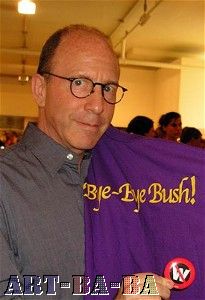
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是纽约杂志的艺评和记者。

Sperone Westwater画廊于纽约Bowery区的新址。
© Sperone Westwater, New York


Urs Fischer和Gavin Brown于2008年在纽约Tony Shafrazi画廊策划的展览《谁怕贾斯培尔.琼斯》《Who’s Afraid of Jasper Johns?》。


2007年Urs Fischer在Gavin Brown's enterprise举办的展览。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THE TRADING FLOOR

纽约的新美术馆
在应约《Flash Art》杂志的邀请下,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马希米里阿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和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在纽约的办公室见面。这次会议聊起了今天纽约艺术环境中的许多有意思的问题。谈话的录音被整理并发表在《Flash Art》为期两刊的专题“聚焦纽约”“ Focus New York”中。其中的大话题包括“艺术家是不是还需要住在纽约才会成功?”,《Flash Art》非常感谢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马希米里阿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和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感谢他们接受了邀请并对这次专题的投入,他们的精神对我们来说是最能代表《Flash Art》的。
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这怪你。我觉得策展人目前处于艺术链中的最低位置。很多大展看上去都差不多一样,拥有同样的55位艺术家,而这些展览同时也被同样的35位策展人策划、评判或推荐。艺术经纪人花那么多精力去寻找艺术家,然而策展人的行动却那么保守,显得像个大知识分子或只按照自己意愿行事。如果画商连续做了10个差劲的展览,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倒闭;然而,如果策展人连续做了10个差劲的展览——大部分的他们——都会被提拔的。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我不赞同。我认为策展分成两个不同的流派。分成非常欧洲的流派和非常美国的流派:美国流派基本上是比较学术的、细致的策展方式,这一般不需要在政治内容或社会层面上体现作者身份——这也说明了欧洲的策展方式,是多少有些需要体现作者身份的。我们大家都非常敬仰的,比如Harald Szeemann、 Kasper Koenig和其他人,他们都是从1990年代开始“策展就是信息特权交易”的一代。
在1990年代,策展是很多人都向往的工作,那是个网络年代、是想法和需要很多收集信息工作的年代。我其实觉得我们近几年都生活在“后观点时代”“post-opinionism”中。近年来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做策展人了。他们想当拍卖商或画廊家,或者,如果有钱就直接当收藏家。很无聊…所以我认为“后观点时代”是一个能找到支持的情况,买的人、展出的人、收藏的人,还包括任何有点质量的作品。就像存在着一个非常饥饿的巨大市场,而作为策展人你必须努力与之对立。
在中国的中产阶级中,非常多的人拥有购买能力,但相关的艺术家却很少,因为藏家们都想要中国绘画,根本就生产不够。我认为这是对逐渐消失的艺术环境的一个很好的隐喻,但和策展人无关。艺术环境崩溃地解散成机构、策展、教育和内容的寻找、意义和差异,还有市场。我不认为策展处于最低位置,但我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策展人的地位在逐渐减弱。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当然,大家都对收藏家是21世纪的策展人抱有同样态度。双年展和策展人在1990年代是变化中的作用者,收藏家和艺博会界定了本世纪的前10年。所以,杰里,我理解你的挑衅,但我也觉得策展人处于链中的最低位置是因为权利在近几年已经转移到商业部门的手上,这让藏家和经纪人越来越有影响力,这在很多案例中都是无疑的。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我们的弱势因该导致更多具有实验性的展览和不寻常的姿态。部分策展人,还有更重要的,有些机构还是比较勇敢的,但,不幸地,很多时候策展人都被要求迎合特定的观众和民众。我觉得这就是问题,当你被要求为观众思考艺术。相反地,我认为机构和展览应该产生观众,而不是倒过来。
杰里.索特兹:虽然如此,看看比如像惠特尼双年展这样的拥有老式学院地位的展览,它认为绘画不好。展览中几乎没有绘画。我觉得策展人干脆就说他们认为绘画不好,他们打算做个“无画双年展”好了,这样比较老实而且更具争辩性。或者,看看最近一届的卡耐基国际作品展,展览中有40%的作品分别来自同样的5家画廊,这些画廊在切尔西(Chelsea)彼此就隔着一条街道。这是多么惊人的狭义和安全。展览的策展工作都不需要通过环游世界考察才能进行了,你只需要坐在桌前将名字写在信封背面就行。看看,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艺术世界正在缩小的过程中。我想纽约大概有100家画廊可以关门了。这个收缩大概在2年。同时,将会有更大的能量位于雷达低下。在接下去的3年里,那些患有疝气的新一代艺术家、经纪人、策展人和艺评,将会出现。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对于崭露头角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个最佳时期。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你怎么衡量策展人的作用?我因为可以赶在柏林还未完全膨胀和空洞前在那儿工作而感到庆幸。我可以在那儿工作很多年,由于某种巧合,或近似意外的,差不多每个新的展览都能在社会中产生影响,从我们的小报到当时的领导人。
比如说,当年圣地亚哥.西耶拉(Santiago Sierra)将避难者放入硬纸板箱,这是对德国形势的隐喻,因为当时德国确实那么对待避难者的。这发生在国家当时那么多有关政治正确性的时候,都与共鸣有关。现在我们拥有一个模糊的柏林,也许是因为有太多的艺术家了。(笑)纽约的艺术环境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你会认为卡耐基国际作品展的目光只有5条街道那么远,这已经是个奇迹。这比你说得好,我认为市场拥有那么多的支配权力是因为太多人参与了艺术的商品化。艺术环境已经分成两批人:很多人参与的商品化和拍卖现象,还有我觉得这个分裂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有意思的环境和具有干涉性的作品。
杰里.索特兹:我认为拍卖世界是“很多很多” 的反面,我认为它是“很少很少”的。我觉得只有1%之1%之1% 人参与了拍卖,而且我不认为艺术家都从中牟利了,除了赚钱我看不出它还有什么。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但我不会认为它特别大或代表了任何部分,这只是个恶劣的行为,一个在公众面前为了引人注目而做的戏剧性的表演。艺术界的人都为钱着迷但钱证明不了质量。过去几年,买家都忘了什么是艺术,只知道迷信那些名为赫斯特、村上隆、理查德…的财神。这些人都把自己变成产品。晚近的Jim Dines。很无聊很悲哀,尤其对那些拥有好本质的艺术家来说。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回到我们的主题,那就是纽约,我想这是一个受到画廊驱使的城市。我的意思是受画廊驱使,而不是受市场驱使。在切尔西有很多画廊大概都不赚钱或赚得不够,无论如何,事实是在切尔西我们有400家画廊,然后每个月有相当于一个“卡塞尔文献展”在发生。我经常想——而这也是我、毛里左.卡特兰和阿里.舒伯尼克在第二期“Charley”想做的——那就是我们应该认为纽约是很精彩的,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展览,那么你就会获得一个很精彩的展览,一个连“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都无法与之竞争的展览。这种力量当然也对机构起到作用。
这是健康的因为它迫使机构改变思考方式,让机构更负责任。但,另一方面,也让机构更弱了。只要市场还好,经营一家画廊就像Richard Prince的卖淫玩笑:“多好的生意啊!你有,你卖,然后你还有。”我想在过去几年画廊一直都是纽约的主要动力。画廊不像美术馆,它们没有基金会的捐款,它们不需要太多内部的共鸣,它们会更小也更快,只要它们能卖,它们就有钱做更好的展览。而且当画廊好了,它们的兴趣也不会一直是赚钱而是生产更好的文化。我不认为市场都是邪恶的。这几年来我在画廊看到很多美术馆级别的展览,比如高古轩画廊做的培根和贾柯梅蒂的展览,或是几年前在Gavin Brown那儿看到的疯狂的Urs Fischer的展览,那个有个洞的展览。现在的事物必须面临转变:最终,市场慢下来了,机构恢复拥有新的话语权。但我们必须从经验中学习:机构必须变得更活泼、更快、更勇敢。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杰里,当你说拍卖市场只有“1%之1%之1% 的人参与”时,我反对你。我认为这是冰山一角,但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一角。它有更广泛的观众而且参与的层面更大。我同意它的直接参与者占少数,但人们钻研它。我经常在公共开放日参观艺博会…但谁会在公共开放日去?这不是冰山一角,这是产业的绝大部分拥护者,我想它看上去像个冰山一角。这点我同意它是1%之1%。当我在威尼斯参观双年展时,有位美术馆的总监在参观了Palazzo Grassi后对我说,“噢,我还没看艺博会呢,也许我在离开前应该去看看,”然后我才发现,他指的是双年展!所以在市场强大的时代下,艺博会和双年展互相较劲。就像马希米里阿诺回忆的,我们在一个谈论策展的小组讨论,我非常意外地发现,讨论会上有一半的策展人是…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画廊家!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对的。与Shafrazy及Barbara Gladstone做精彩的策展表演。我想画廊真的可以利用它们自己的独立性,这在纽约是很常见的。
杰里.索特兹:在柏林他们说纽约的一切都有关市场。在伦敦他们也说纽约只有市场。所有人都指控纽约只有市场。在柏林和纽约,我终于忍不住爆发说,“你们展同样的艺术家,你们卖给同样的收藏家,你们和同样的策展人合作然后赚很多很多的钱。纽约比起其它选择不是市场的太多还是太少而已。”。现在,没有人是有关市场了,谢天谢地。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纽约会更明显地把所有的画廊集中在同一个区,这很聪明。
杰里.索特兹:这是纽约一直拥有的一点。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记得在2000年,Andrea Rosen告诉我如果展览很棒,春天的星期六下午,参观者可以达到8千人,我觉得这在柏林或伦敦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然,画廊是免费入场的,所以会有那么多观众。但,这同样表示,就算他们不是在和MOMA比较,他们也确实在文化方面达到了令人留下深刻影响的效果。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你在说的是有关策展人的多变,整个系统就是在那儿开始崩溃的。你可以在一个私人的地方策展,你可以用非常吓人的方式,都可以很棒。然后,还有美术馆,它还得是个“矫正”,变化中的永恒不变,其他人的领头羊,寻找着某种原则,让人同意抑或不同意。这个论述还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现在都去当拍卖家了。其实,就像Lisa Dennison离开高古轩到苏富比去一样,这很有意思,是非常不同的观点。
杰里.索特兹:这是普遍上的观点,不是特定的。我认为Lisa Dennison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回到了自己的根源。她知道工作在哪儿,她可以很直接地和收藏家工作,用更快的方式,这样也没什么错。两者间我都希望拍卖界会掉下悬崖,最后只能和死去的艺术家合作。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杰里,你刚刚说了很重要的一点,Lisa Dennison现在可以用更快的方式工作。我想这也是私人单位和美术馆的差别。高古轩可以推出Roy Lichtenstein的展览“Girls”(2008年纽约的展览)——非常精彩——然后过了几个月后他们可以打电话给杰夫.昆斯,叫他出本画册,他们有钱支付一切。这是纽约的任何机构都无法达到的速度,而且也没有那个自由。
杰里.索特兹:你们为什么不做呢?作品都不是为了销售的,他们必须保证,你们也有保险,必须是借来的——你可以那么做。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认为一间美术馆,收藏还是不收藏,都必须要接受所有的标准。它经常会有很多相互联系,共同掌管美术馆的思想和简介。想一想那些不容易被收藏的作品…
杰里.索特兹:有什么事不能被收藏的?录像可以被收藏,一罐空气可以被收藏,一罐屎也可以被收藏。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们知道,一罐屎可以很容易地被收藏,但还是有很多作品不用说是非常商品化的,因为它们需要很多空间,而且没有交换价值。然后,你想想行为艺术,自从我们MOMA现在开始大规模地研究行为——我刚刚在洛杉矶见了Simone Forti,问她关于过去40年中创作的行为作品,她仍在思考如何保存这些作品。我认为她是重要的艺术家!这些事情应该是美术馆负责的,而不是将她拍卖成一位拥有一千七百万美元左右的蓝筹艺术家。我希望这是完全不同的过程。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最后,我同意如果美术馆的质量好,那么他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我们应该打破惯例地去思考,我们应该展示在其它地方展示不了的东西。
杰里.索特兹:我觉得在MOMA更困难,但大家都应该会欢迎它,如果你的建议很酷,没有人会反对你:董事或是收藏家,或是馆长都不会。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知道这也是你们想要的。P.S.1完全没有被充分地利用起来,它应该是世界上最棒的另类空间。因此我每次去那儿时都很兴奋,但奇怪的是离开时又那么失望。MOMA和P.S.1的婚姻是还未被开发的婚姻。他们需要在公共场所进行狂野的性爱。目前。频繁地。或者P.S.1应该傍大款。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们在努力,但不是在傍大款那一方面。
杰里.索特兹:其实,Michael Govan开了Dia: Beacon然后又把Dia: New York关闭的举动让我感到悲哀和难忘。对我来说,这就像小布什攻打伊拉克一样。Govan和Dia之间的问题需要至少五年的时间才能解开。这是过去10年中,美术馆界内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现在洛杉矶的MoCA也因为馆长和董事的问题而烦恼。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新美术馆的好机会,但仍然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占领的。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记得为了奥莱佛.伊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我们把过道给封闭了,安装了单频的黄色灯管,将天井清空,安装了一个通风设备——将作品安置在艺术建筑内,没有人清楚这到底是件雕塑还是奇怪的灯型装置。我觉得这些步骤都是美术馆愿意踏出的,而且也的确踏出了。这是没有标签的展览,它看上去或许是很小的一步,但愿意这样做就意味着它是激进的。
杰里.索特兹:我同意。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觉得我们谈论市场和机构,这很有意思,但我们没有谈到艺术家。你们难道不觉得情况愈来愈不以艺术家为中心了?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不,我不那么认为。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那么,想想柏林的曾经和仍然保持的很多层面。我在那儿居住了两年,虽然我同意它的确改变了许多,但柏林仍然是由艺术家组成的非常与众不同的城市。也许这从特定的一代艺术家开始,奥莱佛.伊利亚松、汤姆斯.迪曼(Thomas Demand)等人…他们是柏林的“起点”,但后来融入了更多的艺术家。目前,仅仅邀请居住在柏林的艺术家就能组成一个国际级别的双年展。在纽约,你有很棒的艺术家以及丰富的艺术家历史:Lawrence Weiner, Dan Graham…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和Mary Heilman.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对,但我不认为你们的艺术家拥有和柏林一样的密度。我在纽约看见许多很好的艺术家,但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洛杉矶已经成为了艺术友好的城市。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想这也是观点的问题:就拿Terence Koh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他在美国只有很少的支持者——Shamim M. Momin和其他人——但在欧洲却得到很大的推崇,他们把他看作是James Lee Byars继承人。在艺术家Ryan McGingley, Dash Snow, Dan Colen 和Nate Lowman…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于背景的理解困难,在纽约他们拥有不同的背景。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当然有很多很棒的年轻艺术家,如Paul Chan或Sharon Hayes,就拿这些我最近合作的人来说。当然,还有其他人。但我觉得你再也不能将纽约描述成一个开放的工作室,他和你在柏林看到的不同。也许,我是夸张了,但我是那么想象纽约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当然,今天的纽约拥有了美术硕士课程的学府,但对我来说这不像一个你可以浪费时间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它太贵了。如果有人问该推荐年轻艺术家到什么地方去好,在纽约和柏林之间选择,我会说,去柏林。
杰里.索特兹:为什么?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不想将柏林神化,你可以在那儿过这纽约一样的生活,但没有金钱压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除非你在经济上非常独立富有。这里的社会游戏也许比较突出。
杰里.索特兹:纽约比柏林更为社会?比起伦敦或者洛杉矶?又来了。居住在艺术城市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穷得有型,这在纽约很困难,但很多艺术家都在寻找这种方式。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感觉洛杉矶或者柏林也许会让你更自由。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觉得柏林和洛杉矶拥有纽约所没有的。柏林有很多时间和空间,就算你不是明星艺术家,你不工作也好,你还是负担得起一间公寓或工作室。
杰里.索特兹:我觉得纽约和它的狂怒是相反的,是很亲密的。我觉得它会保持活跃的可能性很大。我们有时间有空间有艺术家。这个沼泽仍在冒出富有创造性的泡泡。是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空间,但这因为我们是个岛文化,我们一直都是个岛文化。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这样说也许很庸俗,但千禧年却在这个城市开始。砰地一声从毁灭中开始,但纽约是独特的,因为它拥有重新来过的能力。很多方面都来它的神话。遗憾地,纽约最近的转变是将钱作为核心争议。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暂停揭露价格或谈论作品的价格。但,让杂志和主流文化更关注艺术的也是这些价格。
杰里.索特兹:美国正处于作为帝国的最后阶段。当帝国崩溃进入混乱后会衍生出巨大的东西。我觉得声称纽约结束了是非常错误的。它或许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是交易场所。也许依然真实的是,没有事情发生就没有重大的事业,这至少在纽约是那么一回事儿。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而如果没有,这个事业就无法完成。我认识一些在自己国家获得极高尊敬的艺术家,但在这里他们还并未获得承认,他们对此拥有巨大的愿望。最近,我在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花费了许多时间,我也常去以色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成为人们离开的地方,从Mona Hatoum谈到Emily Jacir,从Sigalit Landau到Yael Bartana,从Guy Ben-Ner到Keren Cytter,有那么多艺术家来自那么小的地方。
杰里.索特兹:因为动荡的社会产生很多的艺术家。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因为P.S.1的项目,所以我和Yael Bartana的对话很频繁,她正尝试将争论转换到波兰或荷兰,她是经常旅行的艺术家,她将自己的信仰和审美转换成地方性的举动对我来说很震撼。我刚去了南非,发现那儿正在改变,从性别和方式上讲,对于发生在那么小的环境来说很令人兴奋。无论如何,他们很想和纽约有所联系,他们希望到那儿展出。当我在泰国时,我有幸和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Surasi Kusolwong以及Navin Rawanchaikul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见面。能看见他们如何实际地建造了非常活跃和真实的场景是非常有意思的,无论如何,我们所想要讨论的,指明了纽约就是个交易场所。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不想听上去像个火药,但没有纽约我们就不能做到吗?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我觉得不行。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觉得如果纽约休息一下会有好处。
杰里.索特兹:对的,纽约——这也许是个秘密也许不——它是世界上最守旧的,而且非常自恋,这很糟糕。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最近我们在MoMA有个会议,我和达喀尔的一个双年展的策展人聊起,每个人都在谈论展览没有反映当地艺术环境的话题。我说,“没问题的,这就像纽约!”看看惠特尼双年展,每个人都说它很有争议性,是本土的、是守旧的而且它就是个美国的双年展,就像达喀尔它就是个非洲的双年展。那么你到底要什么?无论如何,纽约是不会承认的,这很好笑。我觉得其中一个对机构的观点是,它们太强大了,然后曲解它。我觉得对于纽约有可能会失败的怀疑反而对纽约会有好处的。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某种程度上说,失败往往像个策展的经典台词:“我们必须失败。”。但是,纽约完全不鼓励失败。纽约鼓励主流和共鸣,有时候还用很有问题的方式。这不是一个欢迎例外的城市,作为一名艺评你经常会喜欢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但当他们做到时,你会说,“你的另一种方式不正确”。
杰里.索特兹:对的,是这样。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你最后一次看见的失败是什么?
杰里.索特兹:我看见很多。Urs Fischer和Gavin Brown在非常有野心的Shafrazi画廊的展览,这个展览的混乱让人视觉疲劳,一方面来说它对我们很不敬,但也是个巨大的成功,呈现了另一种不同的空间,不是死的,它像个咒语抵消掉了很多艺术。在纽约有很多建筑都抵消了艺术。对于下一代的艺术经纪人来说,制造一个冲击不因该只会学习成为Barbara Gladstones,他们应该探讨不同的方式。如果你成为切尔西的一个迷你画廊,你永远只能呆在儿童桌上。是时候让新的一代取代了。尤其现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艺术已经快死了。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我觉得纽约不知道空间的多样性。也许是因为我在米兰的Trussardi基金会工作的缘故才会对此产生这样的印象,Trussardi基金会像个守候活动,但我和卡特兰及阿里一起做的柏林双年展也一样,和过去的历史有关,那些被历史化身的建筑。当然,像Creative Time、Art Production Fund 和 Public Art Fund创造的移动机构非常好,这是别人所提供不了的。我总是觉得艺术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而感到很享受,有时候这也可能是纽约的问题。
杰里.索特兹:是的,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权利,也许这也是艺术家想要的。如果他们不想要,这也就不会发生了。也许将来,我们只剩下一间画廊,那就是高古轩。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或者David Zwirner。(不是开玩笑)
(完)
翻译:嘿乐乐
《Flash Art》杂志,264期,2009年1月-2月

克劳斯.比安桑巴赫(Klaus Biesenbach)刚刚成为P.S.1艺术中心的总监。

马希米里阿诺.乔尼(Massimiliano Gioni)是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特别展览总监/米兰Trussardi基金会的总监。他和艺术家卡特兰及阿里.舒伯尼克创办了“错误画廊”(wrong gall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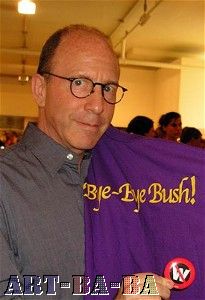
杰里.索特兹(Jerry Saltz)是纽约杂志的艺评和记者。

Sperone Westwater画廊于纽约Bowery区的新址。
© Sperone Westwater, New York


Urs Fischer和Gavin Brown于2008年在纽约Tony Shafrazi画廊策划的展览《谁怕贾斯培尔.琼斯》《Who’s Afraid of Jasper Johns?》。


2007年Urs Fischer在Gavin Brown's enterprise举办的展览。
好文!


可以看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很实际的问题,这样的文章应该越多越好。增加了解之后也能发现自己的问题。

如果画商连续做了10个差劲的展览,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倒闭;然而,如果策展人连续做了10个差劲的展览——大部分的他们——都会被提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