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3月初,杨紫完成了M+博物馆首届希克中国艺术研究资助计划的演讲,这个以“弥散性宗教与中国前卫艺术的起源”为主题的论文,是历经近一年研究的结果,他试图从图像和贯穿古今的信仰结构看待中国前卫艺术的历史,“这对我的工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起点。之后希望能策划一系列非盈利的、小规模的群展,也是与‘图像的任意性和整合性’这样的话题有关。”杨紫说。

以独立策展人身份行走的杨紫曾任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及公共项目总监,及《艺术界》杂志编辑。2020年,他获选为首届“希克中国艺术研究资助计划”研究学人,并担任画廊周北京评委;2019年担任年度华宇青年奖初选评委;他曾入围2017 Hyundai Blue Prize年度艺术大奖。
杨紫称原本最想选社会学的自己是误打误撞进入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而他现在的研究仍与社会学有着更多联系。
“从前几年开始,全世界范围内都开始新的一轮对原始宗教、萨满或神秘学的关注,如果说上一波类似的风潮是西方自觉的去殖民化意识的表现,那么这次的背景是,全球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资本和科技新的统治,让理性主义进入了尴尬的境地,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国与国,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隔绝和撕裂。而人类文明早期恰好具有普世性的特征,或许能为这一症状提供解药。”杨紫选择的“弥散性宗教玉中国前卫艺术的起源”的论题也尝试从人类文明早期的普世性重新入手全球化在当下遇到的新问题。
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的采访中,杨紫讲述了一个年轻策展人是如何跨入艺术行业,又如何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断联结、寻找“涌现”、编织知识,做出自己的艺术判断和职业选择。

策展人杨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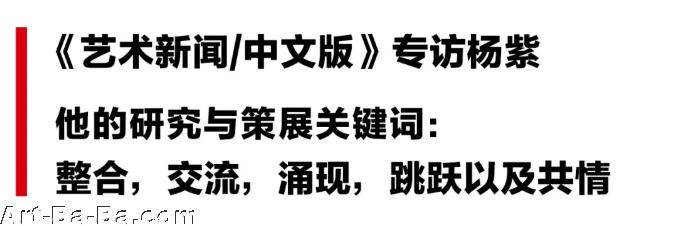
Q:你是怎样跨入艺术行业的?
A: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当代艺术,得知南京江心洲的圣划艺术中心后,去做了志愿者。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德国策展人,在偏远的圣划做了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精彩展览,艺术家包括徐冰、吴山专、申凡等。我从头跟到尾,跟着他打杂,用蹩脚的英语询问他问题,开了眼界。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做社会运动的同时,也关注着当代艺术,在2008年参与了UCCA“青年批评家计划”(YCCA),研习艺术评论写作。但真正从事艺术写作的话要从2010年左右算起,在《艺术界LEAP》做了几年编辑后,在UCCA近五年的工作经历中,几乎再美术馆的各个内容部门都锻炼了一遍:从PR、研究部、展览部,再到公教。

马六明,《与吉尔伯特和乔治的对话》,行为,1993,图片来源:马六明及M+博物馆

Q: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弥散性的宗教与中国前卫艺术的起源”这一研究方向的?
A:从2016年起。阅读瓦尔堡、潘诺夫斯基等学者的图像学著作时,我发现图像的任意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做文字工作的时候,往往要把一个观点一以贯之地说清楚,尽量排除模糊性;但图像有更丰富的“熵”值,可以承载特别多的意思。我发现,中国的宗教中的图像亦是如此,很多图像“正”着、“反”着都能用,比如说皇帝以及试图推翻皇帝的民间起义者所使用的宗教图像可能非常相近,但代表的立场却截然不同。那些图像兼具权威性和颠覆性、世俗性和神圣性——比如说一块稀松平常的石头在某些信仰中,是会被认为神圣的。这一点特别吸引我。

我2019年4月在UCCA沙丘美术馆策划的“敢当:当代神石注疏”,收录10位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在形式或材料上均与石头有所联系,也偏向从当代的眼光审视这一沉默的质料的古老文化意义。说句题外话,那场展览策划线索特别多,而我也刚好喜欢这种多线程工作的方式——做这个展览的时候,除了中国民俗和神话,我同时还在研究极简主义装置和现代主义绘画,以及两者之间的分裂和继承。当时去了欧洲,有机会观摩到属于这两块艺术脉络的重要作品原作。从美学上来看,“敢当:当代神石注疏”中也是暗含有极简主义的策划线索的。这个展览策划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强化了之前只是直觉的信号,那就是,古与今,传统民间文化与当代艺术之间,具有某种图像或主题上的延续,并开始广泛地搜寻证据。
Q:近年来,回溯宗教与当代艺术的关联,或是将宗教融汇到创作中形成了一种趋势,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A:中国的前卫艺术与格林伯格口中的“前卫艺术”是不尽相同的,后者是在一个不停往前冲的,具有目的论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中形成的。而前者的语境恰恰相反,是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反思。因而,在前卫艺术中,短暂的理性启蒙主义的乐观情绪之后,我们看到的艺术家的创作,常常是把普遍被视作神圣化的事物降落到人间。

吕胜中,《招魂堂》,综合媒介,1990年,图片来源:吕胜中

媒介理论家和艺术评论家鲍里斯·格洛伊斯(Boris Groys)曾在文章《艺术与金钱》中引述过格林伯格的《前卫性与媚俗》,他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说,即现代主义的维护者格林伯格在写作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媚俗或者世俗化是前卫艺术的必然结果。这个令人震惊的观点对我的写作也影响很大。
我关注的民间宗教不是一个教派、教别,它是对祖先、对天的普遍祭祀方式,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它的一个客观的社会功能是能够帮助统治者进行社会整合。中国幅员辽阔,要将不同地貌中生活、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统一起来,统治者除了施行行政命令,信仰上的统一也很重要。于是,具有包容性的、非人工化的自然神——天,而不是一位憎恶分明的人格神承担了这样的、在多元文化领地中信仰统一的任务。我认为,这种社会组织办法并非天然地独属于某一个国家,而视觉有更普遍的意义。现在,宗教受我这样一个当代艺术从业者的关注,我觉得是出于这样一个当下无法回避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由经济往来所驱动的世界全球化被民族主义国家的隔阂打破之后,我们该如何促成整个世界整合和联动?

宁波凤凰禅寺里的车神,图片来源:张晓
Q:在这篇论文的筹备过程中,你会与哪些人做交流?
A:与有宗教、人类学、哲学背景的朋友交流比较多,与艺术界的人聊的少。同时,我也保持着与身边亲密的、没有任何艺术或者学术经验的亲友的交流。我工作的出发点源于展览策划的上手经验。在做过很多展览后,我会从展览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会试想一名普通观众能从一场展览中能够得到什么。这就让我回到开放的图像,在这样的图像中,没有艺术经验的人也完全可以用自身的经验进入、理解一个展览,或许,在激起兴趣之后,他们会继续往深处探索。我想说的是,哲学、科学、宗教的经验和角度表面看起来是种种学科建制,实际上是连接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人生观的通道,是本来就流淌在每个人眼球表面的经验。
贡布里希曾表示“没有一双无辜的眼睛”。策展就是去串接多重线索,让观众看到可能已被他们自己遗忘的“历史-心理”潜意识。一些秘密被揭示出来,它并没有超过观众本人,没有超过作品本身,也不是一个学科的注脚。它本身蕴含着我们所有人的经验。人与作品是连接在一起的,人与人也是连接在一起的。

池社,《作品2号——绿色空间中的行者》,1988年,图片来源:张培力
Q:你在寻找材料的过程中,有没有推翻过自己原本的预设?
A:一直在推翻。它不是一个目的论的研究,我最开始的预设更像抛砖引玉,需要获得外界——无论是我想象出来的“他者”,还是一些给我提供线索的友人——的反馈。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有一个重要概念是“涌现”(emergence),我们姑且可以简单理解为“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很多人可能自己都不能意识到的共通之处,最后就可以组织、涌现为统一的整体。潜意识的“合”在策展中特别重要,或者说,它就是策展的本质。

王晋,《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2008年,图片来源:M+博物馆
Q:编辑工作的经验对策展有哪些促进作用?
A:至少可以让自己的思维变清楚。我本身的思维习惯是发散性的,很容易松散,所以通过写作让思路清楚、富有逻辑还是挺重要的。瓦尔堡(20世纪初德国艺术史家,现代图像学的创始人)对我影响很大,他提出过一个“好邻居”的研究原则,就是当你有一个疑难——比如关于花卉的艺术史上的疑问——需要解决的时候,他会去查看他的书架。他的书架不是按照学科划分的,而是按照主题。于是,花卉的问题可能被讨论花卉的艺术史书籍周围的,哲学、宗教、语言学、神话甚至是关于魔法与占星术的书所回答。他的书围绕某一中心理念或主题被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差异又相互毗邻的互补的世界。凭借此,他不停地在各种学科里跳跃思维。我觉得这也比较适合我的大脑节奏。

比如说,去年在北京当代·艺术展2020“艺述”单元做的主题展“金汤”,艺博会就是这个展览的“好邻居”。我从几年前就开始就幻想能在一个博览会上去呈现这次展览。后来疫情来了,大家都陷于某种末日情结的惶恐之中,我就更觉得这是一个探讨即将面对分水岭的新自由主义议题的好时机。但这些问题落在一个展览的面貌上,又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史中贵重金属所折射出的图像学意义在当下现实中的回应,金色内部流动的超越精神与世俗美学的冲突,以及虚幻又真实的经济焦虑如何驱动了整个社会的欲望引擎,想把这些宏观的问题串联在一起,理性的书写、归类和分析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Q:做独立策展人与以往有哪些变化?
A:从艺术机构中抽身出来,肯定有所失也有所得。但我相信“不破不立”这句话,也相信,很多事要实践后才知道能不能行。做独立策展人,我还处于尝试的阶段,或者这样的阶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美术馆的工作让我积累很多经验,可以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培养了与团队,以及与艺术家的共情能力,对此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也很感恩。但我也知道,人生苦短,感到麻木了,就要赶紧找出路,不能停下来。(采访、撰文/孟宪晖,编辑/叶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