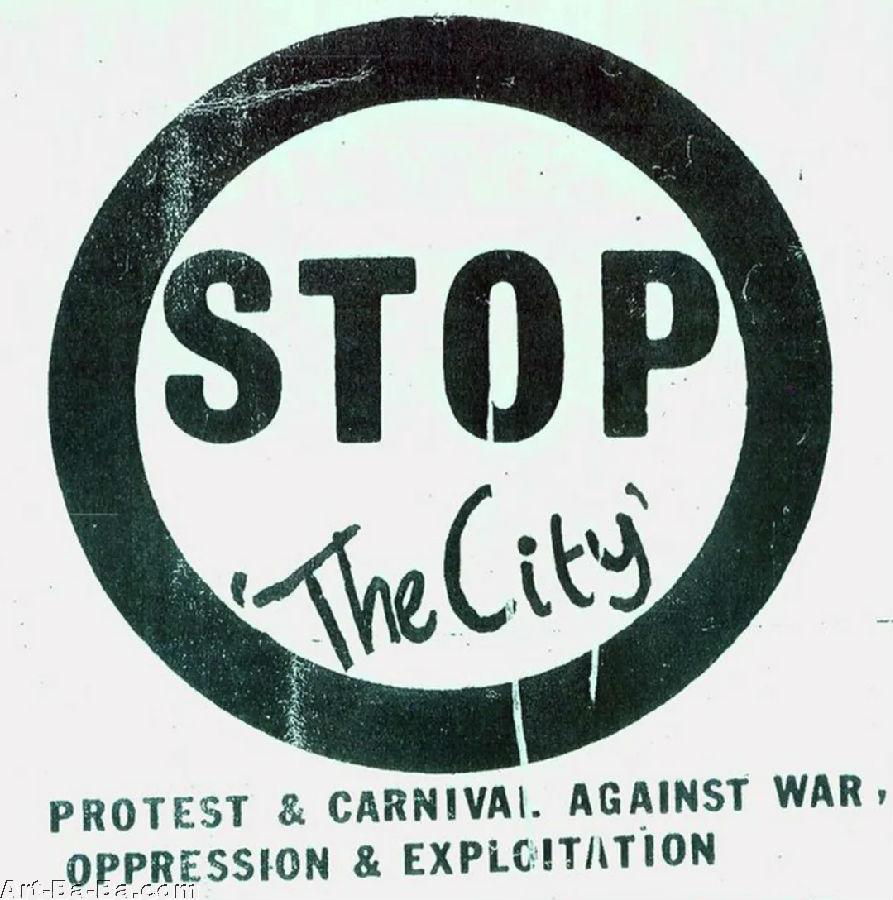来源:ArtReview Asia
文/Adelina Chia
电力站(The Substation)今年为其年度艺术节Septfest(3月4日—28日)发布的预告视频有着伤感的基调。这一持续整月的艺术节通常于九月举行,以纪念电力站的成立。伴随着屏幕上该建筑内灯泡闪烁的镜头,以及来自过去诸多活动的纪录影像,现任联合艺术总监瑞卡·迈特拉(Raka Maitra)在画外音中说:“电力站将在七月底不复存在。一度显而易见的事情会消失。因此,我们送给新加坡的告别礼物是关于边缘和边缘人群的,这点也很合时宜……电力站在此停驻已有三十年,它是边缘人群唯一的避风港。我很害怕我们也会被遗忘。”

Speak Cryptic,《如果你知道歌词就一起唱》(Sing Along If You Know The Words),2019,壁画
作为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独立艺术空间,今年7月,电力站将不得不离开已有30年历史的场地。位于亚美尼亚街45号的大楼将进行为期两年的修整,之后它将变为多租户艺术中心重新投入使用。翻修完成后,电力站将回到这一空间,但彼时它必须与其他团体共享该建筑。为电力站提供资金及场地的国家艺术理事会(National Arts Council,NAC)的一位总监在写给《今天》报纸的一封长信中解释说,考虑到“艺术界的日益活跃,艺术家及团体也在持续寻找能够支持他们工作的实体空间”,这一(共享)模式是必要的。他补充说,即将进行的翻新工程对电力站的管理人员来说并非新闻,他们也一直在“定期参与”这些进展。
出自系列“城市会改变,人会死去,你所认识的一切都会离开”(cities change. people die. everything you know goes away.) 2018-2019
他的意思很明确:NAC并没有做电力站意料之外的事。这一“危机”已经酝酿了多年。但电力站空间遭到削减的消息还是引起了当地部分艺术界人士的惊愕,其中多数争论都围绕该机构的历史和象征价值。对于许多人而言,电力站代表了一个来之不易的自由表达和实验的空间。其创立者,剧作家兼导演郭宝崑(Kuo Pao Kun),是当地艺术史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郭宝崑以其见证了新加坡历史和身份的多语种嬗变及对其艺术的支持而闻名,他同时也是许多艺术家的导师。他在1990年成功游说政府建立了电力站。该艺术中心的场地位于新加坡市政区(Civic District)一个发电站旧址内,拥有一个黑匣子空间、展厅、工作室和其他工作空间,整体上展现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气质。多年来,它以展示年轻视觉艺术家的创作、实验性表演和独立音乐而闻名。对于具体的某一代艺术家来说,电力站的地位与郭宝崑的精神遗产息息相关,也因此是神圣的。戏剧教育家、1996年至2000年担任电力站艺术总监的沙士德兰(Thirunalan Sasitharan)在脸书上发文提问:“为什么电力站在建筑改装后不能拿回所有的空间?”他诉诸电力站的谱系和成就:“难道它没有反复证明过自己的价值吗?难道还有这么多其他与其紧迫竞争的对艺术空间的需求,以至于(这个)总体规划要求抹去一个由可谓是新加坡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艺术家所创立的极负赞誉的艺术场所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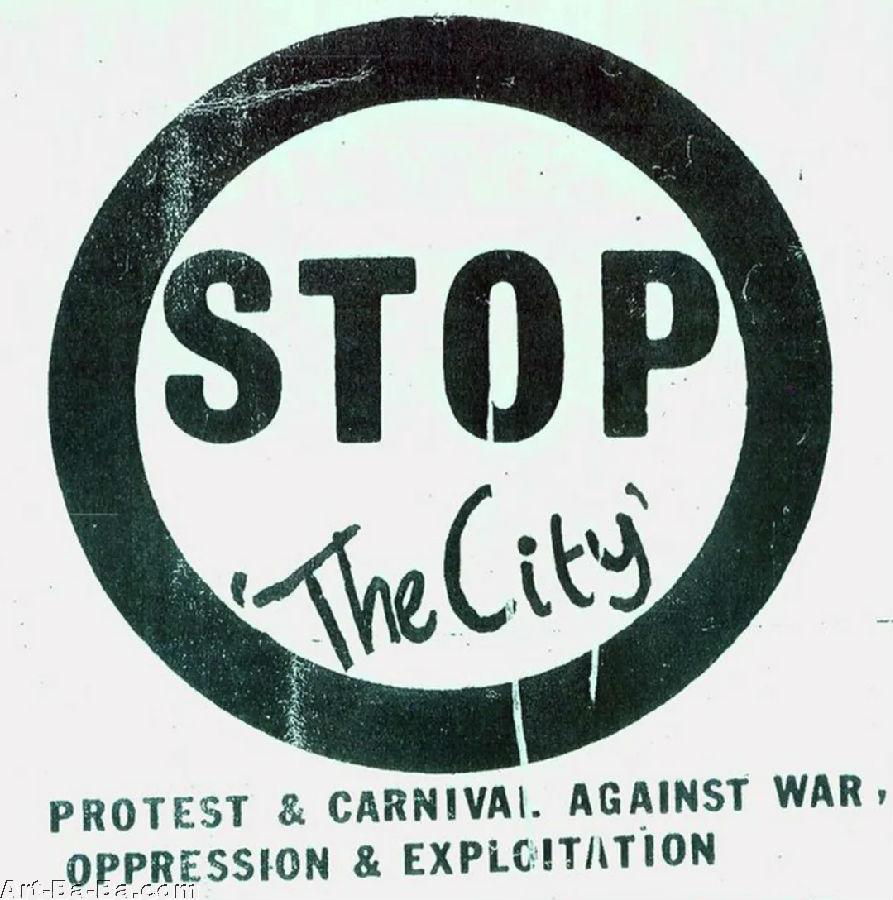
史蒂芬·史库塔斯(Stevphen Shukaitis),《停止城市……再论》(Stop the City… Revisited),2017
出自电力站 2017 年展览“规训城市”(Discipline the City)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问题在于电力站是否应该在失去原有空间的情况下继续作为一个组织运作(毕竟艺术中心是根据其场地的历史命名的)。2015年到2019年担任电力站艺术总监的艺术家、策展人黄治维(Alan Oei)认为将是一种无意义的屈辱。他在脸书上写道:“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必须离开这座建筑,那么电力站也应该永久关闭。这将是我们不得不集体承受的伤疤和耻辱。而如果我们有朝一日忘记了它,那么(它的)缺席本身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指认。”电力站迁出现址真的是一件如此糟糕的事情吗?它的创办人并没有把这个机构的观念与场地捆绑。1995年,郭宝崑在给电力站的临别赠言中,引用了该空间25周年纪念刊物中的内容:“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离开这个岗位而说再见。因为电力站首先不是一个物理空间。它更像一个精神空间,一种文化意识,一个一时冲动成长为的强烈欲望,后来成为一种理想,最后成为现实。它已经成为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去表达和接受新的、不同的、有挑战性的事物的更大自由。”
电力站入口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被创始人对艺术中心的愿景所束缚。但即使是对于他最忠实的、最本本主义的追随者而言,郭宝崑的言语也一定是指向了一种灵活性。时代在改变,也许电力站也是时候改变自己了。对其领导层而言,迁出现址或许能为其提供一个机会,去批判性地重思自己的架构、身份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位置。多年来,电力站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抵制商业主义和国家主导的“创意经济”工具化倾向的替代空间。也许在1990年代它确实处在一个激进的位置上。作为新加坡第一个致力于发展艺术的独立空间,它的成长伴随着当地当代艺术场域的形成和先驱一代艺术家——如唐大雾(Tang Da Wu)、李文(Lee Wen)、哉昆宁(Zai Kuning)等——个人事业的发展。随着当代艺术基础设施在2000年代变得更加饱和,电力站不得不与更新、更时髦的艺术场馆竞争,如滨海艺术中心(Esplanade—Theatres on the Bay)、艺术之家(The Arts House,旧新加坡国会大厦)和翻新过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它到底还是坚持了下来,仍旧打着它不论形式地支持各种需要“缓慢”发展、实验性和过程性创作活动的旗号。但电力站究竟是否如迈特拉所说,是“新加坡边缘人唯一的避风港”?我不太确定。单就视觉艺术而言,规模较小、更为灵活的机构正在兴起,比如致力于研究和展览制作的灰色计划(Grey Projects)和艺术合作计划soft/WALL/studs,以及Supernormal和Coda Culture等独立机构。这些机构也得到政府的资助,但是以项目经费的形式,这在总体上给了他们更大的灵活性。诚然,这些机构都偏重视觉艺术,而不像电力站那么强调跨学科模式,但它们的较小规模和较高专注性也意味着转型应是一件易事。例如已经搬过两次家且目前没有实体空间的Supernormal,却在最近的新加坡艺术周上在吉尔曼军营艺术区(Gillman Barracks)做了一个快闪展览。这些空间的精神也是不同的,它们较少受到中心—边缘、压迫性的国家—自由的艺术家、开放—封闭等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束缚。这似乎反映了新一代从业者的精神,他们在思维和创作模式中更偏好开放性和合作性——这在今天或许是更有效的模式。
Post-Museum,《三联九回肠》(Bukit Brown Index #132: Triptych of the Unseen),2018
在电力站去年举办的“空间,空间们,制造空间” (Space, Spaces and Spacing)会议上,学者契连·乔治(Cherian George)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认为,新加坡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面临民主的衰退。当年吴作栋总理“昭示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允许了更多的开放性。乔治补充道:“我甚至可以说,如果电力站尚不存在,且今天有一个郭宝崑提出建立一个这样的空间,现任政府会拒绝这个想法。电力站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一个狭窄的机会窗口期间出现的,这个窗口自那时已经关闭了。”电力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在艺术界基础设施尚不发达且政治气候较为宽容的年代填补了一个空白。在当时看来它的架构是对的:一个独立的单体,接纳一切非商业和实验性事物。但时过境迁,电力站的规模今日看来反倒显得笨重,仿佛它在被自身的象征意义压垮。连这栋建筑都吱吱作响。而它周围的世界早已变得多样化和颗粒化。它的资助机构国家艺术理事会(NAC)也变为了一个更加庞杂的官僚机构,他们大方的资助也附带着更多的条件。考虑到新加坡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电力站在当地艺术史中的角色,它如果永久关闭将会是一件憾事。它也许还能生存,但一定不是以现在的状态。它真正需要的是一场灾变式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