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王子云

相比往年,此时此刻会有很多可以回望的展览、实践和作品可以被筛选、整理和讨论。然而,当2020已成档案之时,页码上歪歪斜斜记下的字迹却有着大段的空白和阻隔,恐惧和笃定共存。于是,我们试图从一个机构的视角入手,不止“照看”这一年,也试图超越时间性的去探查艺术生态中一些并不喧闹,却历久弥新的追求和探索。

泰康空间十周年展览“从复兴门到草场地:泰康空间2003—”,展览现场,2013

“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5
十一年来,泰康空间从2009年草场地新空间的开馆展览“泰康收藏摘要”起,开始有一定文献意识地将自身的收藏、展示体系与机构档案的建立,看作是两条并驾齐驱的道路。此后一些重要的节点,2013年“从复兴门到草场地:泰康空间2003—”展览在纪念的同时梳理机构的前史与历史,将空间的过往汇聚成一套“家庭影集”,以图片文献的方式呈现,并将手稿、日记、文献和实物作为展示的方法。2015年展览“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举办,这是泰康空间在摄影史研究的基础上举办的一个标志性的展览,通过三位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沙飞、吴印咸、罗光达拍摄的三张白求恩的照片考察开始,对白求恩形象(影像)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塑造与传播进行考证,揭示出一套摄影生产和美学机制。这是泰康空间文献研究与展览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正式的尝试。同年,设立文献与档案中心,成立的初衷是想以现有的文献收藏和积累的图书资料,成立一个主题性的图书馆。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渐拓展开来,一方面不断地扩展文献资料的收藏框架,另一方面也在很多展览中将文献研究、档案、展览集合,探索一种学术研究的新方式。2019年以泰康的收藏体系为线索的第三次公开展览“中国风景:2019泰康收藏精品展”举办,在此次展览中文献档案的呈现与艺术作品共同构成展示的整体。2020是泰康空间的“文献年”,一共推出3个研究性的文献展,展览由文献与档案中心的研究员和展览部的策展人来策划,既将他们阶段性的研究课题以展览的方式呈现,也有围绕档案这一概念本身提出的假设,同时也更为系统性的总结现阶段的机构实践。

“中国风景:2019泰康收藏精品展”展览现场,文献区域局部,2019

泰康空间文献展“自然观:十七年时期的艺术与水利工程”,展览现场,2020

十二个月以来,尽管疫情封闭造成种种困境仍在继续,泰康空间还是结合自身的理念和现实继续推动着当代艺术的展览与实践。过往与今年所共同走出的路径,使得泰康空间更加确定在档案的研究与展示,档案的作品性和作品的档案性,机构收藏的档案化和研究性之间可以互相承接和转合的关系,并在这一年的展览实践中尝试以此为出发点,回溯已经成为历史的时间,复杂纷纭的此时时刻,以及诡谲莫测,扑打面颊的未来。
以下,笔者将从不同的角度,分别与唐昕、苏文祥和许崇宝共话时间中的那些年和这一年。

Q:
2009年的时间节点,泰康空间确立了2.0版本的机构理解“追溯与激励”,追溯过往的历史特别是中国20世纪,鼓励当代艺术的创造和实验。就“追溯”而言,这一理念确立之初是否就已经包含了将“档案”的再发现和研究作为工作重心的倾向?之后,是否有一些内部的史料收藏也围绕此展开呢?
“追溯”的指向,它的含义实际上是指历史性,也就是确定了一种机构看待当代的历史观。所以很快我们就形成了机构的方法论:从1942年以来看当代,当时还没有覆盖整个20世纪,应该说是将20世纪中期与当代艺术连接到一起,看这两段历史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和认识,不能局限于它本身的范畴,而要放到更大的历史框架中去看。“追溯”其实主要指的是这样一种思考方式。
在展开研究时不可避免的要使用研究材料,通过各种材料去反观历史,研究艺术的发展。肯定要看原作,但看原作品机会有限,是远远不够的,就要去找去搜集各种历史材料,逐渐就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慢慢的在日常研究中、展览项目中对资料的运用也比较熟悉了。另一方面,出于对机构自身展览项目档案的梳理的需求。2015年,就正式成立了文献与档案中心。

“泰康收藏摘要”展览现场,泰康空间

《泰康收藏摘要》出版物掠影,2009
从档案角度来看,泰康空间自身的机构文献,泰康的收藏(艺术作品与文献),中国摄影史和当代艺术相关的文献等等都可以看做是一份历史档案。对于这份档案的所有机构,你怎么看待它们与历史书写的关系,与当下的关系?
实际上你刚才说的这几种类型的档案,都是不同角度的历史的证物。我们通过艺术史,一方面可以看到艺术自身的发展和走向,同时也可以看到它对相应时代的反映,以及它跟时代的关联性,也就是被卷入时代浪潮中的个体,他们的创作生产与所在时代的关系。所以艺术是特别丰富,而且反映的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图景。不论是文学、美术还是摄影,它们都提供了一种进入历史的视角和理解历史的可能性。
比方说像摄影,泰康收藏摄影,是把摄影作为20世纪早期的一种西方的技术媒介来看待,覆盖摄影进入中国之后的发展全过程。所以摄影收藏并没有受到1942年这样的断代的限制,而是聚焦它如何在中国落地并被使用,它在中国的命运,它在本土生长形成的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那一下就连带出来对摄影与政治、经济,还有方方面面的这种关系的观察。所以一个是宏观上去看摄影这种媒介跟其他问题的关联,另一个就是具体的,去看它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其中的题材和内容、拍摄者或图像生产者、观看者等。所以当我们把摄影作为技术媒介放到时空当中去,可以看到太多信息了,这份档案它就有了多种价值和意义。泰康收藏中绘画方面也同样。
泰康空间自己的那份档案呈现的是17年以来这样一个本土空间,它怎么生长,为何存在。未来这份机构档案公开时,至少是一个21世纪非营利机构的样本。

佚名,北京电影制片厂建厂初期工作人员标准照相册,每张4x2.5cm,银盐纸基,1950s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昆明春城照相馆等,肖像,尺寸不等,银盐纸基,1980s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政纯办,政先生,120x155.7cm,彩色照片,2007 ©️泰康收藏 TAIKANG COLLECTION
从最初泰康空间有意识的将档案化的研究和展示,作为阶段性反思的工作方法,这些年来有哪些契机促使这一工作不断的拓展和推进?
首先,我个人有一个习惯,在早期我做完项目后会整理一个文件夹,现在它们就变成最早期的档案。另外,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书架,收集研究用的文献。随着空间研究性图书和文献资料的量越来越多,我们开始觉得要有思路、有框架、有计划地去做它,所以对它的关注度就又不太一样了,这是一个转变。此外,我在给泰康做收藏的时候,摄影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它除了艺术创作媒介的属性外,还具有很强的文献性。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观看历史、理解物质材料的启发,后来逐渐形成了相对清晰的意识。
到了2013年,泰康空间10周年时做了一场机构回顾展,包括每年大事记的梳理、手写稿、图片、出版物、对谈等等,那是一次运用在自己机构身上的大规模使用文献的展览。经过那次之后,展览项目中使用文献的经验又有了变化。
泰康空间日常的展览逐步也成为更注重研究性的展览,或者说对历史的研究成为一个团队共同的方法论。比如,2012年的“华北农村1947-1948”、2015年的“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等,对于文献认识、对历史的观看,就不光是在讨论的层面,而是把它放到展览实践过程当中去了。每一个人必须要去做研究以及资料收集,所以文献又变成在工作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和一种方法。接着就是到了2020年泰康空间文献年,是文献与档案中心成立5年时间的总结,我们希望对这部分工作,针对文献的认识、意义和使用,有个阶段性的讨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尽管没有完全公开,但据我所知泰康的收藏体系和泰康空间的文献收藏,已经颇具规模,有没有考虑整理之后形成可以共享的学术资源,并进一步的电子化,建立类似于香港AAA一样的线上开放数据库?
文献公开其实是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如果外部条件成熟的话应该没问题。因为本来我们现有的资料也是可以对学者或有需要的人士小范围的采用预约制开放的。但如果要做文献资料的电子化,目前从人力等各方面条件还达不到。因为资料越来越多,除了一系列电子化工作之外,还有在哪里展示的平台问题,谁来交流,管理的人员和制度问题,需要有对一整个链条的考虑,才能成为既方便别人使用,也方便我们管理的平台,所以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泰康空间机构档案的部分会公开。我们把17年的梳理,具体工作、项目,机构不同阶段的成长,理念、方法、关注的问题,都会包含在内,之后会通过一个新改版的空间网站公开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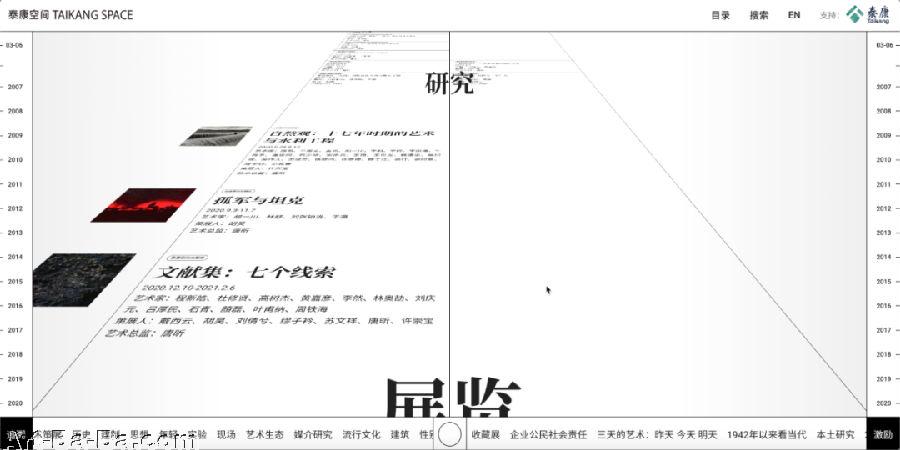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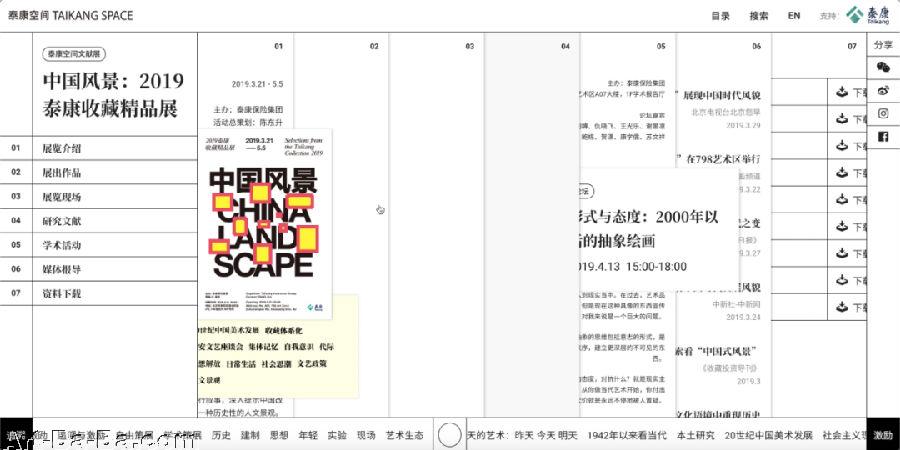
即将上线的泰康空间线上机构档案预览
非常巧合,2003年“非典”之后泰康空间成立,这一年你们的工作也因为疫情深受影响。作为一名机构的负责人,为何将档案作为本年度工作的重心,是不得已为之,还是主动的采取措施拓展机构工作的方向和方法?这是否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间节点?
我们是在2019年底的时候,确定2020年的工作是文献这个方向。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要梳理泰康空间机构发展的档案,就是对泰康空间成立至今的梳理,盘点整个机构发展历程,其中不光是学术工作,还包括机构不同阶段的成长,理念、方法、关注的问题,还有团队的架构等等。从成立文献与档案中心开始,我们的研究员和策展人的工作就有了差别,有不同的岗位、职责。目前学术团队在空间的占比超过一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希望研究员不仅做理论上的研究,还能介入到机构的展览实践的这种生产当中。这样实际上考虑的是把研究员作为策展人的一种储备。2020年希望把策展人的工作做另外一种调整,就把展览的任务交给了研究员,他们已经有了好几年的资料、阅读和问题的积累,应该有机会转化呈现出来。
2020文献年也是希望探讨对于当代艺术机构来说,到底什么是文献、文献性,什么事物带有文献性、什么可以被称为文献展、展览中的文献与作品有什么区别,等等。我们在2020年这样一个文献年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在机构内部、在行业里进行一些讨论,并且提升自身对于文献的认识,实际上是空间策展人和研究员都参与讨论的。疫情也有些影响,就是展览的数量比较少。主要是泰康空间这两年,本身注意力也集中在自身盘点上,疫情正适合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内务工作和美术馆筹备的研究上。所以也空间文献年的安排不完全是疫情的影响,综合起来就变成今年这种状态了。

除了机构工作人员的角色,你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并且也在2009年发起过“51㎡”的实验项目,这个项目试图从哪些方面促成和推动泰康空间转折性的面貌?
我还没有加入泰康之前,就跟唐昕认识了,那会儿我们应该都面临着转变的契机。我那会儿刚从上海来北京,一直是有一个想法,很像今天的90后艺术家那种感觉,刚毕业还比较年轻也喜欢与人交往,认识了很多年龄差不多的朋友,就觉得这一波人挺有意思的。当时想如果能有一个机构,有一个空间,可以持续地为这些年轻艺术家做展览就好了。有天唐昕到我们家来,我就讲了这些想法、计划,还有大概的名单。她说我们也做过类似的尝试,你到我们这来做吧,我们来提供支持,所以一拍即合。“51㎡”这个项目,其实是我们俩一起完成的,我们一起去探访了几十位艺术家,一起讨论,一起策划。后来非常认真慎重地确定了十六个艺术家,每三周开一个展览,这么高的频率,也突显了这批艺术家创作的面貌与之前艺术圈里普遍关注的那些艺术家有显著的不同,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现在看来,当时决定做新一代年轻的艺术家,是在泰康空间1.0版本的机构理念“鼓舞与激励”时已经积累下来的想法了。所以我在想,肯定唐昕是早有准备了,所以才能一拍即合聊得起来,才能搭得上。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巧合甚至预言,都为后面泰康空间的工作做了一些铺垫。

“51㎡”项目艺术家讨论会,2010

“51㎡:7# 胡向前”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0

“51㎡:8# 辛云鹏”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0

“51㎡:12# 马秋莎”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0

“51㎡:10# 卢征远”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0
Q:
在此之后,你继续推动着机构展览项目的实施,但也在尝试从“档案”出发,展开研究和展览有关的工作,比如“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2015),“日常与革命:黄山、庐山的两种风景”(2018)等,“1949:艺术的选择”(2019)这其中有着哪些主动建立起的学术线索?
我现在想想,如果总结的话,的确有一些能够串联起来的线索和关系。但在之前完全没有主动也没有预设,都是一点一点的像挖洞一样展开的。我个人认为,在泰康空间的工作经历是一种互相激发和生长的感觉。最初我连吴印咸是谁都不知道,但伴随着自己越来越深入地站在机构的学术视野当中,也包括看到很丰富的藏品,后来很快地进入到了对中国摄影史的考察,并且对从摄影展开的政治图像的生产和使用产生了浓厚兴趣。比如很多经典的历史题材的绘画,从构图或者说画面的布局等,都参考了早期摄影的图示,这里边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做。
2015年空间关于白求恩的展览,一上来其实有点无从下手,但当时我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白求恩的这些影像我们是了解的,但是它到底是在怎么样环境里面产生的?又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当时一起做策划和研究的三个同事,觉得有必要去实地田野调查,就租了一辆车,大概三天时间,把我们能知道的白求恩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就用车轮去丈量了一遍。进入到影像生产的地理人文环境之后,确实产生了更深层次的体会。我们带回了一些实物的、影像等各种形态的材料,也尝试在展览中实现了带有一些创作性的文献档案,具体的这里先不展开说了,想了解的话可以看我们去年发布过的一篇文章。

“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5

“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展前实地田野调查,五台县松岩口模范病院,2015
泰康空间有丰富的现当代摄影收藏,特别是一些老照片,你们在具体的项目实施中为何会聚焦这一媒介的创作,更强调这些摄影的档案性还是作品性,二者如何调和?
从摄影的角度界定它挺难的,它既具有作品性,因为它有作者,有构图、布局、光影在里面,也具有一定的文献性。但我们可能在更多的时候,还是要看问题意识切入的角度。比如像吴印咸这样的个案,我们可能既要强调他作为摄影家的身份,体现他在摄影艺术本身的独到之处,或者他在摄影生态中起到的作用,强调他的作品性。但如果呈现的是一种问题的话,例如将他拍摄的白求恩做手术的照片,放到“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里面时,除了其作者性外,它的文献性在此处肯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考量。
在我参与的展览中,更多的还是从问题出发,随时调整眼光来处理它们的文献性和作品性。当然,有具体作者的,肯定会首先强调他的作者性、作品性。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首先分析作品,而是关注在作品背后勾连的现象和问题,这是作品档案性的体现。所以这些摄影,我首先把它认定为是一种图像和媒介,而非停止在摄影艺术这个概念,然后基于问题的结构去看待它们。


“日常与革命:黄山、庐山的两种风景”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8
在你策划的一些研究性展览中,经常会在具有一定线性的时间叙述中横向切入与当代艺术有关的线索,并将文献与作品相关的主题并置,这一策展方法使用试图带给观者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
如果粗略地按阶段来划分,传统的沙龙展览可以定义为1.0时代,这肯定是相比较起来最没有问题性的做法。到了第二个阶段,现代美术馆开始有意识地按照流派、时间或叙事线索来策划展览,但这种方式到了今天也已经成为一种套路,尤其值得策展人和艺术家反思。我自己在想,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策展实践,或许不是只做艺术作品的策展,而应该是一种非常综合性的表达,一切都可以进入策展,都可以进入展览。
其次,在某种特定类型的展览中,并置加入更多的材料,或者横向的多领域的证据或素材,或是某种关照性的内容,都是很正常的方式。如果可以这么定义的话,历史性的摄影和当代的艺术作品的并置,对于双方来说,都各自扩大了对它们的认知,获得了另外一种与其平行的对某个问题的交集和认知。现在,除了针对策展来讲,其实艺术家比策展人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要打破某种套路,打破原有的理解上的套路,打破做法的套路。所以可能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反思,到底展什么,到底是不是只有唯一的办法,到底能否给予多重的观察和多重的经验……

“日常与革命:黄山、庐山的两种风景”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8

“1949:艺术的选择”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19
不管是之前围绕白求恩这一英雄形象所展开的图像考,还是此次“文献集:七个线索”展览中以摄影师杜修贤(1926-2014)为中心所展开的考察,你们试图在历史、作品、档案和个体之间建立了哪些研究方法和路径?
再回到你第一个问题,现在跳出来看,是存在一条线索。杜修贤这个案例正是基于之前的一些铺垫和积累。有一次,泰康买了一批摄影古籍,一般在入库之前,空间策展人是可以看一看的。当时我一看到杜修贤这批手稿就特别感兴趣,他以摄影师的专业身份,与权力核心的人有书信来往,所有书信里面讨论的全是从摄影展开的问题。当然那会儿还没想到要做成展览,但这些文献就像种子一样在我脑子里面存放起来了。泰康空间今年着重提出文献年,我就开始仔细在我的素材库里面搜索挖掘有哪些可能,就想到了杜修贤。通过这样的一位摄影师,可以管中窥豹尝试着去看背后隐藏的那种激荡的社会面貌。摄影作为一种技术和媒介恰恰连接了这样的权力和网络,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所以在“文献集:七个线索”简要呈现了一下。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党史很感兴趣,所以基本上碰到这一类历史图像,我都会把它放在革命史或者政治背景中做考量,或者说有点像当代艺术图像分析一样。其实从图像本身获得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当你从他的生活、交往,从当时的环境、政策,或是其他的侧面证据来观察时,反而更加有助于理解图像本身。它为什么被创造出来,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样的思考方式可以激发新的对图像的观看路径。



泰康空间文献展“文献集:七个线索”,“杜修贤手稿档案”单元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20

泰康空间研究员
文献与档案中心负责人
作为2015年成立的文献与档案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和研究员之一,除了图书馆这一初衷,中心建立之后有哪些方面已经确立和逐步展开的工作方向?
这个部门成立的初衷是为泰康空间的研究性项目从文献档案角度提供学术支持,基础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与泰康空间学术体系相呼应的图书馆,二是梳理泰康空间成立以来的展览项目档案。当然泰康空间也鼓励研究员从自己的学术兴趣点出发展开文献研究,并转化为空间的项目生产。




泰康藏书掠影,依次是“大地魔术师”展览25周年出版物、《建筑的元素》、“连续撞击”展览出版物、《申报馆 剪报资料·上海卷 淞沪抗战专辑》
泰康空间近年来的展览实践,越来越多的文献与研究中心的研究推进结合,是否可以说研究中心的工作,为展览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即思想、理论和方法?可以从你参与的一些案例展开谈谈。
展览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来源于策展人,在一些具体展览中,文献档案中心的同事会作为研究员参与,配合策展人的工作,对思想、理论和方法,与策展人有一些讨论。比如我参与的《1949:艺术的选择》,基于我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美术史研究的兴趣、接触到的历史材料、走访的机构与学者,去丰富展览的内容构架。还有一些基于文献的研究工作,是在展览开幕后逐步深入的,如《肖像热:泰康摄影收藏》在展览期间对历史当事人的采访,为我们理解照片提供了生动的语境。
从档案的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和展览项目实施中,常常会将作品文献化,文献作品化,在你的工作过程中,这些尝试为策展与展示、档案和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方法?
作品是表达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它与文献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化”只是一种展示上的技术处理,比如装裱方式、在展厅里与其他材料的位置关系、呈现形式等。这些处理也许会以打破对某种艺术媒介语言的传统认知为代价,但可以支持将艺术作品放置于一个立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祛魅式的讨论方法。



泰康空间文献展“自然观:十七年时期的艺术与水利工程”,展览现场,2020
除了历史文献档案,以及泰康空间的藏品,你们也常常会将一些委任的创作放在展示的线索中,是否有担心这些这些新的作品太过寄寓于一种历史语境而缺乏独立性,该如何看待它们与诸多文献丛簇的关系?
在以文献研究为主要面貌的展览里基本不会以委任创作的形式邀请新作品参加展览,而是这件作品由当代艺术家近期创作、契合展览所要讨论的问题,邀请进入展览作为一种当代视角回应文献,形成一个话语网络。
你在今年5月份策划展览“自然观:十七年的艺术和水利工程”(2020),也在此次“文献集:七个线索”展览中以“劳动与友谊”为主题参与到年度项目中来,前者强调在一个时期内劳动和建设对新的自然观形成的推动作用,后者强调劳动所建立起来的国际与人际之间的情谊,这两者存在研究的延续性和关联么?
有直接的关联。“自然观”展览里的劳动场景以及2020年初以来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的对劳动问题的讨论、对白左的批判,让我意识到“劳动”不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方式,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与集体主义等观念作为一个总体性工具被用于塑造新中国人民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国家间的交往中尤为凸显,比如在援建坦赞铁路的工作者们身上。所以借泰康空间第三次文献展之机,将新中国各类表现劳动的图像资料与当代艺术家以劳动、国际关系为出发点的相关创作,做一次开题式的综合阅读,后续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泰康空间文献展“文献集:七个线索”,“劳动与友谊”单元展览现场,泰康空间,2020
(本文根据作者与唐昕、苏文祥的访谈和许崇宝的笔谈编辑,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