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Ocula艺术之眼 刘曼堃

展览现场:“寂静春天来临前”,WMA空间,香港(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1月15日)。图片提供:艺术家。
香港年轻艺术家劳丽丽在香港中环非营利机构WMA空间的个展以“寂静春天来临前”(展期: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1月15日)为题,援引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被视为美国六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并进一步设问:在生态和社会危机导致全然寂灭之前(这个或这些临界点将随时甚至已经到来),我们还能如何行动?
相应地,艺术家在展览的五频录像装置作品中没有直接回应由卡森开启、近年来正急速扩充的生态讨论,而是从自己所在的团体“生活馆”(2010-)自反高铁运动期间成立以来在香港新界锦田的十年实践历程出发,借此次创作的类纪实影像作品记录并呈现与生活馆成员们的对话,由此从复数的个体视角为耕种伦理、个人与集体实践中的张力,新界土地的环境、生态和物种,以及香港社会气候的变化等议题打开层层讨论空间。

展览现场:“寂静春天来临前”,WMA空间,香港(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1月15日)。图片提供:WMA空间。
展览作品为时长约一小时的同名五频影像作品营造了一个沉浸式空间,并在视听维度上呈现出一种“极多性”。展厅入口的一道宽阔软帘,与两侧的投影墙,及房间尽头的显示器构成了作品的四个分屏。
四屏之间交错出现图像,以在空间内运动的节奏呼应镜头内容的切换。影像在种植到收获、生活馆的建成到拓展,以及郊野到城市的数个交叠的时空线索上铺陈,展现仪式般的耕种过程、工事与劳作、休憩与放空、乡间生活中的人、事,动植物,以及零星穿插在移动影像中的、时间切片般的胶片摄影。

展览现场:“寂静春天来临前”,WMA空间,香港(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1月15日)。图片提供:艺术家。
配合“复调“的影像,劳丽丽与音乐人黄衍仁和声音艺术家李颖珊共同制作的声效织成作品的经纬。借同行友人的说法,让人“置身展厅中仿佛站在田间地头”——蝴蝶振翅、虫鸣、雀鸟啁啾、人细簌往来、水声流动,黄昏时,嘈杂随田野上光线收束之声消失;转眼飞机轰鸣、燃烧的秸秆堆中火星噼啪。
田野录音之间隔着转场时渐起的弦乐旋律和击打声,既像沉郁行进的步伐,呼应展览主题的催促,也如艺术家所述,“重现了日常劳作中舒缓和安慰的伴音”[1]。环境音和旋律汇入耳机内,又成为艺术家与生活馆同伴对话片段的间奏。

展览现场:“保持缄默”,Tomorrow Maybe,香港(2020年1月23日至3月1日)。图片提供:Tomorrow Maybe。
“极多性”像是“寂静春天”这一意象的疏解和拒斥,在主题和氛围上与艺术家数月前在非营利空间Tomorrow Maybe的个展“保持缄默”(展期:2020年1月23日至3月1日)[2]构成对读;同时,“极多”也为单向度的电影时间线上行进的叙事提供了无数重组和发散的方式,令影像、声音与对话文本互相指涉,从而增加了观者经验和体察作品的路径。
当艺术家和友人围绕着”营役“感谈起对在耕田和其它实践中陷入不自主状态的困惑时,亮起的单屏画面中出现一群夜晚路灯下的飞蛾;又如当生活馆Kids Club的发起人之一,李俊妮讲述自己如何在一次身心不支的经历后不再“强撑”——屏幕中是一只在与镜头对峙的小跳蛛,接着画面开始摇动失焦,仿佛带入动物的视角,经历了从叶片上跌落时的天旋地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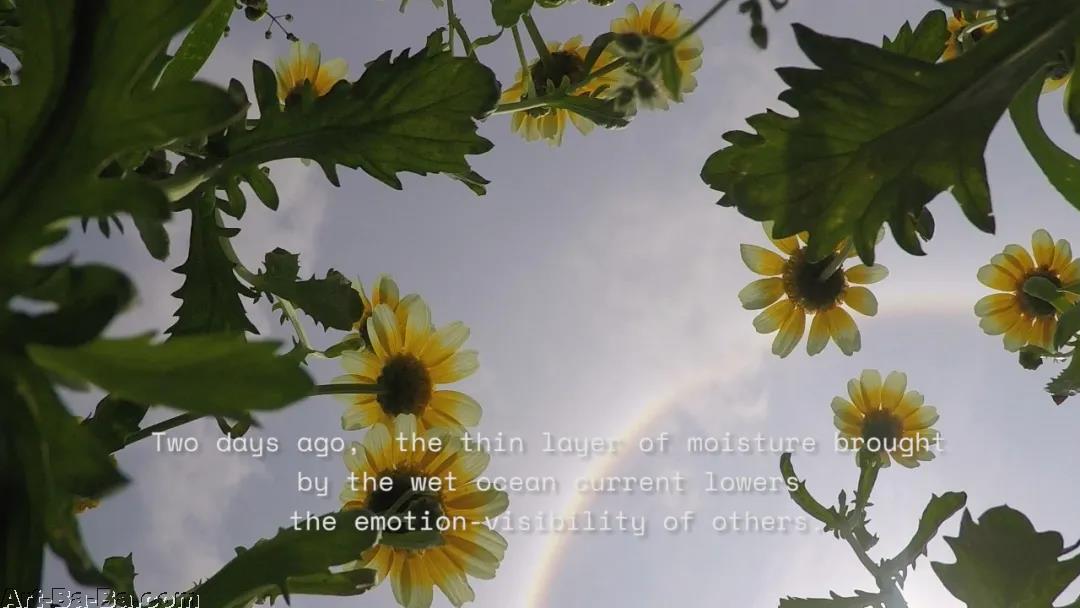
劳丽丽,《天气女郎》,2016。粤语英文字幕影像,6分32秒。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
这些镜头配合着对全景、特写和慢镜头等视觉语言的调度,在艺术家、对话者、以及生活馆周边生态圈中的动植物的视角间穿行,令观众在聚焦和出神的时刻被某一主体所捕获。
艺术家在过往的流动影像作品《天气女郎》(2016)、《飞天潜水艇》(2017)、《焉知》和《焉知之后》(2018)中逐渐建立起这种穿透性的视角,它往往配合着艺术家结合田野调查和虚构撰写的、叙述主体摇摆于人类和动植物间的旁白,从而建立对生态系统中不同持份者所可能抱有的欲望和意图的内部体察。个展“寂静春天来临前”则将这种建立影像的方法带回到它生长的环境中,还原它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生产认知,而体认又如何推动图像转化为隐喻,将隐喻建立为共感的场域。

展览现场:“寂静春天来临前”,WMA空间,香港(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1月15日)。图片提供:艺术家。
在影像理论研究者特丽莎·卡斯特罗(Teresa Castro)看来,移动影像消解了观看与被看的主客体分立,虽无法打破拟人法(anthropomorphism)在其它生命中投射人的意向性的惯性,却无碍其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这是由于镜头在表现其它物种的觉知能力(sentience)和生命形式时,已然对现代主义的思想禁锢进行了解殖——它不再承认自然-社会或人类-非人的二分法。[3]
与这一乐观论点相悖的是当代影像创作者在回应生态危机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如艺术家苏珊娜·德·苏沙·迪亚兹(Susana de Sousa Dias)为例,她在2020年一场关于人类世影像的线上讨论中反思了自己在《福特兰迪亚病症》(Fordlandia Malaise, 2019)中运用***拍摄的伦理问题:一方面,她试图从高空捕捉福特公司在自然、原住民群体和土地上刻下的殖民痕迹;另一方面,***视角内嵌着资本对下方地景进行窥视和统治的欲望,并在把观看体验带离体外的同时将人类与环境割离。[4]
苏珊娜的疑问提示了影像创作者们似乎无法走出汉娜·阿伦特指出的,随着望远镜、飞行器和卫星图像的诞生而将人类自身抛掷于自身社群、乃至地球之外的那种笼罩着现代社会的超脱状态[5]。与这一论述相印证,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提出自然和社会的二元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并非源自人类中心主义——正相反,启蒙主义的错误恰恰是否定人性而宣称一种超验视角。因此,与其将超越物种局限的希望寄于后人类论述,不如思考如何重建“人的维度”以及与周遭环境的联系。[6]

劳丽丽,《依存》,2020。静帧截屏。图片提供:艺术家。
问题是,如何做?这既是对如何生活、行动和感知,也是对影像创作和展示怎样能够不减少现实遭遇中的复杂性的提问。如果说《寂静春天来临前》(2020)对如上问题做出了回应,无疑是将“走出人类世”的命题强加其上。
然而,展览所呈现的在地、“极多”的视角所指向的艺术家及生活馆的整体实践提示了单纯在技术和图像政治层面的讨论生态影像的不足。在人与人,以及人与其它生命长期共生的复杂生态网络中,影像既非再魅的手段亦非再殖民的工具,而是成为创作者练习对他(它)者经验的关切的众多方法之一。
[1] 劳丽丽采访,2021年1月1日。
[2] 展期由2020年1月23至3月1日,详见“何倩彤访劳丽丽《保持缄默》”,
https://www.cobosocial.com/dossiers/lo-lai-lai-tomorrow-maybe/
[3] Teresa Castro, “The Mediated Plant,” E-flux journal #102, 2019年9月。
[4] E-flux, “Visualizing the Anthropocen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线上讨论,2020年10月1日,
https://www.e-flux.com/video/351120/visualizing-the-anthropocene-aesthetics-and-politics/
[5]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6] Tim Ingold 在“The Social, the Biological, and More—the Anthropology of Tim Ingold”线上研讨会的发言,2020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