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王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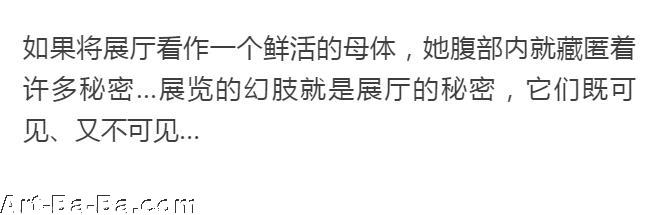
对展览幻肢的第三次揣测、描述与正视

我们总能瞥见展览现场有一些配角伫立、徘徊或试图遮遮掩掩鬼鬼祟祟地回避你我的视线,白天繁忙的展厅中,它们脸上就刻着“只是配角”的字样,告诉你不要打扰它们工作,每当夜幕降临,展厅大门紧锁,那些不被留意的配角们,便开始掠夺艺术品的主体地位从而成为一时的主角。我们或称它们为展览幻肢,因为它们从来不属于展品,却必须与展品如影随形,它们永远不会消失,直到展览不再是展览。
如果在我们脚下正踩着的这个艺术现场——寻求“艺术价值”作为最高真理的场域中,将艺术品比作是一种资本主义,那它们就是无产阶级,它们在普遍的价值体系里成为代表,却难以与“艺术真理”发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艺术系统里涌动着“政治正确的正义”,那么,人们应该为它们感到不公与愤恨,因为它们总是卑微地站在艺术的“背面”。
事实上,它们的存在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因为艺术家的作品时常需要从它们的口中诉说出来,可现实往往却是,人们向来只关心艺术作品,根本没人在意它们的存在,或者说,就算意识到了它们的身形,也必须视而不见!即便它们已经蜷缩在墙角低沉地承认自己只是配角了,可这还远远不够,人们多么希望它们能够消散于空气中,随着窗户或空调管道悄无声息地排出去!
相矛盾的是,它们偶尔也会因其体貌露出原型,而显得格外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扰人,可以说,策展人和艺术家为它们操心不已,目的正是要将其存在感将至零度。除非它们生来个性张扬,实在太过显眼,从而不得不将它们“美化”处理。人们会为它们搭建房屋,粉刷上保护色,或把它们贡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来暗淡它们从此不再耀眼,可惜这根本不起作用!它们依旧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并且,当你越发端详它们,它们就越嚣张跋扈,无限放大,直到你的视线再也不能从它们身上挪去,再也不能从它们身上挪去,再也不能挪去,再也不能……
我认识一位艺术家朋友,他的作品不能举办个展,并不是任何资历、体量抑或政治问题,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必须发生在群展里面才能生效,可能你会好奇,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只能发生在群展里?据我了解,这位艺术家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是关于艺术群体间容易被忽视的共生关系,也即是说,只有当一种关系被建立起来,成为其目标对象时,他才能基于这种关系进而构建他的作品。所以不难想象,在以往的实践中,他用作品切割空间、扰动看展逻辑、参与突如其来的开幕表演,甚至有一次临场回应同期参展的另一位艺术家作品,并连夜剪辑出一段录像。
我常常形容他是一位善于寄生的艺术家,或者说,寄生这种方式就是他的创作方法论,他必须借由他人的思考来牵引出自己的思考。所以你会看到,在他的简历里,从来都是各种各样的或大型或小型的群展履历,以至于但凡有机会能够看到有这位艺术家参与的群展,我都会在除了展览本身的主题和内容以外,花精力在展厅里辨认他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另一种展览提供的乐趣之所在。我想当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被指认的时候,最常被问及的问题恐怕就是你的作品是什么?是关于什么?甚至我为什么都没有看到?诸如此类的吧。
最近一次看到他参与的展览也超过七个月之久,那档展览是策展人有意在讨论关于“劳动价值与共同创作”相关的命题。同样,展览名单赫然提到这位艺术家的名字,但我在展厅里兜兜转转好几圈,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存在,我就在想,像我这样如此警惕和极具目的性地去寻找他作品的观众,都难以辨识,他又如何形成有力度的讨论呢?
直到最近,全球疫情的严峻形势下总算有星星散散的机构正常开放。我在一档展览里看着一部不长不短的录像,期间投影仪可能因为某种意外的故障,从而让被播放的作品产生了难以形容的视觉体验。我猛然回想到那位只参与群展的艺术家朋友,难怪半年前在现场我绞尽脑汁寻找“可疑的展品”都未能如愿,原来那些习惯又陌生的投影机、灯轨与射灯甚至刻意保留的杂乱电线才是答案之所在!
如此看来,这位朋友想必也是非常善于揣测策展人意图并作出应激反应的作品了。因为讨论所谓“共同创作”的边界伦理,恐怕早在讨论生效以前就已经有一些细节于预设的边缘处被忽视了——就如同展览中那些不被归属于展品却必须与展品一同出场的辅助设备们,在艺术家这里,正以一种奇怪的身姿,重新夺回其被观看的目光和被忽视的剩余价值,并如此根深蒂固地参与到作品的身形之中。

正视
如果将展厅看作一个鲜活的母体,她腹部内就藏匿着许多秘密,每当她送走最后一位观众和工作人员离开,秘密就不再是秘密,展览的幻肢就是展厅的秘密,它们既可见、又不可见,能够确定的是,它们必须与展品同在,它们不会因为布展结束的一刻而消失,而是因布展结束的时刻而郑重其事地成为“展览幻肢”。
在刚刚对展览幻肢的第二次描写中,我捏造了一位不存在的艺术家,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模型本身提供的一种思辨情景——当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辅助性设备不应纳入进作品范畴,就一如布展工人的劳动不应属于创造的一部分一样,其中的思辨远远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二元与简单。当然,我接下来要做的并不是要为辅助设备指认为艺术品而辩护,而是寻找能够激活其潜能的可能性存在于何处。
鲍里斯·格罗伊(Boris Groys)斯在谈及媒介问题时,就大肆使用过揣测一词,揣测,意味着一种对固有的、科学的、实证主义式的不信任和三思,揣测,至少是激发媒介意义的。“如果媒介表面没有察觉到移动、转移和困扰,那么媒介主体就看起来似乎十分平静,而正是这种内在的平静使得亚媒介空间变得特别值得揣测。”媒介的平静或许正是指征了一种理所应当的状况,正如那些“循规蹈矩”展示着图像、文本和影片的媒介载体,之所以不被重视正是因为它们只不过印证了我们对其一向的期望罢了。
而当代艺术现场的例外之处,不正是恰恰因为它是一个塞得满满当当的亚媒介空间吗?事实上,当一台正在播放着艺术家作品的投影机与一台没有通电的投影机及一台播放着商业广告的投影机,同时出现在一个展览空间时,它们作为媒介的意义与价值是不一样的,一如同样型号的投影机分别出现在展览现场和档案室内也有所不同。在研究媒介的知识中,当人们想要探究电视的机器内部运行方式的时候,就必须将电视机解除电源,与此同时影像消失,这也即是说电视机短暂地祛除了其作为媒介的身份,人们才得以研究。
再回到当代艺术现场,只有当人们开始思考和视检这样一个亚媒介空间的集合时,才能找到其细微的不同,类似投影机处境的其它辅助性物件之所以不被报以一种艺术性的目光去看待,也往往正是因为人们尚未视检到这个亚媒介空间,而徘徊在一个世俗空间中。
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宣称一台正在播放着艺术家作品的投影机就是艺术的投影机,而是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投影机短暂地与艺术发生过关系。谈论至此,我们的目的似乎变得更加清晰:
如何让人们重新拾起对那些辅助性设备的重视程度?摆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如何让其进一步与艺术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在这个只有展现艺术思考力才能彰显价值的场域里面,理论上,似乎只要让展示媒介自身获得一种价值——让人们得以卷入重新思考艺术的动作里,那么,媒介载体也便能够脱离其仅仅是展示,而毫无艺术价值的处境。人们得以在这里借载体揣测媒介意图——那些亚麻画布、纸张、电视机和蓝牙音箱们,将协同一跃成为一个宏观的空间装置。
当然,这早已不是杜尚现成品的年代;也似乎过了亚瑟·丹托谈论的画框的时候,几乎不可能用简化的挪用和所谓的寻常物之嬗变的话术来指征它。不如我们将其看成是一场精致的复古——将人们重新拉回了重塑意义的年代,只不过在此时,现成品的价值构建变成了一台计算机或投影仪的价值构建。如今,人们已经很难再有底气用二元对立的口吻来打压描述对象了,一台投影机也绝不会毫无潜能,人们或许可以将谈论媒介的问题意识后置,就像当我们借摄影机谈影像运动性的时候,将摄影机制造的运动性过渡到投影仪中来;当我们借材料谈论雕塑本体性的时候,将强调射灯对其本体性的塑造纳入进本体意义中。
话说回来,辅助设备仍然不被观看者重视,正是因为它们的潜能被排除了!可被排除开来的某种加持,往往是只有特定辅助设备在某种程度上所能够提供的一种此时此刻与此地且非他不可的灵光;往往是它产生了让艺术作品必须借由它才能发散的某种艺术性特质,只不过人们时常低估罢了。这意味着,如果人们期待着辅助设备能够重新赢得观看者的目光并报以尊重,那么,人们就必须在辅助设备身上重新开发出上述那种非他不可的灵光。
最极端的情景或许就是,那些辅助性工作本身嫁接了一个当代艺术的逻辑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为创造工作的一环时,同样是一些辅助设备与辅助工作,是否便赢得了一张重新考虑其价值的通行证?——一位有着艺术家理想的布展工人,在其布展过程中提供了巧妙的、甚至卓越的展示策略;一台不甘心只做播放设备的投影机,用它执拗的个性颠覆影像的画面时,媒介的问题往往需要在这样的瞬间被重新考虑。
此刻开始
就如同人们端详暗箱,探究观察主体的技术一样;就如同人们拆开钟表,探究时间究竟是什么一样,这并不能称之为是一种无聊掺杂着荒诞的行为,而是重塑认知、发现隐秘的知识的过程。如果有一个可以对当代艺术现场中的辅助展示设备做出透彻观察的时刻,我希望这是一次不可遏制的偏离、激荡与挑衅,致给那些展览现场中的边角料们。
图片资料来源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