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同济理论电车 文:陆兴华

摘 要:电影研究也许更应该研究观众如何将电影变成他们自己的个人技术,找到自己的时间图像、时间和自由,自我解放和走向跨个人化。德勒兹、朗西埃和斯蒂格勒的电影哲学为我们思考如何向观众赋权提供了思路:电影应该帮观众通过运动图像来找到自己的时间图像,将导演的电影变成他们自己的电影。
关键词:时间图像 时间 自我解放 跨个人化
目前的电影理论研究主流大都聚焦在对电影叙述及其形式的分析,不自觉地只将电影当成了文学文本或艺术作品来研究,就遗失了观众在看电影时对于电影这种技术-媒体的主动借用这一部分:错过了德勒兹说的观众通过看电影而找到一个时间-图像,走进自己的时间,或忽视了朗西埃指出的观众会通过电影而分享更多、更大的命运从而自我解放,或未认识到斯蒂格勒说的观众在看电影时重拍自己的电影给自己看时所实现的跨个人化。

陆兴华与朗西埃,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 摄
本文想要从下面六个角度来开掘出一个研究电影的新路径:抛开故事、叙述方式、电影史关联、视觉分析、性别政治和社会运动等等关怀,将导演的看与观众的看拉平,将观众自己的拍、剪、放和导演的拍、剪、放平等看待,当成是互相竞赛的“看”。全文要通过下面的讨论来认真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看电影”?
一,什么是看电影?
本文认为,电影是那些本身并不存在的图像的虚假运动,是供观众继续自拍、自映的那一串图像。它很可能会像广告、韩剧或新闻图片和绘画那样玩弄、毒害观众。如果不主动去“看”它,它就是一串意识形态或广告,是一只捕鼠器那样的东西。认真看电影时,观众是要在导演指挥的电影,也就是一大堆运动-图像中,去打捞出一张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图像。那么,观众如何在普遍、时时和到处,包括在电影中的那些图像的陈词滥调的包围中,淘洗出一张自己的新时间图像?这工作必须由观众自己来完成,导演急了也没有用,但可以示范。商业或艺术电影本身只是像工业酱油那样的东西,只是供给观众做白日梦用的佐料,由他们自己去配出美味,助他们去找到自己的那一张时间图像。导演必须努力通过自己的电影去帮助每一个观众找到自己的时间图像,深入虎穴,但又能从普遍的图像陈套包围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像启发术那样困难的工作,与催眠或蛊惑的工作相反。电影必须解放观众,朗西埃说,好的电影和好的导演是要帮助观众离开观看的位置,进入导演的位置,主动在导演的电影里拍剪放他们自己的电影。一个放着一部好电影的电影院里是同时放着几百部电影的,观众都是在面前的电影里拍剪放着自己的电影给自己看。
画家培根(Francis Bacon)发现,在绘画前,画布上总已有太多的东西蜂拥和纷纭其上。作画,是要驱赶这些已经一窝蜂地纷纭在看上去空白的画布上面的东西,像培根那样,先画几笔,再从画里找到一个泉眼,在一张画中打开另一张画,让那另一个世界像泉水那样地涌出来。观众也是要在电影的千万个图像中里找到那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图像。等到那个时间图像涌出来之后,整部电影就都是围绕这一观众自己的时间-图像来展开,这时,电影也就是观众自己的作品了。为什么只要找出一个时间图像就够?德勒兹认为,因为如果观众认定的是这一个图像的话,那么,其它所有图像就都是为这一个时间图像服务的。这就是电影的部分和总体之间的辩证。[1]而处理整体和部分方面的高手,是爱森斯坦(Eisenstein),《战舰波将金号》(Bronenosets Potemkin)想要用48小时述说人类过去和未来各2500多年。

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
电影是运动图像,必须通过图像运动,去造成观众自己的时间图像,最后在观众眼里和手里生产出图像时间:电影于是成为个人自己的绵延,那一爱森斯坦在电影中所要营造的世界历史(黑格尔说的个人走向世界精神)。看自己给自己放映的电影,到最后,观众得到了自己的时间,于是也就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摆脱了来自大众媒体和电影本身的图像纠缠和毒害,摆脱了意识形态通过广告和电视剧和电影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编程,开始了自己的真正的日常生活。而我们天天身处这种有组织的图像堆积而造成的苦难和毒害之中(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语)。看电影因此也是:在电影中找出能摆脱这部电影的这部分会毒害观众的图像的另一部分电影,用电影里的这部分与电影中的那一部分斗争,这就是斯蒂格勒电影思想的核心:电影是个人的药式体外化过程中所需的“梦的器官术”,像吸毒那样,让我们把梦做得更猛烈一些,将毒变成药,使我们在心理和集体这两个层面上“跨个人化”。[2]
看电影是观众要在电影中得到一张时间图像?得到他们自己的时间和自由?那么,什么是时间?康德将时间定义为我们的先天直觉之一。他认为,时间并不单独存在,总是我们自己给出了时间,是我们自己给了自己时间。在电影中,观众通过找到时间图像,而自己向自己给出了时间;他们由此而有那么一会儿是生活在自己的时间(绵延)里了。
这种电影经验是先验的,也就是说这是人站在神的位置上的经验:是我像神那样给出了时间,是我给了自己时间,一切于是都是我要它是的样子了:费里尼镜头里的罗马街头一开始是被好莱坞败坏的,人人都在模仿电影里的走路样子。但导演之后重新让罗马街头成为他和观众的平滑面,用电影战胜了电影:他们人人又能像真正的好莱坞明星那样地潇洒于罗马街头了,不论他们身境如何。
德里达在《给时间》(Donner le temps)中讨论了两种“给时间”,在这里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无条件赠予对方礼物,是给对方时间的余地;[3]抽烟吸毒,如波德莱尔说,是给自己时间的余地,仿佛自己由此而手里多出了一些时间,感到放松了。看完电影,我们感情到的放松不正是这种吗? 我们为什么还要像收租婆那样地去纠缠那个编剧和导演讲的故事合理不合理,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安慰,符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达到我们需要的政治正确?而这就是长镜头存在的意义:像要打井找水,被时间的流动夹裹的观众,在导演的帮助下,垂直地钻探了时间,像在阿巴斯的《樱桃之味》结尾一样,第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慷慨:导演将整个块时间留给了观众,让他们得到了成为神的感觉。好电影里,仿佛是导演将时间挽成花束,献给了观众那样,看完电影后的观众对导演的这种好客都会充满感激:他们获赠了大把时间。
相反,看电影时,我们总想回到一个让我们自己感到舒服的故事之中,而那是主动自我囚禁,是好不容易从俄狄浦斯三角逃出,马上又在第一时间里跳进俄狄浦斯三角,为了找到另一个爸爸,一个新爸爸,一个更好的爸爸,是还没疼,就预先给自己吃上了止痛药。电影里的故事总是:一开始主人公要挣脱旧爸爸,可是,到结尾时,他们又慌了,觉得不在一个新爸爸麾下,会麻烦的,总在故事结束前的第一时间里又去抱住了一个新爸爸,因为不这样,他们或者说我们观众自己就会受不了,而这样做了,等于是前面的故事全都白讲了。可以说,好莱坞内外,很少有一个男女关系的电影故事能逃脱这一我们从旧爸爸扑到新爸爸怀里的过程的。所以,如齐泽克说,所有故事片的最后十二分钟都必须被剪掉,因为那一定是帮我们扑向一个新的大爸爸的陷阱。好导演和好电影必须帮观众在看电影时与这种故事瘾、情节症作斗争。这方面的优秀榜样,德勒兹认为是菲茨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但好莱坞无法改编好它。BBC拍的劳伦斯的三集剧《恋爱中的女人》跳出了这一陷阱。里面也有故事,但全不照观众的要求走。这电影里的时间螺旋是一条宇宙线,导演用它帮观众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甩在脑后。而电影就是用来帮助我们与那一统治我们的俄狄浦斯三角作斗争的。

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说,在“自然”中,仿佛人就站在上帝的位置上了:自然是我的花园,每株花草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你看,它们多顺眼啊,必须的!看电影时也是这样的:看了那么多过渡性的图像运动后,我终于找到线索,可以这样说了:是我要电影成为这个样子的,导演只是来帮我的助手。我是照了“这一个”我自己选定的时间图像,来将导演的电影重新剪成我自己的电影的。电影中,导演搭建的梦境是供观众的梦境来篡夺的。
这就是观众的先验想象对于电影的主动摆布。康德说,先验图式从头就在我们的脑中,像图纸那样,被我们落实到眼前现实之中。我们看到了现实,就要去追认:人通过先验想象而将自己脑中、梦中的图式强加到了现实之中,然后说,是我要它这样的:这就是设计和发明。阿多诺对好莱坞的批判,就基于对这一康德主义之先验理性的批判:工业电影短路了观众对自己身上的先验想象的运用,走到电影这种群众性艺术的积极的政治功能的反面去了。今天的艺术电影和把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关心社会现实的纪录片,在这一点上说,多半也与商业片一样地反动:都是导演的个人炫情,忘了将电影交接给观众。
那为什么观众必须到电影中去走进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时间?柏格森说,人会自己营造精神现实,与物理时间无关,前者就是绵延,就是我们人走向宇宙的过程,因为人并不生活在物理时间之中。爱因斯坦于是就说他是书呆子。这话很鲁莽,使很多科学家都反感爱因斯坦,认为后者搞坏了科学和哲学之间一直良好的互助关系,最后就不让他的相对论得诺贝尔奖。德勒兹站在柏格森一边:蒙太奇里,螺旋线是宇宙时间,比如导演拍的天空上飞行的鸟群的阵列的滑行,就是电影中的宇宙线,是要帮观众用自己的天线接到自己的宇宙时间,不需要爱因斯坦们的帮助,电影就能将我们带入人的这一精神现实:时间。[4]物理学家们理解的时间比水晶棺还可怕,或者说,后者非常需要我们用电影和梦去填补。
如何用天线去接收到自己的宇宙时间?德勒兹说,观众是这样做的:在电影中创造概念,又在概念之间建立内在平面或平滑面,最后就在上面滑行,走进自己的时间,与这个星球重新叠加一次,走向宇宙,使宇宙成为“我”的宇宙。而这就是看电影:用图像运动使自己加速,将自己再一次叠加到这个星球之上。
[1] Gilles Deleuze,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trans. by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p. 32-40.
[2] Bernard Stiegler, Qu’appelle-t-on panser? 1.L’immense regression, Paris: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18, pp.203, 248ff.
[3] Jacques Derrida, Donner le temps, I, Paris: Galilée, 1991, p.60ff.
[4] Gilles Deleuze,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op.cit., pp. 7-11.
二、看电影是观众在电影里搞自己的哲学
首先,德勒兹认为,哲学也是电影,把电影当电影来看,就是一次哲学行动。观众是在研究、发明自己的时间图像,努力生产出图像时间。其次,导演在拍电影时引起、遭遇了一些哲学问题。越在其作品中与这一哲学问题搏斗得惊险,电影的水平就越高。哲学家是前来帮导演和观众在电影中处理由导演和观众的电影工作引起的那些哲学问题的。而电影中的哲学问题仍是电影问题。第三,每一部电影都围绕一个大观念展开。导演用尽全力与它搏斗,最后精疲力竭了,如贝克特那样,留下了一个哲学工作的现场让观众来继承其遗志:电影是这一搏斗后留下的现场,像一次哲学实践后留下的残局。[1]而对于观众也一样:电影中这一观念太大,他们有点承受不住了,像汽车超重了,需要停下来,解决掉过重的哲学负担,才能继续前行。观众是在重新发动导演留下的电影中的那一观念,通过发明他们自己的概念,而在电影中创造和发明出只属于这一次观看的那些概念,并以它们为坐标,来建立自己的平滑面,重新吸收这部电影。对于德勒兹,这样地重建平滑面,才是看电影,否则就是被动地在座位上等待一个狗屁的爱情或情义故事来捕捉他们。
观众在看电影时自己亲自遭遇了哲学问题,因为电影在强迫观众在电影之中开始自己的概念创造的工作;电影会以它自己的方式迫使观众去搞出一个针对这部电影的内部哲学工程。所以,他们需要哲学教师的帮助,就像如宜家这样的DIY店也需要指导员来帮顾客去开始DIY一样。

德勒兹《电影2:时间-影像》,谢强等 译
在电影中搞导演和观众自己的哲学,在电影中做哲学,按照德勒兹的说法是:在电影中,观众自己在一个概念上复界(re-territorialize)。那什么叫复界?复界前,先须去界(de-territorialize),也就是观众先通过运动图像来加速,摆脱掉被那打扮成图像的广告和意识形态所编程的日常生活,重新降临,认领一片新领土。这种复界才使人“成为”。狮子总忘了前一天的领土,一大早就会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撒一泡尿,来宣布它的新领土,去复界,人也应该这样。范冰冰的复出就将是复界。观众在电影中通过创造自己的概念,来布排出一个平滑面,来复界。看电影时,他们有了机会来这样做。
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去发明一个概念,然后将我们自己复界到这一概念上,像要彻底搬家那样,这就是在电影中做哲学。观众在文学和电影中搞哲学:像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黑泽明的《七武士》中那样,复界到电影所引起、或由观众自己为了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时间图像而创造出的某一个或某一些概念之上。守卫一个村庄?大兵压境后怎么办?以什么范围和尺度来看这问题?黑帮内?封建社会内?全球化中?面对着宇宙地?我们,也就是导演和观众,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这一情境中,还是另外更大的上下文?过去的25个西方一神教眼中的世界历史式世纪里,有哪些人曾有与我们此刻一样的遭遇?这就是黑泽明的电影逼观众走进的思考位置。张艺谋学到他这种史诗和神话般的讲述方式了吗?观众也像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面对这样的重大的难题那样地来面对人物所遇到的没有先例的困境。观众变得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黑泽明那样地深沉起来,开始创造概念,再将自己的此时的存在境况复界到这些新概念上,来建立自己的新的平滑面:也就是这样地将导演的电影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电影。
《地球的最后夜晚》里,那些位于失败男子黄觉和风尘女子汤唯之间的由观众自己在观看过程中发明的“概念”,使他们着迷了。这电影的哪一困境、哪一细节、哪一概念是历史上第一次,或在他们所了解的所有男女关系中,在他们看来是第一次冒出?银幕上不断冒出这样一些感性(affects),向他们扑面而来,他们被拖进某一种情愫(ethos)之中。这些都是供观众使用的感性图像,他们可以用自己临时发明的那些概念当坐标,去连成一个平滑面,用这一平滑面来收服它们以及整个的混沌,来解释过去的那有了人类式讲述的25个世纪,并将他们自己复界到它上面。
电影看到一半,观众一定在思忖了:这一对男女之间的到底哪一个“分子”是可被他们重新创造成为概念,来当作滑板,助他们思考的?看电影时,他们用了里面冒出的种种感性,来创造出自己的概念,这之后,他们就照着这一概念来回收整部电影,后者都是他们自己要处理的材料,都被他们搬到对这一他们自己创造的概念的进一步的创造之上。这时,电影本身就成了他们自己的平滑面,像是他们自己的溜冰场了。评论电影时因此也是他们在自己的那一电影平滑面上溜冰给我们看,与导演的拍关系不大。
总之,德勒兹号召我们在电影中搞我们观众自己的哲学,反对我们用哲学教义去分析电影。导演和观众只要处理电影中、看电影时自己引发的哲学问题就够了,不用去关心哲学家们说的哲学。哲学家是来帮他们处理在电影中由他们自己引起的哲学问题的;而导演的哲学问题也并不是观众的哲学问题。观众是不得不在电影中搞哲学:在电影中发明出自己的概念,围着一个大观念来处理他们将要拍剪放的自己的电影,因为他们一坐下来观看,那部电影就是他们自己的电影了,导演只是为他们服务的。

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年-1996年)
杜拉斯的《阿加莎与无边界阅读》(Agatha et les lectures illimitées)的结尾,观众跟着一个镜头,从一个黑暗的房间走向面朝沙滩的窗口,终于在那个有反光的沙滩上,找到了自己的时间图像。这就是那部电影故事的结尾。观众甚至不用去看电影,也可以自己这样来拍,用小说,用电影,像写诗。
这时,杜拉斯到底是要讲什么故事,已不重要,观众自己找到了入口。在文学作品、电影、新闻图片、广告之中,我们都可以用杜拉斯这一方式,来找到自己的时间图像。我们都可以自己去做杜拉斯,不论是不是在电影院或摄影棚。电影导演对我们而言不是必需的。
杜拉斯的这部电影的故事是一次也许发生也许没有发生的兄妹乱伦,也可以说是导演与观众之间的一次乱伦。用镜头将观众拖到窗外的刺眼的沙滩上时,导演已将自己的位置让位给观众,要他们自己接管过去,来处理这一很幽深的问题。电影不是要用这一故事里的哪一点去吸引观众,而是要帮每一个观众从中创造出一个自己的观念,并用这一观念来通盘理解整部电影,找到自己的时间图像,得到属于自己的时间,从图像的包围中重获自由,包括照观众自己的意愿去拍剪放这部导演手里的电影的自由。
德勒兹在电影课里高度评价了杜拉斯根据她自己的小说拍的这部《阿加莎和无限阅读》,认为它道出了电影的真谛。[2]电影的目标就是要将观众带到这样的窗外,到“那一条”反光的沙滩上(是哪一条沙滩又有什么关系!),找到他们自己的时间,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任何人都可以走向这样一条反光的沙滩,来拍出自己的电影,也只能这样去拍:走向个人存在的新的总体,使后者更开放。这方面做的好的,还有威尔斯的《公民凯恩》,被德勒兹认为是表达电影总体性的巅峰之作:电影使个人的存在之总体不断被螺旋式打开和丰富:带观众走向宇宙,成为弥撒亚,重新降临。[3]
电影是一架不断将我们搅拌到一个更大的总体之中(爱森斯坦的《十月》是比列宁的那个革命更大的总体)的机器。总体是向绵延开放的。成为观众的时间图像后,电影就成了绵延本身;人的现实也必须是这一将一切都卷进去的总体之绵延。电影通过蒙太奇而将我们不断带到更大的总体之中,也就是在帮我们形成自己的绵延,而走向宇宙。
[1] Gilles Deleuze, Cinema 2: The
Time-Image, trans. by Hugh Tomlinson and Robert Galet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 147ff.
[2] Gilles Deleuze, 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 op. cit., p. 122.
[3] Ibid., p. 26.
三、邀观众在导演的电影中拍自己的电影:里维特电影中的观众主动权
德勒兹说,里维特(Jacques Rivette)是最法国的电影导演。他只拍巴黎,特别善于拍夕阳下的城市幻影,将它变成观众自己的梦境。他认为,只有观众自己的梦才能给巴黎带去现实和关联。[1]是人的活动才能使城景活起来,观众的演救活了城市这一舞台。
每一部电影中,里维特一开始总是要找到人物正确的身体姿势,找到人物与场地之间的最好的相处关系,但总是找不到,也不是为了真找,而是为让观众像一个老练的导演那样来接管过去,来掌控现场。

导演里维特(Jacques Rivette,1928年~ 2016年)
他在电影中排练的姿势和动作,既不是电影本身需要,也不是出于剧场或剧情的要求。他使演员既不在舞台上,也不成为电影中的浮标。他仿佛是在电影里给演员试镜,帮助观众自己去挑演员,最后由观众来决定谁可以来当观众自己的那一部电影中的主角。所以,他习惯使用的双女主角的结构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总是要观众自己来定夺这两位女主角里谁来当主演更合适,电影的故事于是总是还未真正开始。里维特的电影前,总是坐着的几百个业余电影导演;他在给他们上导演课,然后当场放权给他们。
在他的电影中,戏剧排练成为镜像(mirror-image)。电影里有剧场性的种子,总未能完成,因为电影所营造的剧场也不是他要的,而是要让观众来接管的。[2]他帮观众做的,是使戏剧与电影对抗,以便在日常生活和仪式之间重新寻找到新姿势,将那些虚假的姿势押回到身体之中,修正它们,重新激活它们:回收我们的破碎的身体姿势,帮它们重新史诗般地亮相。因此,他永远使演员的姿势处于边缘状态,既不实在,也不想象,既不日常,也不仪式,总是处于幻觉和错觉当中。这等于为观众在电影中发明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剧场中的剧场性。[3]观众在电影中接过了导演赠予的这一剧场性。
[1] Gilles Deleuze, Cinema 2: The Time-Image, op.cit., p. 11.
[2] Ibid., p. 76.
[3] p.194.
四、人民通过看电影来成为当代人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13节中说:人民想在电影里描绘自己;但电影公司启动巨大的公关机器,用明星的事业和爱情,民意测验和选美,来歪曲和败坏群众想用电影来描绘自己的兴趣。而观众本来想用电影来理解自己和他们的阶级的。电影本来应该成为大众的媒体,大众应该通过它而与绘画这种资产阶级媒体告别。
电影与绘画的区别,是魔术师(画家)与外科大夫(电影导演)之间的区别。画家与现实保持天然距离,电影导演则插入现实纤维之中。电影对于现实的呈现因此是无可比拟地对今天的人们更有意义的。它给了今人的现实中的那些能够摆脱装备支撑的方面(不需要搭景,观众也能通过电影来拍自己的电影;戈达尔的“人人的电影书房”或我们今天互联网上的电影“资源”,就指这种)。电影比绘画进步在:它直接和亲密地整合了快乐(看和经历之快乐)和专家式评价(观众在电影面前都是准专家,正如他们在观看体育运动节目时一样)这两者。
就其本性而言,绘画无法为集体的共是观看(接受)提供对象,而建筑却一直都可以,史诗有段时间里也可以,而替代了建筑成为今天的部体艺术的电影,在今天完全能做到这个。电影用几十分之一秒当**,轰开了这个监狱-世界,于是,我们可以在它的四处飞溅的残骸之中,去平静地开始我们的梦,我们的冒险之航。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年 —1940年)
一用近镜特写,空间就扩张。一用慢镜头,运动就延伸。电影将物质的全新结构展现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走路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但对迈步的几十分之一秒里发生了什么,则是一无所知。达达主义是想用绘画(文学)去制造出今天的公众从电影中寻求的效果(第17节)。走神地观看,在所有艺术区域已越来越成为常规,常被看作病症,但在电影观看中,却适得其所。电影在训练我们去三心二意地观看(第20节)。
大众是铸模、母基,经过它的翻模,所有惯常的面对艺术作品的行为,在今天,都被翻新(第18节)。面对艺术品,观众的深思式沉浸,走到了它的对立面:三心二意的徘徊(Ablenkung)是我们今天面对艺术作品时的最习惯的态度(第17节)。我们面对艺术品的方式,从此将不是传承下来,不是精英们教导而来,而是从新形成的群众对于媒体的集体感受和使用方式比如电影那儿习得:精英也不得不在大众的这种三心二意的看中去学习如何观看。[1]那么演员在向谁表演?他们是向在场的技术人员。后者的背后是群众。在电影时代,群众就是镜子。张国荣们是将粉丝当镜子,来化妆和表演的(第12节)。
蒙太奇与电影制作人员无关,而与观众有关。观众是电影的原作者,负责和身负对蒙太奇中的电影的拍剪放。观众还想要看到他们自己与集体一起在镜头之中;不是想看影像,而是想要将自己拍在其中,同时成为导演、演员和观众。所以,电影共产主义或电影作为共产主义机器(维尔托夫(Dzig***ertov)语)的意思是:电影能使大众过共产主义生活;过共产主义生活的意思是:被与其余的人拍在同一个镜头内;下午在田间劳动,晚上看纪录片里所有人一起在劳动,意气风发地。观众成为导演是为了这个。这是戈达尔对于维尔托夫电影精神的阐释,也是电影新浪潮的核心精神。
[1]观众三心二意是因为,他们在艺术作品前想运用触觉,场景和聚焦就必须时时在变,以便得到被击打的效果(像在打击乐中那样)。在建筑方面是一向如此。人们使用建筑,并感知建筑,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在触觉和光学上去接受建筑。这种接受是与游客在著名建筑前的专注很不同的。
触觉是通过习惯,而不是通过专注,去接受。随便的留意,而不是专注的观察,是我们光学式接受建筑的方式。在历史转折点上,人的感知装置是不能光通过光学式也就是沉思,而是通过触觉,通过习惯,来被慢慢掌握。最三心二意的人也能形成习惯。电影应该成为三心二意式感知/接受的训练(第18节)。
五、观众通过看电影来自我解放
帮观众解放自己,这不是真要让观众冲到舞台上,去当演员,也不只是要使观众成为作者,而是要鼓励观众当场用摆在她面前的电影,来讲她自己的故事,自导、自演、自看。用别人的电影,来拍出自己的电影事来自听、自看。这就是通过电影来讲寓言的意思,从来,人们都是在用日常语言来这样做的。电影作为一种本体论艺术,是在向观众提供本体:利用电影里的故事,来讲自己的故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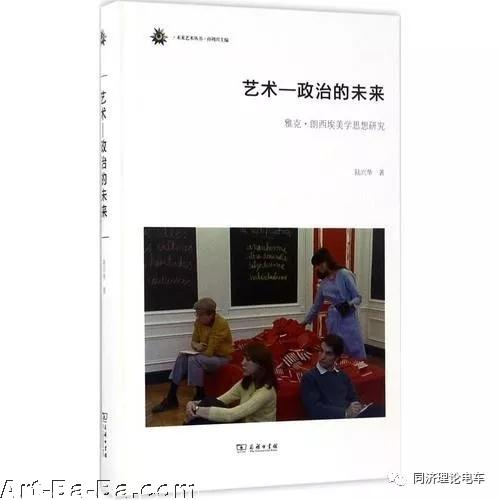
陆兴华《艺术—政治的未来——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
观众不是要去作品中找那个作者刻意设计、巧妙地告诉她的东西。面对自我解放的观众,作者应该成为无知的老师(le Maître ignorant):她不是要将她知道的东西强加给作为观众、读者的学生,而是鼓励学生,进入她们面前的符号丛林,去勇敢冒险,从已知的,渐渐过渡到未知的,就像她们小时学母语那样。
成为观众,是我们日常做的事儿,并不会因此使我们成为俘虏,但在文化工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编程下,我们的看却常常成了自投罗网。在生活中,我们总是同时既教也学,是同时作为观众来行动和认知的,将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过去已看过和做过的事儿连接在一起,既教又学地来这样做,也就忘了自己是天天在这样做的。
我们人人都有同样的能力来发明,来翻译;不懂,看上去不可能,我们就通过翻译,就去发明。一旦以这种平等的态度来参与艺术实践,观众就可以自己来居有作品,用与原作者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其作品。柏拉图认为,合唱队就能唱出共同体的本质,哪里用得着剧场;在我们时代,情况已坏到迎合观众的电视剧拉住了80%以上有投票权的观众,表现我们日常生活或政治共同体本质的严肃戏剧,则需要国家的补贴来维生,且其能否真的表现那种本质,亦因此而极受怀疑。
戏剧必须成为一种导演和演员的自我抹煞的中介,来激活共同体的艺术。现代戏剧中,布莱希特和阿尔托给我们开了两个好头。布莱希特是要将观众与舞台之间的距离抹掉,从观众中抽出本质,再将其甩回到观众自己头上。而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则是要将舞台上发生的边缘化,让它只成为触动和激发观众的参与激情的工具。观众看戏的目的,只是要在剧场里感受到集体行动的动能,像是汽车在加油站里加油一样。[2]
在朗西埃看来,电影短路了我们的全部叙事装置。它挫灭了笔写的故事。[3]在我们去观看的那一刻,电影才是真的,而先前的历史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像戈达尔那样:分拆图像群,将图像的连续切分为一系列的碎片、明信片和课程;将图像重新洗牌,做一种粗暴的图像接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的字可见,使马克思主义的图像可读。艺术与政治在电影中这时就是同一种工作了:使字与图像互相向对方漂移;总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重新表面可见与不可见。[4]
[1] Jacques Rancirère, Et tant pis pour les gens fatigués, Paris :Amsterdam, 2009, p. 389ff.
[2] Jacques Rancière, Le Destin des images, Paris, Le Fabique, 2003, p.37.
[3] Jacques Rancière, La Fable cinématographique, Paris: Seul, 2001, p. 8ff.
[4] Ibid., p. 187ff.
结语:观众通过看电影来实现跨个人化
斯蒂格勒说的跨个人化(transindividuation)是指:个人在心理和集体两个层面上技术地(电影地)将自己嫁接到一个更大的“我们”之上而分枝、延异。电影是梦的器官术,人人都在用自己的梦来制作电影给自己看,而走向一个更大的“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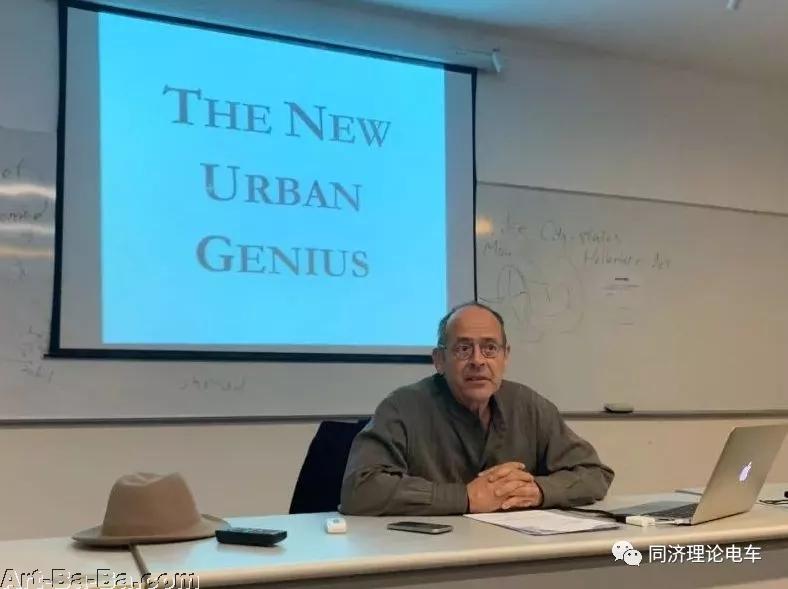
斯蒂格勒在同济大学,2018年摄
斯蒂格勒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想象这一概念出发,来论证个人的先验图式能接纳胡塞尔所说的时间-对象,能将电影这种假肢当作药罐。他认为,德波(Guy Debord)只说出了电影的毒性这一面,没有注意到我们能像费里尼那样将电影当作药罐的一面,对付有毒性的那一面。他认为,个人的意识就已经是一个电影院。个人在自己的器官之间拍剪放着电影。[1]好莱坞电影或一般而言的电影,电影景观,也是个人可用的第三存留,可取其片断,当材料,用到自己个人的拍剪放中。跨个人化需要每一个人自己用技术,梦的技术,也就是今天的电影,去搭建。电影本来就是药罐,我们应该在梦与欲望的戏剧中主动去利用其药性。[2]
本文咬定德勒兹的《电影I,II》中发展出来的下面这个重要结论,来直击当前的电影理论研究的一个盲点:导演要帮助观众通过图像运动来找出自己的时间图像,来进入自己的时间。作者又用这一思路来串起朗西埃和斯蒂格勒的关于个人通过电影来自我解放和实现跨个人化这一电影赋权(empowerment)的思想,想要从这个角度来给电影研究打开一个新面向。(本文原载于《文化研究》2019年第37辑)
[1] 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I-III, Paris: Fayard, 2018, p. 616ff.
[2] Bernard Stiegler, Rechanter le monde, Paris:Champs, 2008, p. 48.
* 感谢同济书店的“法国文艺思想讲座”和“深圳艺穗影展”的邀请,使本文的以上思路有幸得到了热烈的现场观众的锤击,很受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