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umero大都市

“经过一个村庄之后
我们突然失去了语言
经过一座城市之后
我们刻意丢弃了声音”
——声音碎片
最近几年,随着北京郊区的整改和拆迁,刘韡工作室已经搬迁过三次,最近一次他搬到了距离北京20公里外的镇子,那里聚集着一些不断在这座城市里迁徙的艺术家群体。刘韡想把工作室的一部分设为酒吧,他曾经在近郊的工作室里摆满了酒和一些常设玩具,如台球桌,以至于那里常常聚集着一批彼此相识的艺术家,但这次他没那么确定了,他说如果开酒吧的话,那么远的路,可能没什么人会去喝吧。
刘韡的展览我已经写过三次,相对于自己的观展经验而言,后续的文字和作品要显得苍白或者多余,所以每次写刘韡,最终都会变成一种自虐的经历。为了让这次碰面轻松点,让他多说,我们约在了798一家有很多艺术家出入的餐厅酒吧。他刚刚从工作室出来,吃了个晚饭,兴致高昂地说着下午在工作室里终于改好了一件要运去克利夫兰展览的作品,他解释说,几乎每件作品的背后都有无数次的推翻重来,往往作品运出也是在截止时间之后,但工作室已经习惯了他一天好几次推翻方案。我想起以前曾听闻,刘韡在2015年尤伦斯个展时布展的神态,他总是执着地在展厅内踱步,调整、移动、变化……观察自己的作品,设想自己是观众,从完美的展厅里寻找可以修改的蛛丝马迹。我相信,如果展览可以延后开幕的话,他可以不断地对自己的方案提出否定意见,重新抛出新的东西。

采访后,我们的聊天内容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我试着将这些语言文字化,或者做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访谈稿,但这很难,作为一位参与过几乎所有的三双年展和作品备受关注的艺术家,他需要诉诸媒体的言论,似乎已经穷尽。这让我想起作为一名观众我对刘韡作品所产生的诸多理解后形成的画面,即便在采访中他很多时候也并不会直接赞同我提出的观点,但正如他所言,对于作品的文字性叙述,其实更像是另一种创作,不同的人发表各家观点,但对于艺术家自身而言,如果在作品结束后还需要辅以文字,那这件作品显然是未完成的和不成功的。对于“作品替我说话”这一点,刘韡从未改变过,他也一直认为,他所坚持的美学是一种更为精准的真实。由此,我产生了“另一篇”的想法,尽力去把浮现在脑海里的场景都描述出来,希望读者阅读了关于这些场景的描述后,下次再看刘韡的展览,能够感受得更多一点。
城市是刘韡口中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在这里,人们聚集在一起,根据智者被传颂的只言片语,进行基础建设,制定规则道德,培训下一代,置换资源,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的角度来看,城市所构筑起的都不只是一幢幢大厦和一条条马路,更重要的还是一种规则无处不在、资本流动、信息交换、文化互融的场所,快速更迭也带来某一些层面上的断裂,如若将三里屯和距其五公里之外的黑桥进行比较,两户同样生活/栖居在城市中的家庭,可能比位于世界两端的另两户人家有着更多的不同。历史在面向未来的时刻才存在,我们所看到、听到或感知到的,除却已经拥有的知识外,是披着现在外衣的未来。现实让人处于矛盾的吊诡中,“丘也与女,皆梦也”。穿梭于处于断裂地带的城市两端,刘韡从现实中发掘出了强大的养分,当我们路过城市的政治中心,看到繁华市井的灯红酒绿,再往更深的城市边缘行进,如果来得及,你还能够看到即将变成城市后花园的矮房子和由劣质建筑材料搭建出来的“乌托邦”。
刘韡当然是这个庞大综合体里面的一个参与者,他居于这座快速行驶着的城市的断裂地带,成为一个随时回来并随时出走的动态观察者,并随着每一次震动而颠簸。对于任何一位艺术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从他所看到和使用的材料本身(对于刘韡来说,是洋铁皮、帆布、铁、木头)做出定论往往不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却往往忽略了刘韡作品所体现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他对于城市复杂性的模仿,不只是美学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权利的问题,它指向的是一种创造平等的能力。

美学是真实的吗?我们在这里不将美看成为一种审美的愉悦之感,而是一种指向真相的能力。我们经常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所看到的美丽事物或场景:“美得让人无法形容。”在印尼语中,“rasa”(音)一词用于描述一瞬间对事物有了醍醐灌顶似的理解,但是无法用任何言语和行为描述出来,而更倾向于心灵上的瞬间契合,也许也是所谓真相的瞬间。在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所展出的两件作品《微观世界》和《吞噬》中,我们只能看到以往作品的影子,材料被模糊了属性,再也无法与粗粝的城市化进程相关,而是凸显出一种物质所具有的独特秩序和美学。当物的材料属性被弱化的同时,物作为物的真相却凸显出来,《微观世界》所塑造的作品局部间有着强烈的相互依存之感,仿佛抽掉一个局部,这个临时的世界就会坍塌,局部和局部的关系在支撑着整体。汪民安在有关展览“物体系”的一则小文中提到如今年轻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思辨实在论,“即主张物有自己的独特领域,物可以从人的视野中,从与人的关系中解脱出来。物有自己的领域、命运和本体,一种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正在形成。”看刘韡的新作也有此同感,即当物体离现实的类比距离越远的时候,它们可能存在的本体才越会彰显出来。
理解这种美学呈现的秩序,需要再回去看刘韡的两件作品:《周期》中,刘韡将七件类圆体雕塑悬挂于天顶匀速旋转,速度的差异将整个空间形成一个微缩宇宙,从而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内实现不同的时间感;《爱它,咬它》这组作品,则是用狗咬胶的特殊材质营造出一种紧张,和随之而来社会与权力的现实问题。这两则例子正证明了,当作品脱离了艺术家而被当成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们仿佛自己“活”了过来,有自己的语言和逻辑,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追溯《微观世界》和《吞噬》这两件作品所产生的变化,不得不提到《幻影》这个实验的场域,如同作家在写完一部新书后来一则后记,如果这样的比喻恰当,《友情》便是这个后记,是通篇感觉的实证。闪烁模糊的夜景灯和一个书桌上的地球仪遥相呼应间,一种无法分辨哪个才是现实的感觉油然而生,是代表地球的模型,还是在地球上发生和被捕捉到的,人类所制造的光源?“友情”的语言例证来源于阿甘本的《论友爱》一文,“一个人看,就是他感觉到在看,一个人听,就是他感觉到在听,一个人走,就是感觉到在走,因此,对其他所有的活动来说也这样,都须有一个东西来感觉到我们在进行这些现实的活动,这样,如果我们有感觉的话,那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感觉,以及如果,我们思想的话,那是我们思想我们在思想。这跟感觉的存在是一回事:存在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感觉和思考。”(中文试译,王立秋,发表于《泼先生PULSASIR》)在这里,友情并非是一个像是“炎热”或“白色”的特定产物,而是“某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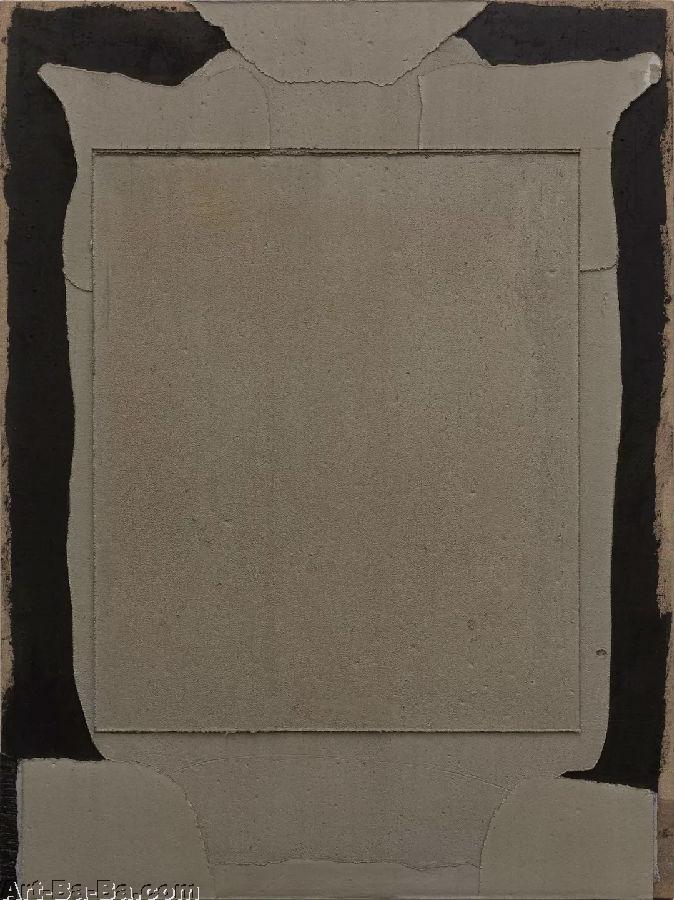
刘韡,《白银》,2017,布面油画,161×121.5cm,
由刘韡工作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