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墙报
导读:注意到周婉京,是她参与的一些艺术策展工作,为艺术家写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了解到她前段时间还做了独立空间的调查,紧接着就发现她出了新书《隐君者女》,各种宣传频繁亮相。带着好奇约见,发现她竟是一位九零后,在读博士生,曾任香港《大公报》收藏版主编。活跃在艺术界,并且是名坚定的左翼写作者,期望做一本真正独立的艺术评论杂志。
和她的年纪几乎不对等的是,她浸淫在艺术行业已达十年之久。甚至她的生活,从未离开过艺术。与她的年纪更不对等的是,她已然是一位学者、策展人、批评家、作家……多重身份之下,却对诸事都有严谨的标准和冷静的判断。
可以把她视为艺术行业的“新生代”,但转身就发现她已经非常“老道”,很多事情做得游刃有余;也可以把她看作艺术圈的“另类青年”,在当下被浮躁和焦虑,以及功利与虚荣层层包裹的艺术行业,还有这么一位理想主义的年轻女孩,她那么清醒,那么醒目地出现了……

2019年5月18日周婉京(左)与胡赳赳在北京UCCA言习所分享会现场
墙报×周婉京
周婉京=Z
墙报=Q
Q: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吗?你的成长背景是怎样的?
Z:我是婉京,名字中有京这个字,是因为我出生在北京。我的母亲也是北京人,她对北京有情意结。我在1990年12月16日出生,我的出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她情意结的出口,所以我的“京”就成了她的情感纹身。
我中学以后去了香港,大学和硕士都在香港读的,其中唯一一段离开香港的日子是在2011年到2013年,为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再修一个双学位,我就去了瑞典。我本科读的是电影,师从导演谭家明先生。谭老师对我格外看重,可我不争气,只会做文章、写东西。我们同班同学黄飞鹏几年前就凭借《十年》拿了金像奖最佳影片,虽然我不喜欢他拍片子的方法,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滥用长镜头的抒情诗人,但我也不得不承认人家比我成功。当时我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有一些老师、同学毕业后去做当代艺术,他们普遍是CIA那个系(现在更名为:批评性跨媒体实验室)出来的,像杨嘉辉、梁学彬、黄荣法、麦影彤和曾家伟。

周婉京系列小说“三城女事”北京UCCA发布会
Q:怎么进入艺术行业的?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哪些人事影响到你?
Z:这可能要看我们要如何定义“艺术”,我一直对纯艺术有愿景,没读电影的时候一直以为它是“映画”、是语言、是神的旨意,学了之后发现其实它是工业、是产业、是无数琐事堆积起来的工程。电影导演,其实就是工头。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决定去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当时推荐我去的是我的老师谭家明和作家马家辉,他们都支持我在所有人都北上拍“合拍片”的时候,做一点不一样的纯度更高的事情,这便带来了我最早开始做视觉文化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契机。
2012年我到瑞典,在瑞典我很幸运地得到在Magasin III做研究助理的短期实习工作,2012年夏天正逢艾未未在瑞典做首个个展,我当时帮助策展人Tessa Praun做一些中文文献的翻译工作。这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当代艺术,在这之前我眼里只有电影。
等到2014年,我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我进入《大公报》副刊文化版工作,2015年初正式接手了收藏版“汲宝斋”,这个版每周三刊出,每次都是A3一个整版来报道古董和当代艺术作品,只有我和我的徒弟卞卡尗两个人负责采写,强度其实挺大的。我2015年到2016年10月(辞职离开报社前)一共做了85篇专访的稿子,几乎涵盖了所有来香港做展览的国内、日韩艺术家的报道。其中,我自己采访的艺术家中对我影响最深(从后续我的发展来看)是李禹焕(Lee Ufan)先生,是他亲自推荐了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西田几多郎给我,让我去读他们的《眼与心》和《善的研究》。李禹焕先生全程是用日语跟我交谈,我的日文很差,好在有个翻译在旁,但是我和李禹焕聊到最后,聊生命哲学聊起了劲,基本用不着翻译了。或者说,翻译已经跟不上我们的速度了。那种感觉特别奇妙。我确实没想到,与他的一次对话就能开启我人生的一扇窗,说话的过程中就觉得有阳光照进了,心里暖洋洋的。后来我想这也许是因为那个阶段,我同时正在写《隐君者女》,写到了瓶颈处和无能为力的地方,所以才会有这种温暖的感觉吧。后来也是因为这篇访谈的影响,我被推荐给《明报月刊》,开始写一些由我发起的有系统的艺术类访谈和评论文章,例如与陈丹青和林璎(Maya Lin)的访谈。

李禹焕送给周婉京的书
01
我很讨厌混圈子
我不想、不愿意、不懂人情事故
Z:我其实很讨厌混圈子,因为我做人的重心都放在了形而上学上。我不想、不愿意、不懂人情世故。所以这让我在2016年底从待了10年的香港回到北京时,特别不适应。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大院小孩,都不能适应北京了,从侧面也可见北京在千禧年后这十多年以来的变化。回来之后就进了北大,做艺术哲学的研究工作,读博士。这个博士读的跟我预想的有点不同,我原先以为象牙塔是另一个乌托邦,后来进了象牙塔之后,觉得这里的江湖和外面的江湖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外面可能是“军阀”,学术圈里面是“学阀”而已。
Q:艺术写作与小说写作,应该是完全不同的语境,你是怎么转换的?
Z:我一直都在对抗,批评这个时代中不公不义的东西。只不过艺术评论是非虚构写作,它的对象看上去很清晰,而小说是虚构写作,它对抗的主体总处在游移且变幻莫测的位置上,不好捕捉。
另外一点造成你有这种“不同”认识的是,小说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讲一个故事,好的小说内核一定是好故事。但是艺术批评不同,好的批评不需要有好的叙事,它甚至不需要回应“好/不好”的问题。因此,我在这两种文体面前不需要转换,我只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去面对就好。我很清楚我自己没什么资格去高谈阔论地聊形式,我做艺术写作的时候就是干净地分析,我做小说的时候就是干净地讲故事。相比怎么讲,我更看重怎么“干净”地讲——不故弄玄虚,不拖泥带水,不胡乱旁征博引。
02
艺术写作用不上的材料、八卦
被我写进小说《隐君者女》
Q:说说新书?《隐君者女》带有艺术圈八卦(大家似乎总是对八卦有热衷)?而《相亲者女》又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Z:长篇小说《隐君者女》的背景确实发生在当代艺术圈,刚刚我也提到了那时我正在香港主持《大公报》收藏版的工作,对于国内的艺术圈八卦的“原始积累”也是从这时开始的。我喜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话,“对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总是伴随着罪恶。”我对艺术圈的观察也是这样,先确定了一个与观察对象(人物及其身上故事)的距离,然后开始储备“罪恶”。可能因为是做过记者的关系,我比较擅长引导对方打开话匣子,聊一些他们从未跟旁人聊过的东西,有些是关于作品的,有些是关于个人经历的,还有一些是关于卖画的诀窍、上位的心得、拍场不流拍的操作办法之类,零零总总有很多内容,有一些能即时用上的就成了收藏版的内容,大部分用不上的内容我替他们保守秘密,后来部分秘密以拼贴、转换的形式变成了《隐君者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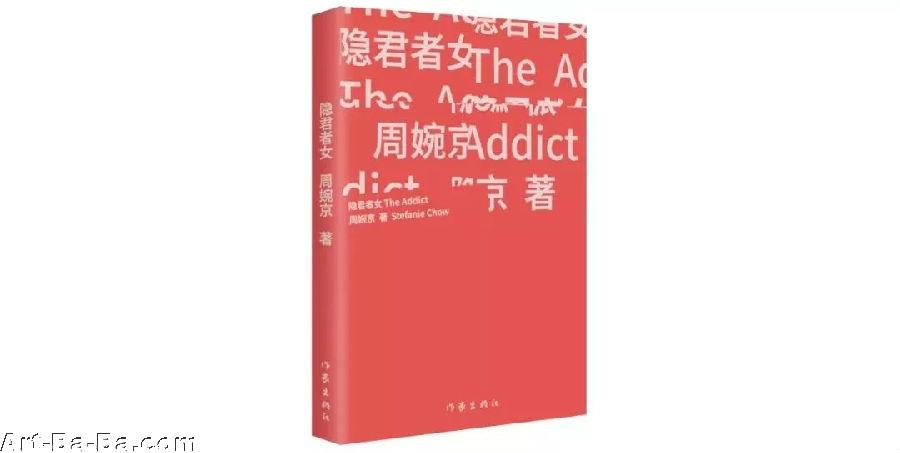
《隐君者女》立体书封面
你在读这本13万字的小说时,艺术记者吴瑾瑜、成名艺术家季周、年轻艺术家吴玳、美协领导陈黔古、海归策展人Naomi、画廊主洪鑫、炒家川子、拍卖行老板等,几乎包含了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在内的艺术圈能够出现的所有典型形象。
《隐君者女》是我2015年上半年开始写的,写了前三章之后才意识到坏了,真难写。难写倒不是因为可能会得罪人,而是另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我运用别人的故事写作时,我发现他们跟我讲述的内容往往真假难辨,我想要借用他们的真实去建构自己的故事,这是非常困难的;其二,我发现资本和金融体系对艺术圈的渗透无处不在,而这个圈子本身又是一个窄小的、纵向发展的小群体,以至于巨大的物质欲望可以在这个窄小的口径中爆裂开来,它也体现在我书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上。
所以,《隐君者女》就这样变成一个“双关语”,它既是书中画作的名称,也是男女主角陷入爱情的状态——一种开始是痴迷、中间是上瘾、结局是**(先卖个关子且不剧透)的状态。为了解决我写作的困境,我尝试加入了许多身体描写,性和欲望的描写让人物的血肉迅速地从艺术圈的大背景中跳了出来,同时带出了更多能够引起共鸣的普遍问题——我们这代80、90后青年在初出茅庐、步入社会时都会经历的隐痛。

《相亲者女》立体书封面
在时间上,其实是先有的《隐君者女》,后有的《相亲者女》。相比之下,《相亲者女》虽然和《隐君者女》同属我的“三城女事”系列,但讲的故事不同,讲故事的方式也不同。《相亲者女》说的是一个大龄剩女嫁人难的故事,这个故事解决的是更多人所面临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圈从业者会遇到的问题。

相亲者女 插图 周婉京手绘
Q:我听说你还做收藏?《隐君者女》中描写艺术品交易这条线索是否有你个人的痕迹?
Z:没错,我自己平时会收一些作品,以影像为主。但我不是一个藏家,虽然我的父辈有收藏习惯,但我收藏的东西都是跟个人趣味有关的小品作品为主,只是我喜欢的,不为投资。我收过的艺术家我基本都认识,例如我也跟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在南法一起蹦过迪,我也有他的一件小作品《Section》。而亚历克斯·普拉格(Alex Prager)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电影圈的宠儿,我身边电影圈的朋友好像都有她的作品。我是误打误撞跟立木画廊买了一张,但这张《Hawkins Street》我很喜欢,不同于Alex的其他作品,它没有着力表现什么,就是铺开一种赤裸的孤单感。我有时候会看着这张摄影会发呆,因为它更像是《隐君者女》里的场景,它对我笔下的人物可能比我还要了解。

Alex Prager2017年摄影作品《Hawkins Street》由周婉京收藏

与Wolfgang Tillmans(左)在南法蹦迪
Q:从媒体人,写作者,再到艺术批评、策展人,入行也快10年,重要的艺术工作可以说一下吗?
Z:刚刚基本都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2012年在瑞典接触到当代艺术这算是“入门”,2014年进入媒体行业、2015年做收藏版的主编,2016年回到北京之后进入北大读艺术哲学,同时正式成为一个独立艺评人……我觉得基本没离开过“艺术”,如果这“艺术”的划分可以容纳电影,是大写的“艺术”而非我们所说的小写的“纯艺术”,那我入行就不止10年。
这些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我针对的艺术家群体,过去在瑞典或香港,能够接触到的中国或亚洲艺术家基本都是比我年长的成功艺术家,或者说只有成功艺术家才能打进香港和海外的市场。这些艺术家的展览完成度高,与他们相处确实能学到东西。然而,我迟迟无法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回应我这一代人的方法。等到2016年之后,我在北京“落叶归根”,我开始交往了一些年轻的国内艺术家,他们很快成为我的朋友。这种友谊不是“仰望”的友谊,而是平等对话、相互激发的友谊。我们处在相同的人生阶段,有着差不多的苦恼和困惑。彼此交流起来,没有“话术”,不谈情怀,就是说方案、聊实施。几乎我所有写过评论的艺术家都是我的“兄弟”,我跟踪观察过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才写文章的。
03
有关独立空间的调查
实践是好的,但没有“好空间”的概念
Z:注意你做了独立空间的调查,可以说说你的调查情况?
周婉京:这个调查前前后后做了将近三个月,因为涉及将近20个空间的资料和10几个人的采访,所以我做得相对没那么快。就在春节的前一天,我还去了798的缓存空间,跟吴小军和傅镭聊了一下他们创立这个空间的原因。

艺术家姚清妹在缓存空间的个人项目《一次彩排》

缓存空间的一次研讨会现场
我之所以做“2018北京独立艺术空间调查”,有两个契机。先说说第一个,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关于现代性与当代艺术案例的研究,这让我对空间与人、空间与作品、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十分敏感。我认为做每一个研究项目时,都需要找到做研究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是具有迫切性的,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这让2018年作为独立艺术空间的一个转折年份浮出了水面,2018年北京有6间新的独立艺术空间诞生(分别是:的|艺术中心、PPPP空间、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空间、车库实验艺术空间、居民楼研修,以及目前已停止运营的纹身店实验艺术空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都在2018?

2019年3月在“的|艺术中心”的独立艺术空间研讨会

2019年3月在“的|艺术中心”的独立艺术空间研讨会
左起:杨帆、周婉京、夏彦国、妮妮、吴小军、富源
2018年,纹身店实验艺术空间刚创立不久就结束了运营,2019年2月,Salts Projects结束了实体空间,同年3月,IFP激发研究所被迫从黑芝麻胡同迁至798艺术区,这些种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以上种种都值得反思。在我的研究分析中,政治与经济、文化政策与资本挤压同时并存,这让独立艺术空间很难真正“独立”,也让他们的面对的对抗对象不只有一个,这是我目前还在继续研究的问题。结果这篇调查最后写了12000字,在我的调查过程中,不断遇到新的没被收入的空间,以至于这篇调查报告不得不分成三个部分发表在《Hi艺术》我的专栏上。我一路写,就一路遇到新的空间,例如胡庆泰的“居民楼研修”和草场地的PPPP空间,这都是朋友推荐给我的,它们都是在2018年成立,却已经做了一些不错的展览。我的提问从最初对“2018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独立艺术空间诞生”转移到“独立艺术空间存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讨论上,我因此也摸索到“非营利”与“独立”之间的区别。
Q:“非营利”与“独立”这两种命名有什么区别?另外,哪些独立空间你认为做得好?好的标准是什么?独立空间的价值体现在当下是怎样的?
Z:“非营利”多数情况下被用以概论这些艺术空间,“非营利”侧重的是“不以牟利为目的”的态度,但它同时也带有一种大型机构的趋向性,这便让它和自发形成的艺术家空间产生了分野。然而我们也要警惕,不该因为某个非营利空间受到资本的青睐而将它推到“独立”的对立面,也不该因为某个非营利空间完全自负盈亏就简而言之是“独立”。然则,非营利空间的讨论边界究竟在何处?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需要不断追问的问题。

箭厂空间 王卫供图
如果趋向于“好”来评论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有可能陷入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集中的知识生产模式。这一点是箭厂空间的何颖宜(Rania)提醒我的。她告诉我,箭厂这10年中所做的实践不是从“好机构”(good institution)的立场出发,她不希望箭厂逐渐变成一个“机构”或是以“机构”作为名衔来固步自封。相反,他们在运营中,依旧将目光聚焦在具体的项目上,结合艺术家各自的特点来创造鲜明的视觉形式。她相信对于“好机构”提问的重点在于不同的回答,而非将自己锁定在“机构”的形象上。
我认为,这些独立空间目前可能遇到的最大困难,倒不是来自2018这一年,而是来自2018之前多年的累积。似乎,如果要在“亚洲→中国→北京”的框架下讨论“独立”,就不得不紧扣现下世界冲突的核心——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的宗教冲突与政治分歧、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立国的抗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想象与争辩、西方“民主”对于共产社会的描述等。如果研究者摆脱不了上世纪冷战政治的遗留问题,那他们口中宣扬的新的“独立”,又会尴尬地回到后冷战的结构性思维上去。
04
策展的工作重心
在治疗自己的过程中治疗艺术家
Q:可以聊聊你密切合作过的艺术家吗?
Z:我从这些艺术家身上学了很多东西,特别感谢他们。
我真正第一次独立策划展览就是去年在北京索卡画廊策划的“毛旭辉:我只是热爱”展览,展出的是毛老师这十年来的作品。我很清楚我作为策展人时的工作重心是什么,我是在治疗(cure)自己的过程中治疗艺术家。如果可以用语言和文字替他们说出藏在作品中的一些隐痛,我觉得我的价值就实现了。


2018年9月“毛旭辉:我只是热爱”个展现场

“毛旭辉:我只是热爱”个展开幕对谈
李怒在宋庄槐谷林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于上周闭幕,这是我最近和冯兮一起策划的李怒个展。作品是一件集体行为和的一件大型装置。这个展览开幕前我和李怒还吵了一架。但这不是我们吵得最凶的一次,最凶的一次是2018年10月底,李怒在上海策划且参加了一个群展,他拟了一个英文名“Silence in Violence”,然后问我中文取什么名字合适。我认真思忖后,给他的回复是“默煞”,但他不同意,他认为叫“赛先生与外先生”合适。我们俩刚开始就“in”怎么能翻译成“与”起了争执,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能拿一个陈腐过时的大帽子去扣一个当下的展览,再者说李怒的这个展览跟新文化运动没有半点关系,我不明白这种无谓的旁征博引究竟有什么意义。后来,Artyoo还报道过我俩的这次争执。我有自己的坚持,我觉得干净是做人和做作品的根本。

李怒槐谷林个展现场,观众在巨型装置上

李怒槐谷林个展现场摆满了民众自己带来的鞋
我还有一个好朋友是蒋竹韵,我跟他虽然没合作过展览,却做过两次对谈。从第一次在博而励的座谈到今年1月份在OCAT上海馆的对谈,我们俩聊的还是T.S.艾略特的《荒原》和他作品中的技术问题,但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彼此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化。这就好像,过去我们是用放大镜来检视问题,现在我俩是在用显微镜来看问题。蒋竹韵说,是我把他带入现代性这个“坑”里的,我认。

2019年初蒋竹韵作品《全景与凝视》在PPPP空间展出
Q: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对于艺术工作,你通常是怎么进行的?
Z:不去学校的时候,我都宅在家里。实际上,为了宅,我甚至把能买的书都买了,这让我没必要再去北大图书馆借书。我的生活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精彩,别人生活是“公司—家”两点一线式的,我的生活是“书—写作”两点一线式的,这个写作包括小说和艺术评论。
如果是一个策展或评论工作,牵涉到写文章,我通常都会跟艺术家先对接、做一个采访,这是我做记者以来的职业习惯。我的提纲与其他人的不同,问题既尖锐又深入,刀锋一半露在外面,另一半藏在里面。
我想要真实的东西,所以我首先会诚恳地提问。之后进入写作阶段,就开始整合数据和资料,做一些繁琐的文献工作。但只要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去看文献,人就丝毫不会觉得困乏。真正进入布展阶段,空间就像是框架,策展人的工作除了帮助艺术家说他们说不清楚的话,还要引导他们在一个空间内尽可能多地展现他们的才华。才华是一个只跟直觉相关的工作。干扰越少,艺术家的完成度就越高。策展人应该是扫雷的人,一直在为艺术家扫清障碍。

“毛旭辉:我只是热爱”展览导览
05
左翼青年的艺术理想
做一本真正独立的艺术评论杂志
Q:关于艺术理想,有什么要说的?
Z:多做少说,别空想。
Q:近期还有什么工作计划?
Z:下半年,我会去布朗大学哲学系访学,我做的是康德三大批判中的美学研究。布朗的保罗•盖耶尔(Paul Guyer)向我发出的邀请,还给了我访问学者(Visiting Research Fellow)的位置,我心里是感激的。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我还会去普林斯顿大学拜访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当中有“犬儒理性艺术”这个章节和他的研究很有关系。
当然,我也想针对创办左翼艺术评论杂志这件事跟福斯特取取经,我很钦佩他创办了《十月》(October),这不仅是一本杂志,还是一个思想阵地。我刚刚提到了“干净”,在我认识的学者里面,哈尔•福斯特绝对算是一个干净的人。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他作为一个年轻学者可以在上世纪90年代,编纂了《反美学:后现代论集》(这本书目前只有台湾立绪出版社翻译的版本,国内暂无翻译版)这种收入鲍德里亚、哈贝马斯、詹明信、萨义德、罗萨琳•克劳斯等人文章的书。哈尔•福斯特确实是既有能力又有野心的左翼学者。谈到哈尔•福斯特我就会兴奋,我还可以一路从他聊到齐泽克以及影响齐泽克至深的拉康,这是一整条线索的,非常精彩。
我希望可以在下面的工作中汇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一个能回应我们这代人(80后90后)所处的困境的杂志,一本真正独立的艺术评论杂志。而不是市面上那些隔靴搔痒、为个人著书立碑的杂志。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近期我和写作者、艺术家郭锦泓会在中间美术馆发起一次研讨会活动。届时,我们会邀请一些年轻、有批判力的写作者共同参与到艺术评论体制与生态的讨论中,严肃批评还是要有人做,我们对这个平台等了太久,既然此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那我们就自己做。

周婉京,青年学者,作家。美国布朗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艺术哲学博士。曾任香港《大公报》收藏版主编。2012年获得香港城市文学奖。2014年参与策划香港艺穗会“漫步漫音艺术节”。2019年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文学评论组最高奖项。目前在台湾《典藏》、香港《Art Plus》杂志和《Hi艺术》开设艺术评论专栏。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欧洲》、《清思集》,中篇小说《相亲者女》和长篇小说《隐君者女》。
文中所有图片由周婉京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