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好奇心日报 曾梦龙

作者简介: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传播学奠基人,比肩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划时代思想家。《理解媒介》是他的代表作,“媒介是人的延伸”、“冷媒介和热媒介”、“媒介即讯息”等观点影响了无数研究者和创业家。麦克卢汉成功预言了互联网的诞生,《连线》杂志在创刊号上尊其为“先知”。其他主要著作有《机器新娘》、《谷登堡星汉》、《媒介定律》等。
译者简介:
何道宽,传播学家与翻译家,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从事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三十余年,尤其致力于译介和传播麦克卢汉的著作,1988年首次将《理解媒介》译入国内。译作超过四十种,销量逾百万册,主要包括《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麦克卢汉书简》、《帝国与传播》、《裸猿》三部曲、《中世纪的秋天》等。
书籍摘录:
理解麦克卢汉(节选)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这本书,如果我们刨除副题,单单只看“理解媒介”这几个字的话,我们会发现书名相当浅显,简直像是写给大众看的。但这个标题其实充满欺骗性,“理解”从来不是容易的。麦克卢汉在书名里真正想表达的是:你们都在使用媒介,有些人还拥有媒介或投资媒介,所有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媒介,但你们都根本不理解媒介,也不明白媒介究竟给我们的人类行为以及人性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副题——人的延伸。我认为,这个非常浅显的书名,显示了麦克卢汉极大的野心,而他也实际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从此以后,只要讨论媒介,就不能不在麦克卢汉的语境下讨论。
麦克卢汉对媒介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定义。如果我们单纯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我们会说一个学英语文学的人杀进了传播学界,把此处搅得翻天覆地。但是,如果你把麦克卢汉的定义放在媒介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这样更大的范畴来看,那你可能就会认可汤姆·沃尔夫的想法——沃尔夫将麦克卢汉说成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无一例外都在学科中扮演带有范式转变性质的颠覆者角色。而颠覆者和颠覆者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巴甫洛夫作为一个颠覆者,他的那套东西就很难真正流行,但是弗洛伊德则不一样,人的潜意识、无意识、梦、各种情结等等,每个人都会在其中找到共情的东西。所以弗洛伊德很容易成为一个流行的文化英雄。达尔文也是如此。而麦克卢汉恰好具有弗洛伊德和达尔文的学科属性,其理论很容易在社会当中造成共鸣,因为每个人受到的媒介影响都太大了。
此外,麦克卢汉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用一种先知式的语言来阐释,有点像希腊德尔斐神庙里的三言两语,比如有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这种特别短促的警句,每个人看到以后都会产生很多复杂的联想,但是每个人又并不真的懂。麦克卢汉非常擅长此道。比如,“热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自我截除不容许自我认识。”“由于不断拥抱各种技术,我们成了技术的伺服机制。”他的这些“金句”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同时又似乎拥有无尽的阐释空间,所以他想不成为大众媒介的宠儿亦不可得。
当然,大众媒介是大众媒介,学界是学界。一直以来学界对麦克卢汉的争议从未断过。最有名的挑战者是美国社会学泰斗罗伯特·默顿。他在一次会上与麦克卢汉狭路相逢。拿着麦克卢汉的论文,他气得脸色发紫:“你的论文的每一处都经不起推敲!”对这种发难,麦克卢汉忍俊不禁地说:“哦,你不喜欢这些想法?那么,我还有些别的……”
不管麦克卢汉是否预测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个回答还是蛮有互联网精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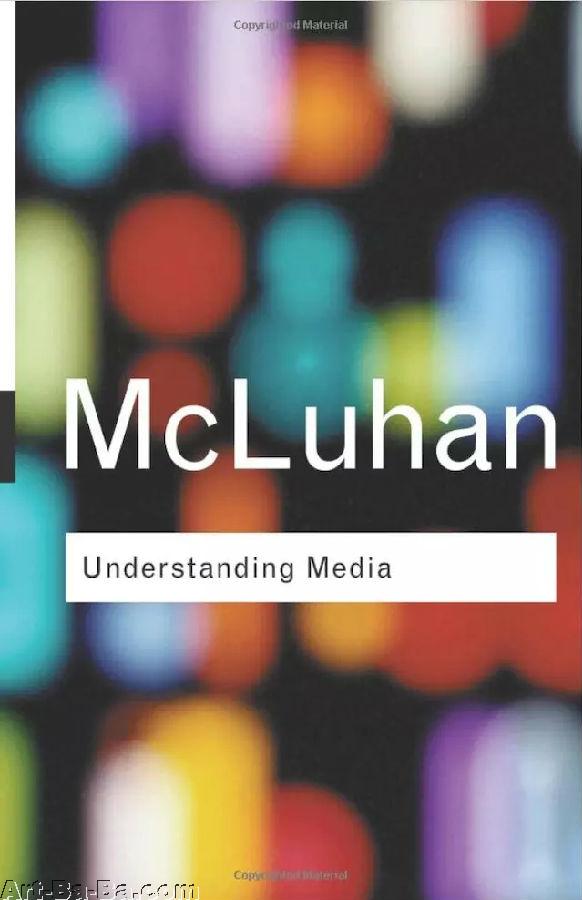
理解媒介,就是理解当代社会
麦克卢汉本人有关媒介效果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首先,他提出,一种媒介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媒介成对工作,一种媒介通过创造内容错觉来掩盖另一种媒介的运作。“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过去对媒介的真正运转机制认识不清,因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熟视无睹”。
媒介由此可以被理解为与其他媒介的关系。正如在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符号的含义总是由其他符号组成。麦克卢汉说:“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所以,“再媒介化”(remediation)可以被理解为有关所有新旧媒介的一般性理论,虽然数字化进程造成的“再媒介化”结果似乎格外明显(Bolter and Grusin,2000)。这不仅意味着新媒介对旧媒介的“再媒介化”,旧媒介同时也可以“再媒介化”新媒介。通过这种方式,各种媒介为自身在文化、经济和美学上的统治地位而争斗。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媒介可以独立运作,并建立自己单独和纯化的文化意义空间。
其次,媒介即环境。在一处,麦克卢汉明确地说,“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一种全新的环境被创造出来了。在另一处,他进一步明确说,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就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速度或模式的变化。注意这个等式:讯息=技术创新引发的变化。麦克卢汉使用“讯息”一词时,总是试图告诉我们,要超越显而易见的范围,寻找新事物所启用、增强、加速或延伸的那些并非显而易见的变化或效果。这里我们用得到那对著名的对照性概念:图形与背景。我们日常所见的媒介都只是图形,仅仅构成其后隐藏的服务环境(a hidden environment of services)的效果。汽车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高速公路、汽车厂、石油公司等。“隐藏的服务环境才是改变人们的事物。环境改变人,而不是技术。”
媒介技术创建了影响使用者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这体现为对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的改变。例如,“电视改变了我们的感官生活和脑力活动的过程”,对各种事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新闻、娱乐、宗教、商业、广告、教育等,不一而足。麦克卢汉还特别指出,人工技术是“反环境”(anti-environment or counter-environment)的东西,给我们提供了感知环境本身的媒介。换言之,没有反环境,所有的环境都是不可见的。也可以说,环境是有意识的,而反环境是无意识的。就像水中的鱼一样,我们无意识地生活在一个技术文化环境中,这个环境是我们通过延伸自身的感官和身体完成的。我们可以把技术(也即反环境)用作训练认知和判断的手段,因为人类迫切需要对技术文化环境的认识。
如果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了进化论视角的媒介种类变迁的话,那么,把媒介视作环境,分析它造成的三大变化(尺度、速度或模式的变化),构成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另一块基石。与反对技术白痴的态度相一致,这种认识表明,技术和媒介从来不是中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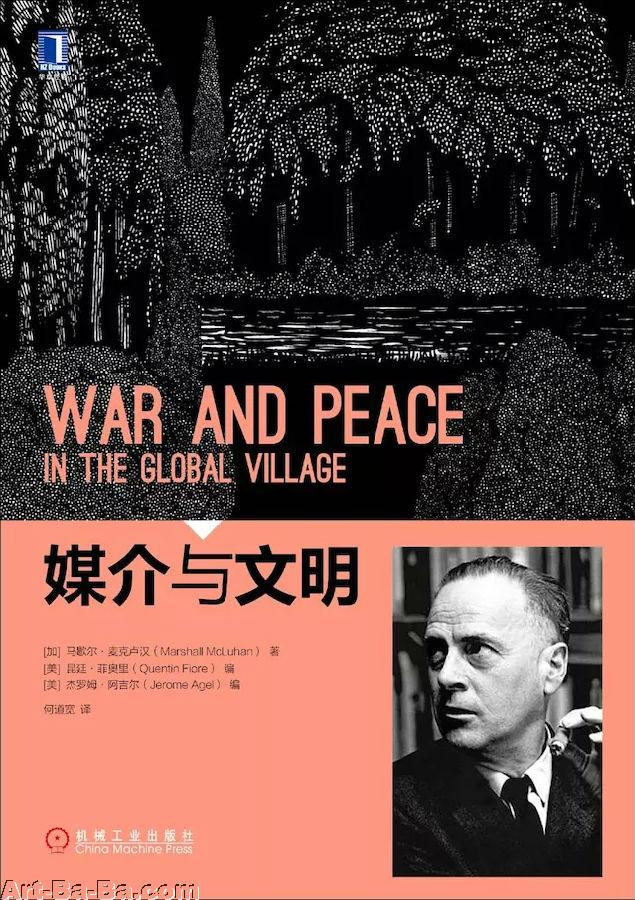
再次,媒介以自己的用户为内容。麦克卢汉在 1971 年致爱德华•霍尔的信中说:“电灯光、铁锤、语言、书籍的使用者才是媒介的内容。这样,界面就完全促成了用户的变形。我认为这一变形是讯息。”在所有的交流当中,无论是何种媒介的用户,都构成该媒介的内容。这符合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察,即认知主体是且将成为他所感知或已知的事物。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引用大卫王在《诗篇》第115篇对偶像的看法——“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即看见偶像会使人顺应偶像,来类比使用技术的人会顺应技术。
而人为何变得会与自己的目睹物一样,英国诗人布莱克在长诗《耶路撒冷》中提供了说明。布莱克认为人被技术所分割,技术是人体器官的自我截除。人内在的东西外延之后,造成对人的催眠,人由此变成了其外延物的傀儡。
这里我们当然就不能不再次提到麦克卢汉有关一切媒介均是人的延伸的著名命题。麦克卢汉坚持技术和生物学的内在关系,坚持“新媒介是自然”,这是因为他把技术看作人类身体或感官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外延。依此定义,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描述极其普遍和广泛,其研究范围从言语和书写,到电话、摄影、电视、货币、游戏、漫画书和汽车,它们都将“无意识的原型形式推入社会意识”。当麦克卢汉提出“环境是过程,而不是容器”时,他的意思是说:所有新技术的作用都在于无声地通过重新设计“感官比例”(ratio of the senses),而将其深刻假设加于人类心理之上。
矛盾的是,延伸也是一种阻碍自我认识的截除手段。延伸的最后阶段(也即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充满了危险:
电力技术到来之后,人延伸出(或者说在体外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到了这一步,这一发展意味着一种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仿佛中枢神经系统再也不能依靠人体器官作为保护性的缓冲装置,去抗衡横暴的机械装置万箭齐发的攻击了。
(第四章“小玩意爱好者:麻木性自恋”)
这是一段相当残酷的描写,接受技术似乎成为人的宿命,我们成为技术的伺服系统。与技术保持和谐的结果是,我们的人性在逐渐消失,直到我们化作调整良好的机器人。从塞缪尔·巴特勒的小说《乌有乡》(Erewhon)那里,麦克卢汉继承了人类是技术世界的性器官的思想。这部小说是最早提出机器作为一种生物会进化出自我意识的作品。虽然人造出了机器,但“机器反过来又对延伸出它对人产生影响,机器因此具有替代性的生殖机能”。“机器世界促进人的意愿和欲望的实现,给人提供物质财富,以此来回报人的呵护。”
如此来看,好像很轻易就可以把麦克卢汉定为技术决定论者,但他其实一直坚持一个双向过程:人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技术。尽管电力媒介时代是无意识和冷漠的时代,但它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到这种无意识的时代。一旦我们对媒介环境产生了意识,发现媒介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损害我们的社会或文化,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效果变得无所不在之前,影响新的创新的发展和演变。
对于麦克卢汉来说,任何社会中的核心中介因素是交流、沟通本身的媒介。通过媒介,麦克卢汉找到了理解当代全球社会的一把钥匙。麦克卢汉论证说,在给定文化中的任何新形式的媒介的引进,都会决定性地改变该文化的成员对其物质世界和既定价值观予以中介化的方式。毋庸置疑,麦克卢汉本人被社会成员的新媒介异化经历所困扰——他既为此着迷,也感到惊慌。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促进新媒介发展,而在于让公众意识到媒介的压倒性影响,以便人们了解自身所处的技术环境及其心理和社会后果。

网络即讯息
在对媒介的理解上,麦克卢汉还有一个关键贡献是,让大家意识到电子媒介促进了人类集体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他自述,《理解媒介》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一切技术都是身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对人体通过延伸而增加的力量和速度所作的反应,又产生新的延伸。新的需要和新的技术回应不断累积,最终导致的并非传统的外爆,而是一场空前的内爆。
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一切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结合起来,以电的速度产生内爆”。“一旦序列让位于同步,人就进入了外形和结构的世界……对专门片段的注意转移到了对整体场的注意。”“今天的电子时代,资料分类让位于模式识别……不是一个分割肢解的世界,而是一个整合模式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整个星球缩小为看重当下的单一社区,人的相互依存意识增强。时间对于一个全球社会不再重要,因为没有什么会停止,也没有人会停止。空间上,人们被卷入村落生活的凝聚形态,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与部落之鼓共鸣的独有压缩空间中”。人类由此发生了从个人主义和碎片化向集体认同的转移,“以部落为基地”。
当麦克卢汉写下“我们把全人类都披作我们的皮肤”(We wear all mankind as our skin)的时候,他应该补充说,我们也装上了全人类的舌头,戴上了全人类的心脏。电子技术使得任何一种代码或语言可以即刻被翻译成另一种代码和语言,对语言学一向着迷的麦克卢汉马上意识到其重大意义。
说到语言,我们很难不想起《圣经》中人类企图兴建通天塔的传说,这一通天塔被叫做“巴别塔”,而“巴别”在希伯来语中有“变乱”之意。据《圣经• 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塔顶通天能传扬己名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说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无法沟通,计划陷入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然而现在,“计算机以技术给人展示了世界大识大同的圣灵降临的希望”。人类得以重返巴别塔倒塌之前。
同时,人类感官和神经系统的延伸创造了统一的体验场域。速度和对信息的适应能力促使该场域像群体大脑一样工作。如果人类意识越来越多地以信息的形式出现,“难道不可以说,当前整个生活转换成信息的精神状态时,全球和人类大家庭都要被转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吗?”麦克卢汉认为,人类终于有机会实现但丁的梦想,即所有人全都由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统一起来。
在感官上,电视时代之后出生长大的人,与之前四百年的印刷世代相比,拥有不同的五种感官的平衡。他们变得更像原始的部落人,互相亲密接触,不论自己是否喜欢。“现在这个世界如同一面不断响起的部落鼓,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从那里得到讯息。”所以,我们可以修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警句,喊出“网络即讯息”(the network is the message)。
麦克卢汉有浓厚的寰宇意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者,因为他的天主教信仰以其公民人文主义传统和对“理性”的内在信念,促使他相信有可能实现普世文化。同时,他认为“‘罪恶’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缺乏‘意识’”,因而,给无知的世人传达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之语法,对他来讲具有某种道德-宗教上的紧迫性,即使这种紧迫性把他置于为同类所不信的先知的位置上。
可以说,麦克卢汉是带着目的论的“人文主义者”,具有一种天主教式的乐观主义。他相信永恒,与之相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世俗概念几乎都不重要。他作为思想家,不是为了庆祝或诋毁世界,而只是为了理解它,认识那些可以解开历史秘密的模式,从而提供上帝设计的线索。他的神秘主义有时导致他希望,电子文明将会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跃进,使人类与上帝更加接近。

但实际上,与大家惯常以为的相反,麦克卢汉并没有坚持多久这样的希望。大约只在1960年代的早期,他曾于电子大同的希望中驻足。后来他很快决定,人性的电子统一只是“基督之体”的一个摹本。他甚至还说,撒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电气工程师。
麦克卢汉再部落化的地球村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和平且和谐的社区,其实,如果仔细阅读麦克卢汉,我们会发现他的幽暗意识。麦克卢汉说,他从来没有认为,统一和宁静是地球村的特性。地球村实际确保了所有议题的最大分歧,因为村庄条件的增加创造了更多的不连续性、分裂性和多样性。人人互联使得很多人感觉不堪重负,失去了个人认同。对此的回应是暴力。战争、酷刑、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行为都是在地球村里对认同的寻求,导致屠宰对方成为最常见的部落游戏。
了解地球村生活的积极潜力和负面影响,已经成为当今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的迫切挑战之一。虽然麦克卢汉一度被吸引到戏剧性的希望当中,但在宇宙意识的视野里,看到古罗马代表时间的神祇双面神(Janus)式的互补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时代既是巅峰的时代(人类可臻至高成就和希望),也是深渊的时代(世界也可能走向暴力和崩溃)。
麦克卢汉终生都在与他所称的“无处不在的无知觉”(impercipience of the ubiquitous)作斗争。他笔下的“梦游症”患者正是被不可见的环境催眠了。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怀疑道:
为什么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自己的制造物对自我意识模式的影响?我已经就这个主题写了好几本书。人类打内心厌恶去理解自己被卷入的过程。这种理解要求对所作所为担负太多的责任。
当麦克卢汉用他神谕一样的口吻来形容人对媒介的臣服时,那真是一派令人恐怖的前景。另一方面,他又声称,卫道士般的抵抗是徒劳的,并且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写道:“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正在倒车的车辆,就它与顺向流动的交通而言,似乎在加速行驶。这似乎是文化保守分子所处的带有讽刺性的地位,潮流集中指向一个方向时,他的抵抗反而确保了更快的变革速度。” 用路易斯•拉潘姆的话说,“对于那些捍卫已失阵地的人,他没有什么同情,也没有什么耐心”,麦克卢汉尽情嘲讽他们说:“多年来我注意到,道学家们典型的伎俩是以愤怒代替感知。”
然而,麦克卢汉最终强调,事实上有一样东西比电子媒介的速度还快:那就是思考。麦克卢汉敦促我们提前思考。他提醒我们:“控制变化不是要和变化同步前进,而是要走在变化的前面。预见赋予人转移和控制力量的能力。”放弃抵抗,但要让我们的思考领先于即将到来的变化,这就是麦克卢汉告诉我们的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拯救我们的人性;或者,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还能够向持久目标前进,并保持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