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小说 陆兴华

杨福东,是的,必经之路,装置、行为表演、影像,2018
[按]
去年冬天我与同学们一起去看上双时,在现场和事后与大家作了讨论,碧纯同学作了录音记录,后我又对记录稿做了修改,形成现在这个稿子。
事后回想起来的总的看法:上双今后不应该再取一个题目,因为取一个题目也是盖不住展览的,而国际双年展现在就是一个超市,干吗要用专名,这不是说它不好。也不用请策展人了,没用,反而是障碍,只要列出24个创作方向,在每个方向上找一些排名前10来展出,就可以,机器人都能干好的。还有,大城市的双年展无非是空降一个国际空间,观众就如上海闹市区吃缅因州的大龙虾,就是要享受这种空降感,要保护观众获得这种刺激性的权利,而上双在这方面我认为表现得极其突出和成功。
去上海双年展看什么?
面对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时,我们到底该做什么?
2018上海双年展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当代艺术都有套路,2018上海双年展中可以看到当代艺术哪些套路?
双年展的在艺术界的重要性相当于体育界的奥运会,或电影界的奥斯卡、戛纳。与这些国际艺术节日不同的是,双年展不设立奖项。威尼斯双年展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有107年的历史,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双年展。其次是德国柏林、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等,上海双年展始创于1996年,在世界范围内大概排名第4到6位。
1、关于本届双年展的主题选择问题。
双年展主题首先一定是宏大且统帅一切的,其次它一定是一个出奇制胜的观点,且这个主题和双年展本身的形象是统一的。柏林双年展之所以好,是因为它的政治性总是很鲜明和及时,比如上届的比特币主题,有一个很刺眼的切入点,或者说主题总被设计得统领双年展内的一切。本届上海双年展主“Proregress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术,用了“Proregress”这个包含既前进又后退的意思的夹心词,意提矛盾地重复。标题中说历史矛盾了,但历史是人的叙述,矛盾与不矛盾,是人身上的来,与这个世界的现实无关。可以说,人们在参观过程中,眼光可能会矛盾,这样的棉花糖一样的主题还说得这么吞吞吐吐,是要被人看轻的。
2、到上海双年展看什么?
双年展像一个超市,像一个嘉年华,有各个门类,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大型的装置作品,它是以服务最低审美底线的人的眼光为基础的,所以双年展这么多作品里一定会有抓住人眼球的东西。双年展中,艺术家关注的幅度一般很宽,和一般的展览不一样,且带着很多的游戏、反思或者自我调侃的意味。
到上海双年展,首先是看视频。这次双年展的视频作品大概占了作品数的60%左右,从时长来算,视频作品长度会到十五小时,但我们观展时间通常只有4-5个小时。这一段时间被高度争夺,你必须时时取舍。这就让你感觉到双年展对你身体的时间作了切割,你被拉扯着去看你不得不看的东西。这可以说是双年展作为一个时间机器,对我们的观看的控制。
在双年展看视频作品的时候,你的身体整个陷在了里面,和在家里、网络上、录像厅看视频太不一样了。双年展的视频作品将某种普遍空间、国际空间、乌托邦空间搬到了上海,使我们得到了一种关于普遍性的经验。这一届上海双年展装饰可能故意简陋,一楼视频放的隔离简陋到和中国80年代县城里面看港台录像片的录像厅差不多,声音还相互干扰,让你有在洞穴里观影感觉,这能加分吗?
到上海双年展,其次是看视频作品。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双年展,要去看里面的视频作品?这是因为,平时,周围飘忽的图像通过网络或媒体包围了我们,我们不会真正沉下心去仔细端详过它们。双年展作品的意图,是要迫使你去搅拌,将你自己和作品在大都市的公共空间里搅拌到一起,搅拌出你自己的东西,从而让这个作品变成你自己的作品,这样才有你自己的观看。
3、到上海双年展怎么看?双年展需要怎样的观众?
双年展是庸俗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像战争一样的拉锯战,在争夺着观众的观看。另一方面,观众的观看也是非常势利、刁钻和挑剔的,因为就去一个下午,必须切割在每一作品面前的驻留时段。
怎么看。双年展的观看,尤其是视频的观看,最终权利都在观众手里。无论是纪录片式的,还是场景式的视频,你看到的就是一些图像材料,之后便是你怎么使用这些图像材料的问题。当然如果有的艺术家非要加个框,拍得很干净、背景音乐非常美妙,观众被拖动在其中,这也可以是一种设计。我的理解是,你不能要求双年展的作品很强势、要它非常像艺术作品,因为你看的全是图像,是一堆材料而已,就像在法庭上向法官提供的那些材料。你是法官,得来处理这些证据。倒过来说,你只有把它处理成你自己的纪录片,作品才有救,全靠你自己。
什么样的观看才是好的?
我们对于双年展的观看总是硬要弄得太学术、太软绵绵。实际上,自拍性的观看更是亵渎性的观看,才是双年展真正需要的观看。只有把自己的形象留在电影镜头里的观看才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打破偶像式的观看,才会看得有力量性的观看。
现在很多人都说生活碎片化了,其实不是生活碎片化了,是我们的注意力碎片化了,我们碎片化的生活是我们的注意力被碎片化以后,去过的那种由假象构成的生活,误以为这才是生活。结果,你的生活中被插进了美剧、奶茶、高跟鞋。你的生活中于是只有三分之一的真正生活,其它都是商品、图像和舆论以及口水和八卦。还有借口、不能实现的欲望等等,这些都是碎片,被你误当成生活,并不是生活本身碎片化了。喜欢在双年展里自拍的女孩子的注意力是碎片化的了,但是她的观看并不会因此而不好,在我看来这种观看是更好的、更强势的。越屌丝,观看就越亵渎。很多人会调整、会伪装,她还不伪装,是很真实地在别人的作品面前看自己,你作为艺术家把作品暴露在这样的眼光下面,我认为是天赐良机。
4、双年展中,艺术家要怎么表达或者说怎么选择主题才是讨巧的?
本届上海双年展有一个视频作品叫《黎明之城》,拍的东西非常的实际、原始,向理想主义者们提出了一种困境。它说,理想主义的城市大概是做不好的,只有乌托邦才是美好的。可是,现实总是这样地没救,我们都在假装能达到乌托邦。片子拍摄得非常脚踏实地,且具有时空感,直接把印度农村的样子放到双年展里面来、搬到上海来。纪录片之于双年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点,它几乎把原地时空搬过来。还有些比如农村、少数民族、森林问题的作品,都是直接将“在地性”搬过来,特别有力量。
视频作品《森林法》中,男主角讲的话语,很像人类学家或者哲学家要他讲的东西,带一点教训意味,比方说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这个错了,那个也错了,这种讲述非常地政治正确,但也弱化了作品。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用一种教学法,向观众示范:我这么讲不是直接教训你,而是我和你商量,这个话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如何和小朋友、和老人、和那些文明人或者另一些原始人去传递森林的重要性,这就牵涉到间距化的问题。你不能直接去控诉这个世界和这个制度,中间必须有一个距离,把作品放在教学法式这样的位子上,相对来讲看上去不会太生硬。
拍摄的真实性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让人在镜头面前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所以纪录片也是搭建以后得到的结果,和故事片一样,必须通过虚构来达到真实,朗西埃这样教导我们的。一个艺术家要真诚,但也可精心搭建,但决不能用搭建来掩盖搭建,那样便适得其反,纪录片里的真实性是慢慢地一点一滴建构出来,人为的,但被观众认可。太想要证明自己的真实性、证明自己的话是真理,就会显得很教条主义。
伟大的艺术家在实践中会把自己的工作弄得十分可疑,在创作的过程中将自己逼到感到无地自容,最后发现连自己的表达位子也不见了。上次我们说到一个先锋导演拍民工,拍着拍着导演感到非常无地自容,民工却像一个个史诗人物一样,像尤利西斯一样的神话人物,越来越有神的样子了。拍民工的艺术家必须反问自己:“我凭什么可以拍民工,这个民工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比我要强大,更像艺术家,我应该让位吗?”最后导演的位子在作品中就不见了,被解构掉了,这是我们当代艺术里如今已很政治正确的一个套路。如果你越拍越显得像个艺术家,越强大(像艾未未那样),一定是不合适的,艺术家需要给自己留出在民工前溜脱的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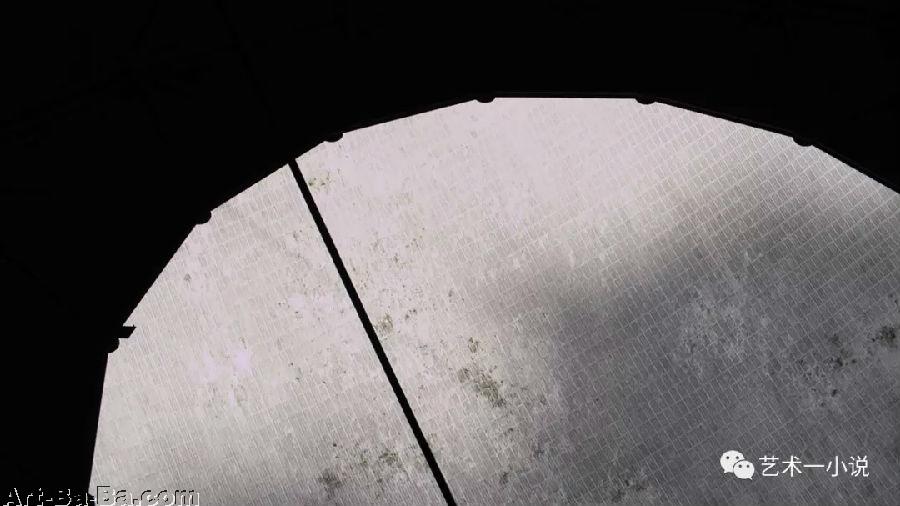
珍妮弗·阿略拉&吉列尔莫·卡萨迪利亚 《大寂静》 16'32"
优秀的艺术家会把好的媒介弱化,甚至弄得看不见,而《大寂静》里艺术家却把他能使用的所有媒介都裸露给了观众看,简陋、不够高级,这是故意的。这个艺术家把自己的方法论暴露在观众面前,这个就是很多的当代艺术创作的套路。这相当于是在向观众让步,艺术家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子上,很简陋,甚至还有些幼稚,本来这个作品可以用很高级的手段来呈现,但艺术家就是要故意退回到很粗糙、很直观的状态。我认为这个作品是艺术家对自己使用的艺术方法论的克制,于是达到了更大的公共性。他把自己的思考100%展示给了观众。不是说鹦鹉说的话有多重要,重点在于艺术家有多大限度把自己的创作方法暴露在观众面前。他不隐藏自己的表达背后的任何东西,这是艺术表达方法里一个很见份量的方式。这跟写小说、拍纪录片完全不一样。克制、谦虚,在观众面前艺术家必须要这样。《大寂静》这个作品很典型,南美洲、非洲很多艺术家都有这个特点,特别能够把文明人类非常复杂的东西简化成特别简陋的几个片段,我称他为编目化回退的姿态。这个姿态十分重要,这就是审美平等,艺术家在双年展这样的场合来表达,一定要把自己的位子放得比观众还要低,才对。这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我们常常喜欢要把自己的观念一股脑儿的讲给观众听,生怕观众听不懂。我觉得在关于森林、鹦鹉的这些视频里,有些观念艺术家自己也是不把自己的讲述很当真的。艺术家自己故意与作品保持距离,这就是所谓的间距感。
关于新技术运用。本届上海双年展许多作品用了无人机镜头(据我观察,甚至可以说——70%以上镜头是不可以不用无人机拍摄的),无人机的使用颠覆了观众的观看体验,给观众一种上帝视角,让观众有一种我掌握一切的上帝感觉。如果你不用无人机,有些镜头也是无法完成的。这就是上海双年展对于观众观看的争夺,如果没有无人机镜头,艺术家的作品里仿佛就少了一点东西,观众看过来就觉得味道不够,就像十三香小龙虾盘里只有十二香一样。
5、看展的时候艺术家表达的意义为什么不重要?
艺术家到底要不要在作品里填装点意义进去,要不要有一个态度,或是要不要和世界产生一些相关性,这是一直有人探讨和疑问的。问题在于,艺术家如果要有展览机会,能被策展人选中,就必须有“意义感”这种东西,不然是无法编目而入选的。但我觉得还不光如此,如果只是一个命题作文把题目选好了,被策展人选中,还是不够的。接下来就是题目的问题,是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关心森林还是艺术家的个人情怀,艺术家喜欢拍森林,这些东西怎么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作品,这事就变得很复杂。很多人开始装逼和无病呻吟。
我热爱森林,我要拍一个森林作品,为什么要拍森林作品?我要展览呀。为什么是森林?因为这个策展人喜欢森林主题啊,我不拍他或她会选择我吗?三重的虚伪和装逼,很多艺术家就认为自己只能这样。但是艺术家装逼不要紧,艺术家可以装逼,他是代理的,有经费就好。但是,你装逼后被阴错阳差地选中,这就是真的创作。我经常说到,艺术-政治主题,艺术-政治-审美主题,3-4个主题掺杂在一起,绝对不是像命题作文这么简单,后面的东西会变成很庸俗、很刻意、很生产化的。

乌苏拉·比尔曼&保罗·塔瓦雷斯《 森林法》,图片来自知乎(黄奎摄影)
2018-12-23 关于上海双年展的课堂讨论(录音整理完整版)
林碧纯:我觉得这次这个展览的视频占的比例特别多,这种情况是线下当代艺术展览的常态或者趋势,我印象中当代艺术中装置类展品给人冲击会大一点,双年展的视频作品和我们平时在家或者在网络上区别在哪里呢?
陆:你真的觉得没有区别吗,从哪个角度看?
林碧纯:应该是区别不大,你在现场看视频你必须完全的沉浸进去,但是你有时候精力有限,特别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双年展,精力无法很好的集中,特别是这次双年展视频占了60-70%左右,会导致我们精力无法focus在展品上。
陆:昨天我们也讨论到这个问题,现在有一种趋势,是“不敢不做视频”的状态,因为其他的作品都太弱了。但是关于双年展中看视频的经验,我觉得和在家里看是很不一样的。
张音彦:是一个看电影和看电视的区别吗?
俞昂:(双年展)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看)?
陆:还不止这些,你在双年展看的时候,你的身体整个掉在里面,和家里面、网络上、录像厅里看的感受太不一样了。而且还有一个时间分配的问题,一个下午只有4、5个小时,你看的时候要做取舍,你要感觉到双年展展览本身是个大装置,它他规定了你身体的和时间的切割,你其实是不自由的,你多看一会儿心里就很焦虑,觉得等会儿会少看其它的了,这就是双年展作为一个时间机器对我们的摆布,与在家里看就很不一样。昨天我还讲到观众在国际双年展中的普遍性经验的问题,这是我在全世界各地观看双年展得到的最深刻的经验,所以不能说和在家里电脑上看一样的,我觉得太不一样了。尽管这次上海双年展装饰装修可能故意做得简陋,,简陋得和80年代中国县城里面看港台录像片差不多,声音相互干扰,你会觉得太low了。但那是洞穴式观看,是当今很潮的方式。
林碧纯:这种声音干扰、简陋的环境导致你无法把精力集中进去。
陆:是的,但恰恰是这个东西我认为是有意思的,如果你很精致的,或者说画廊里的展览,保证很精致,保证场面和环境干净,但你看的时候你感觉没有那种在“洞穴”里的感觉。洞穴就是什么都很简陋、灯光一闪一闪的地方,是在别人的梦中做观众自己的梦,是梦里做梦,将观众自己做进这个梦中梦之中。
林碧纯:3楼有个作品叫“天堂电影院”,真的布置的像在洞穴里一样,用一个类似于蜘蛛一样的装置把投影仪架起来。
陆:这个现场反而给人感觉不强烈,1楼比较简陋,更有洞穴感。3楼这个等于说是一个隐喻,投影机放在蜘蛛上,我还拍了照,无非是说投影仪做了很古老的事儿。你这个问题戳到了一个点上:我们要到双年展装置里面去观看的原因就在于此。
俞昂:我之前去看上海影像展,有个作品是把实景和原画做了个结合,我觉得原画在影片中的运用应该可以拓展更多的艺术表达,我们看到现在双年展很多作品是直接拍的,是不是可以将原画这种表达方式更多地加入到影像作品创作中去?目前在国际影像艺术方面,有原画与现实取材相结合的作品这一创作趋势吗?
陆:我没听懂,你是不是说视频里面把好莱坞制作和艺术家自己的表达这两者作一种新技术式的结合会好一点?
俞昂:假的和真的结合,类似漫威这样。
陆:为什么你觉得视频要这样做?你要考虑到这个也是和时间有关系的,在无政府主义那个《黎明之城》,它的拍摄特别反对你提的这种技术。,它拍的东西非常的实际、原始,给理想主义者提出了一种困境,它说理想主义的城市是做不好的,乌托邦更美好,可是现实只是这个样子,但也没关系,我们假装能达到乌托邦就好,所以知道现在还是不够好的,好不好也不重要。这样一种态度是很特别的。我认为这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你讲的这种极端,另一个极端是很抽象主义的、象征主义的,非常脚踏实地,且具有时空感。我去过好几次印度,所以它更容易使我喜欢这个片子里拍摄的印度农村的样子。它竟然直接把那样的时空拖到双年展里面来、搬到上海来。纪录片很重要,就是因为这一点。几乎把原地时空搬过来了,在这个叫做国际当代艺术的普遍主义空间里。你刚才讲的是要反对这种时空,要把各方面都深化、处理得更加艺术,这我认为是错误的。纪录片似乎就是把真实的时空搬过来,使我们不得不沉浸其中,就完成任务了。它给我们时间。它帮我们生产出自己的时间。这个视频里的印度农村时间成了昨天下午的我的时间,这就是完成了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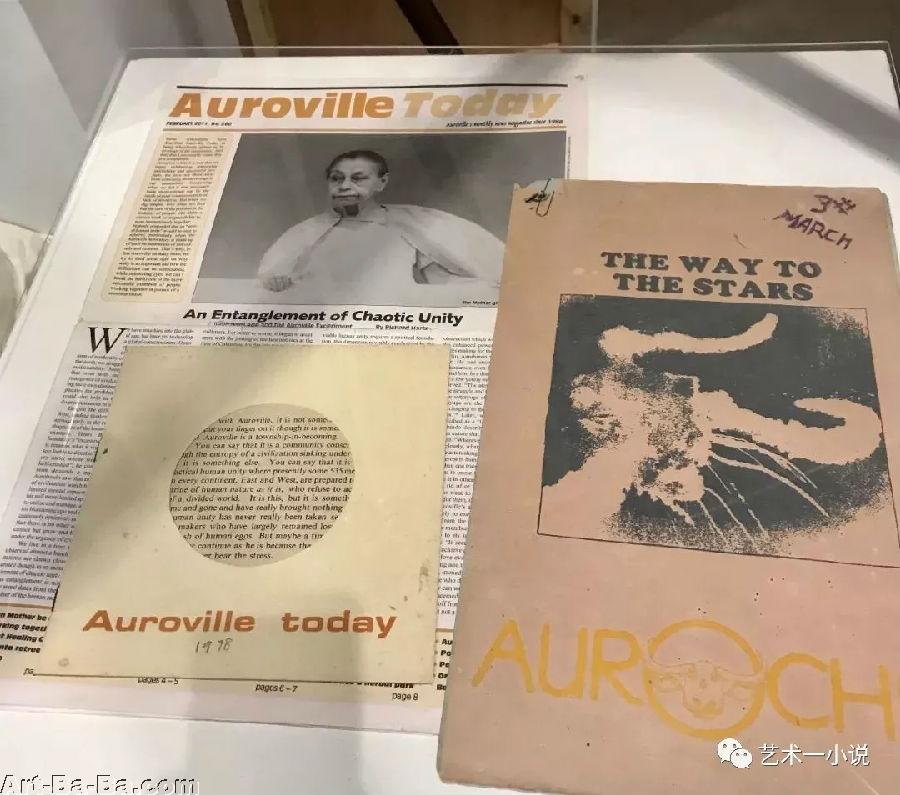
克里斯托夫·德雷格尔&海德龙·霍茨法因德《黎明之城》,图片来自网络
俞昂:是更有创作性,结合原画创作给影像作品更多表达方式的选择。
陆:我觉得说更有创作性也不对,这个印度无政府组织纪录片把印度农村搬到上海来,这个做法本身就已经很艺术性了。为什么还要额外去艺术化,或者说为什么只有你这样说的艺术化才是艺术化呢?艺术化肯定不止这么一种,当然你提的这种也属于艺术化,但不是只有这一种的。把原时间、原地点通过纪录片拍下来、直接搬过来,放到国际双年展的空间里就比用家里投影效果好,因为,这是在展览时间里发生,不是在日常生活的时间中发生。因为这一点,我认为将印度的时空搬过来是有道理的,不是说都应该这样,恰恰是有些东西比如农村、少数民族、森林里面抓拍的东西,放到国际双年展这种乌托邦空间里来,是特别好的。国际双年展是一个乌托邦装置,是我们要它那样的样子。在上海双年展这样的空间里,我们作为观众徜徉在里面,就是要让我们自己的欲望去欲望:在包托邦时间里生产我们自己的乌托邦时间,在电影院、电视和电脑屏幕前我们何尝不想这样呢!但是,我刚才在说,就双年展的空间里格外合适,更到位。
用了很多无人机镜头,也是因为这一原因,效果才会这么好:无人机的飞行带我们走向宇宙,走向宇宙时间。这在技术上超过了电影拍摄的能力。人走向宇宙,这正是德勒兹向往的电影的功能啊,但无人机能做得更好了!有了无人机拍摄后的电影,得好好升级了!
张音彦:老师,既然无人机效果好,那么作为同样是当代流行的拍摄设备,你对使用Go Pro进行的拍摄怎么看?
陆:Go Pro很原始,那个东西永远是被决定的,而且是被规定在运动轨道里面的,无人机是脱缰的,无人机比Go Pro高好几个档次,完全颠覆你的观看,可以给你一种上帝视角,让观众有一种“我掌握一切”的上帝感。上面说了,用不用无人机镜头,是一种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如果你不用无人机,有些镜头就无法与其它艺术家竞争。这就是你对观众观看的争夺,如果没有无人机镜头,你的作品里就少了一点东西,观众看过来就觉得味道不够,像十三香小龙虾里只有十二香。双年展是很庸俗的,像一个军事计划,像战争一样,里面是在争夺观众的观看。观众的观看是非常势利、刁钻和挑剔的。
俞昂:那双年展的组织机构是?
陆:国际上看,主要是特大城市的旅游局,将它看城市旅游的国际宣传的一部分。每个大城市都做了,圣保罗做了,上海也要做“世界的上海”。1996年上海双年展成立是由几个艺术家发动,市政府还不太支持,但是现在市政府很主动,圣保罗都搞了上海怎么可以不搞呢。2010年我参加了上海双年展的行动委员会,了解到邀请来的了圣保罗双年展的负责人据说还是当地黑社会老大,办双年展有另外的目的,洗钱或者说黑社会要改变自己的形象,都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当代艺术、双年展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比红灯区后面还要复杂的。
上海双年展的投资可以做到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目前最大的投资商是瑞士的Swatch公司但这个投资远远不够。上海双年展目前还是办得很小气的,市政府不敢乱搞,如果按照圣保罗的标准组织,上海可以举办全世界最好的双年展。有大型公司都想投资赞助,上海的市政府不让他们投资,因为这是准官方项目。
目前上海双年展在全世界的双年展中的地位大概是第五六的样子,威尼斯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柏林双年展,很政治化的,圣保罗可能在上海前面,骄傲一点也可以将上海排第四第五的。上海双年展和柏林双年展是没的比的,保守,搞来搞去就变得很中庸,比如今年这个标题太差了,什么叫“历史的矛盾”,“历史”如何矛盾呀,历史是我们写出来的某种类型的故事啊,是你自己看的时候你的眼光可能矛盾了,中英文标题都不好。观念没到一个卓越的点上,没有一个宏大的统帅一切的东西。柏林双年展一定不会犯这类错误的,主题和形象必须统一,比如上届的比特币政治这一主题,一定是一个很刺眼的点,相当于一个设计一样。上海双年展的题目一向都乱七八糟,请我策展也会是这个样子,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双年展后面有个领导机构也没关系,但是,考虑到我们一向错乱得厉害,下一届上海双年展咱们就不要用题目好了行不行?写作文离题会得零分,写不到扣题,那咱干要给自己出一个我们必须会离开它的题目,难道不应该?因为,不光是上海的双年展,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做法:由策展人与一个领导机构罗列当代艺术世界最重要的艺术家,电影领域、视频领域、装置领域、重大图像领域等等,一罗列,名单就出来,从中选前三名不就行了?反正在中国,我觉得领导机构肯定要来幕后操纵,策展人是幌子,所以还不如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就不会犯挂羊头买狗肉的错误了。
俞昂:出现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是中国人才华有限还是审核严格?
陆:都不是,举个例子,为什么现在大量的制作、技术上比较先进的公司都集中在柏林,这和小商品集中在义乌一样,比如在以色列死海附近拍的《裂谷横渡计划》,无人机工程师3个、制作团队33个人,制作好看的水面画面的技术也很复杂,观众愈发挑剔,你拍摄好的成品不去柏林过一过,这个图像质量肯定是不行的。这样成本本来是13万美元,去柏林做技术升级7万。20万美金的话就会制约作品的产生,一般的艺术家就不能碰,一定要有名的、收藏家已经看中了的艺术家才会投资。

西蒙 斯塔林《裂谷横渡计划》文献
田坤:老师那这些参展艺术家经费来源是?
陆:主办方给,大的、贵的装置就要双方协商,一般会有个天花板,各个门类的价格多少,大牌的谈判资格就多。
俞昂:看过了许多展览之后,是否只会挑双年展观看,其他一些商业展就觉得不好看?
陆:不一定,双年展像一个超市,有各个门类,其他展览就你可能想关心这个门类里最前沿的东西,其他方面没有区别。刚才我讲到艺术的生产关系。制作质量好的作品你看过以后,你就以为自己知道它的平均水平、较高水平、顶级水平分别是怎么,无非就是这样。但搞当代艺术难道仅仅是做这个吗?
孟迅:我对《森林法》这个视频,如果它想传达的是保护生态、保护森林的观念,我有注意到接受采访的这个男主人公,他穿的衣服、他的皮带、戴的手表也都是现代化的、森林之外的东西,那这种视频会不会像您说的质量被降低了,主旨也被某种程度上无形地弱化了,因为男主人公也在穿工业制品。
陆:这个视频里没有讨论到工业制品的使用和森林砍伐的关系,我自己的关注点不在此,我觉得男主人公穿着工业性的皮带问题不大,我主要关心里面他讲的话语,他话语很像人类学家或者哲学家要他讲的东西,这种讲述非常地政治正确。
俞昂:是否是他为了打这个官司特地去写了这个术语?
陆:的确有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这样表达,用另外的话语来说也很难,现在保护森林也是有一套话语来指引的,比如原始部落代表他们所处的被破坏的区域,来向我们文明人类来讲述一些东西,这个也是套路,但这个作品做的我感觉不太好的,主要他用的话语不对劲,他的语言带一点教训意味,比方说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这个错了这个也错了,这样话语我认为使这个作品不强大。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应该是用一种教学法式的表达,我这么讲不是直接的教训你,而是说我和你商量,这个话题是很麻烦很麻烦的,我们怎么样跟小朋友、跟老人、跟那些文明人或者另外一些原始人去讲森林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我代表森林来发言,直截了当来控诉或者要求你做出什么东西。
俞昂:这个片子这样的表述方式太强势了是么?
陆:我看是的,间距化不够,你不能直接来控诉这个制度,中间必须有一个距离。我和你商量,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向第三方来诉说这个问题,把作品放在教学法式这样的位子上,我认为相对来讲就不会生硬一点。包括杀大象的作品里,也有这个问题,用生命的颤抖、抽搐来要挟观众,这就有太直接的嫌疑,可能艺术家有不同的考虑。
季晨洁:那他这样的视频作品和纪录片有什么区别吗?大象和杀鲸的纪录片有什么区别?
陆:的确,这次上双很多作品都处在一个纪录片的状态里,大象和杀鲸完全是一个套路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纪录片可以作为艺术作品呈现在展览里面吗?从展览角度讲是不可以的,不可以拍纪录片,必须是视频,我们昨天也在讨论这个最终的认定是哪种现实的权利在谁手里的问题,有的艺术家选择放手,你可以把他当视频也可以当纪录片。双年展的观看包括视频的观看,最终权利还是在观众手里,观众没有看到纪录片,你看到的纪录片是没有框的,你是看了一些图像材料,之后是你怎么使用这些图像材料的问题。如果有的艺术家非要架个框,拍的很干净、背景音乐非常妙,观众被拖动在里面,这也是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你不能要求双年展的作品很强势、非常的像艺术作品,因为你看的全是图像,是一堆材料而已,就像在法庭里面提供材料,你是法官你怎么处理这个证据。倒过来反问,你有没有把他处理成不像纪录片,只有这样作品才有救,全靠你自己。这样说的话,搬进纪录片来,只要观众懂得处理,问题也不大。
孟迅:接着《森林法》这个视频,因为石油公司要进入森林,住在森林的原住民拒绝他们进入,他身上穿的还是那种现代工业制品,我想说如果给我们做这个视频,可不可以把他艺术化,我们能不能为了强化某种观念,让他穿的比较生态。
陆: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呢,这个就牵涉到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区别,你这种说法就是故事片。好的纪录片导演明白,所有我们的叙述、证据、揭露,都是破碎的、有问题的,哪怕是一个理直气壮捍卫森林权利为森林说话的人,他的证据里面也都是漏洞百出的,如果艺术家想要掩盖这个漏洞,就不是一个好艺术家了。拖泥带水、泥沙俱下,都是没问题的,这是一个做作品的伦理问题,纪录片也是搭建出来的,是你叫他站在镜头面前他才站到镜头面前,这个已经和换不换衣服没什么区别了。我特别赞赏《黎明之城》这个作品,特别好,作品里都是嬉皮士,本身生活过得已经够怪了,拍摄的镜头里小孩跳舞、很多人讲述都很自然,是演不出来的,我相信他绝对是真实的,虽然那个日常的东西看着很无聊,但特别真实。
陈凤:全球各地的嬉皮士涌到这个地方,构建了这个社区,但我发现他们还是有贫富差距的,不同的人住的房子,有的人泳池带别墅,有的人住集装箱,我好奇的点在于住什么房子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金钱没有关系吗?
陆:这个社区里他们所有使用的家具、财产都是共同分享的,只是选择成这个样子,可能在老家有点存款,但在这个社区里是不允许有人占有的。他们坚信未来会有更好的城市,所以目前只能暂时住在垃圾堆里面也没关系,他们所有人都认为那个地方是个垃圾堆,占有它也是没有意义的。可能社区里也有一个规则,尽管我们共同拥有,但你也不能打扰里面的人。重要的一点,你不占有,所有人也拥有你手里的财富,这个时候你就放松了,前提是所有人认为这个是没有意思的。60年代的美国有很多嬉皮士运动,在旧金山自治区搞过很多实验,这些自治区现在都荒凉了,现在在印度比较空旷的地方搞这个东西,有很多理想在继续,活在这个理想里,将这个理想生活搬到双年展的时间之中,是有意思的。这些人有的来自澳大利亚,有的来自法国,都是放弃原本比较好的生活过去印度的,在这个社区里没有货币,一起过生活,所以他们选择和是否有金钱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的问题很有道理,一个建筑师、一个很有文化的人,他在里面仍旧可以过着很好的生活,因为他善于利用现有的东西,文化的观念还是起了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既然是嬉皮士,他也不会羡慕另外一个人有文化,就过得比我文明,我就要妒嫉他,这他不会的,他看不上文明的东西。法国60年代的情境主义者德波,比G。C。D还要激进,既是个政治组织也是个艺术组织还是个共产主义组织。他认为这样一个点就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可以说,《黎明之城》里已经是共产主义状态了,过得好不好不重要,但这是起点。这么一个片子放在上海双年展,非常有意思,这么多人还在坚持这样活。
大家继续抛问题,刚才几个问题已经把双年展里面最最核心的逻辑扯出来了,怎么观看、怎么制作、怎么选择作品主题。
田坤:您的观点是说制作视频的时候真实性是最重要的,是不是说越真实越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你不能去摆拍
陆:不是说不能去摆拍,总是已经摆拍了,真实性不是说已经在就在的,是你让人在镜头面前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所以,纪录片也是搭建以后得到的结果,和故事片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好的艺术家要真诚,已经搭建了,不能用搭建来掩盖搭建,那样很假。伦理上讲,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纪录片里的真实性是慢慢一点一点建构出来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有的电影、视频,都要调试,这个调试不是艺术家能完成的所以虽然你讲真实,但是最后还要调色,一调色整个都变了。什么叫真实性,刚才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
张音彦:那《黎明之城》拍摄的那些嬉皮士,他们在镜头下还是做真是的自己,是不是?一般情况下,纪录片拍摄时势必会要求镜头前的人去表达一些看法,比如在《森林法》中,被拍摄的那个人一定会紧张,那个说话方式就变得不真实了,所以《黎明之城》的好是不是在于那些人面对镜头的状况是最真实的,他们还是做自己、不紧张,是这样吗?
陆:不光这样子,不仅仅是镜头前老练不老练的问题,《黎明之城》里面的一个人物讲得很好,是用印度语在讲的问题,为什么要过那种生活,为什么艺术家去拍那个生活能保证相对真实,因为他抛弃了占有感,我们在座的人都是一个个拎着超市塑料袋消费的畜生,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面,为少部分人数钱,然而我们还快乐死了,谈何真实性。就算是笑得美丽一点,无非是像范冰冰这样的女明星笑得美一点而已,但还是畜生的笑,相当于是为了人而去过人的生活。这个片子已经不光是真实性的问题了,而是他们因为相信某种观念,而成了艺术家的问题。将一种不好的生活过得像共产主义生活,这不是伟大艺术家才能做到的事吗?
张音彦:那这样岂不是被拍摄者才是艺术家本身,那作为拍摄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陆:对比之下这个艺术家显得比较差,使得拍摄这个视频的艺术家反而有点半艺术家的意味,很有意思,我认为这个点很好。拍摄过程里显出拍的那个人很有问题很可疑,这就是很伟大的艺术家,在实践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工作变得很可疑、变得不合法,好的艺术家都是这样,在创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无地自容,最后连自己的位子都不见了。上次我们说到一个先锋导演拍民工,拍啊拍啊导演感到非常无地自容,民工像一个史诗人物一样,像尤利西斯,等于说神一样的人物,拍民工的艺术家反问自己,我凭什么可以拍民工,这个民工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比我要强大、比我更像艺术家,最后导演的位子就不见了,被解构掉了,这是我们当代艺术里很政治正确的一个套路。如果你越拍,艺术家越强大,一定是不好的。

珍妮弗·阿略拉&吉列尔莫·卡萨迪利亚 《大寂静》 16'32"
陈洁:刚才大家讨论到拍摄的真实性包括色调,好的纪录片里面也不一定是需要这样,像这次上双的《大寂静》,拍森林里的鹦鹉,故事是虚构的,里面也不是站在一个责备的角度,鹦鹉说“人类的活动已经让我们濒临灭绝,但我不怪他们。我知道他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不太关注我们而已。”而且我觉得里面用了很多的方法,包括把纪录片和特德·姜小说《大寂静》结合起来,然后又把他和一些人类学的问题结合起来,举了4个人类学的问题:毕达哥拉斯派的神秘主义者、五旬节运动、婆罗门教,包括还举了一个费米悖论,我觉得艺术家对各个方面的知识必须是很了解,他的镜头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森林的镜头、配曲和字幕,然后就开始讲故事,所以我觉得这种有很深的道理的作品里面镜头其实都不要紧。
陆:你刚才讲的完全不是一个视频了,像一个幻灯在教室里面给学生讲一个故事差不多,这个也是好的,比较简单的比较原始的艺术方法,像下棋一样的,让给观众两步棋,这种做法是加分的。
孟迅:《大寂静》里有一些话是主观的,代替鹦鹉去说的,那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掺杂了一些主观的思想在里面,实际上和鹦鹉并没有关系。
陆:实际上这种讲述是荒唐的,是一种夸张的寓言,他这个故事讲的不像是对儿童讲的,把人类学、天文学这些全搅在一起,我觉得你讲的是艺术家对媒体的解构的问题,优秀的艺术家是把好的媒体搞得看不见,而这个视频里艺术家把他能使用的所有媒体裸露给观众看,而且很简陋、不够高级,这个是故意的,这个艺术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方法论暴露在观众面前,这个就是今天的很多的创作的套路。这相当于是在向观众让步,艺术家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子上,很简陋听上去还有点幼稚,本来这个作品可以用很高级的手段来做,他故意还原到很粗糙、很直观。我认为这个片子是艺术家对自己使用的艺术方法论的很克制的、非常公共性的,把自己玩的讨论100%展示给观众,不是说鹦鹉说的有多重要,重点在于艺术家有多么把自己的创作方法暴露在观众面前,他不隐藏,这是艺术表达方法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写小说、拍纪录片完全不一样。很克制、很谦虚,艺术家必须要这样,在观众面前。这个作品很典型,南美洲、非洲很多艺术家都有这个特点,特别能够把文明人类非常复杂的东西简化成特别简陋的几个片段,我称他为编目化。这个姿态放在里面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审美平等,艺术家在双年展这样的场合表达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位子放得比观众还要低。这是很多人会犯的错误,一定要把自己的观念一股脑儿的讲给观众听,生怕观众听不懂,我觉得在森林、鹦鹉这些视频里,有些观念艺术家自己也不当真的,艺术家自己会故意保持和作品的距离,就是所谓的间距感。
陈洁:那这个视频里面他举的人类学与语言关系的例子也可能是假的对么?
陆:不是假的,就是引用而已。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双年展?这是因为,我们周围飘忽的图像,平时都是在网络上或者书本上了解,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他,双年展作品的意图在于迫使你去搅拌,搅拌出自己的东西,从而让这个作品变成你的作品,这样才是你的观看。
张音彦:说到把技术展现给观众的话,我看到有个作品叫《消音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放的视频是交响乐队在演奏,照理说作为一个听音乐的人,是想听到音乐的乐音的,但是我只听到乐器使用摩擦和演奏者气息的声音,我会比较好奇这个声音是怎么录出来的,但是这个作品想表达的含义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想要听的东西反而听不到了。
陆:我觉得这和媒体有关,指出我们的媒体错觉。平时我们欣赏音乐是和这个东西有关系的,其实光去看这个动作,也只是杂音而已,唱片的音乐是反复修改过的,是商品而已,是假的不真实的。乐器在音箱里发出来的东西和录音的时候被修改过的东西是另外一回事,记录这个东西的意义,表示你平时听的里面有很大的错觉空间在里面,在提醒你这个东西。这就是用媒体本身做了一个作品,媒体无非是这样的东西。
廖芳芳:这次印象深刻的有2个作品,一个是《排演》,有3个场景,刚进去有2幅画,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直接走到观影区,拍摄的就是一个小红车在爬一个很陡的坡,一直爬一直爬,但就是爬不上去。我本来想拍照,发现后面坐了一排人,大概是在期待小车什么时候爬上去,我就觉得这其实是很简单一件事情,但是会把人吸引过去,一直在期待跟着他的爬坡速度。我再回头看这个作品外面的图片的时候,他说是一直在循环,作者表示这是他对时间性的一个解读,是不是和时间性、普遍性有点相关。第二个作品是一个人,在十字交叉口摔倒了,艺术家用9个镜头来描述这个事件,一开始我们在第一个镜头只是看到他摔倒了但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摔倒的,然后另外一个镜头知道是一个狗过来冲撞了他,然后另外一个镜头是狗的视角它在觅食,从狗的角度来说是人冲撞了它但只不过狗没有摔倒,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你看着就很有味道,这种事在生活中很常见,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电影中,出现的特别多。
陆:这个作品很典型,我都没有完全看懂,你一说我懂了很多,因为我没有耐心只看了2分钟就走掉了。音乐非常抓人,相当于解说一样的,是现场的乐队很粗糙的音乐,这个事件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无法解释的事件,艺术家在很固执的讲一个道理,其实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艺术家在讲述中解构这一过程,直到最后散开,你感觉到像一个数学公式一样,回头走开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悬在那边。什么是事件?它是黑洞。哪怕倒下去这个事情,一旦要解释的时候,是无法解释的,原因和结果全在一个黑洞里面。但这么小一个事情,墙上挂了很多小视频,艺术家非要你看这个,非常粘人,带着调戏、玩弄的意味。这个作品胜在他的姿态里,他对图像的表达很简单、很简陋、很抓人,这属于策展人很喜欢的作品,这个作品可以打75-80分,一定在平均分以上。他没有一个特别深奥的东西在里面,但展览需要这样的作品。。
杨毅:这个作品是吸引我们的好奇心还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视频是照一幢楼,照各家各户的阳台,从下往上照,照了好久,其实也好无聊,但是我就一直站在那不想离开,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头,一直站在那看他播完。
陆:你看完会觉得浪费我5分钟,但回头一看又是有意思的,因为他简单、不复杂。你说的这个作品对我们这种受过教育的观众会好一点,看了2分钟会发出“我这个好奇心、我这种窥隐癖,真恶心”,但对于那些从来不看电视、不看艺术作品的人第一次看打击很大,我看1分钟就明白,是挖苦我这种窥阴癖,我们城市里面许多人喜欢偷窥,这个作品就在玩弄你、挖苦你。他的技术要点我认为是,这个无人机这么这么稳定的,看着像无人机的广告——我们的无人机是不抖的。
孟迅:你是否有注意到在不起眼的角落,有老鼠的干尸?每个干尸前还放了一面小镜子,这个作品您能解说一下吗?
陆:我看到报道了,对比一下这个作品不怎么样我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游戏。第一天的报道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拍成照片,我进去反而没有新鲜感了。这个也是对双年展这种严肃展览的一个调戏,双年展展示装置的自我调侃,艺术家自己也不当真,与自己的作品保持距离感,这样的展示才有效果。如果100%相信,就变成推销自己的展品,成了商业展览了。当代艺术展览里面带着很多的游戏、反思,或者自我调侃。
张音彦:来拍照啊,老师你对他们拍照怎么看?
陆: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在某个电影镜头里面拍。是啊,我们对于双年展的观看太学术,只有自拍性的看才是真正亵渎性的看,才是双年展真正需要的看,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成立的。我们的看还是太软绵绵的看,只有把自己的形象留在电影镜头里的看才是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打破偶像型的看。
张音彦:那个24小时时钟的作品就被破坏了。
陆:我们对比一下,我们这样的学术性地看双年展更需要,还是他们的看双年展更需要?我现在要强调的是他们的看双年展才更需要,我认为他们的看有一种特点,热爱自拍的人是特别三心两意的人、特别分神的人,我认为我们时代里真正伟大的看的人都是这种人,像打印店的店员边聊桌面微信边给我打印文件,一个眼睛看3个东西,一个脑子三个用。我真觉得,弹幕型的教育是未来,一对一的课堂教学将被淘汰。双年展需要这种弹幕式的观看,像打印店的女孩、像儿童的观看,才是更有价值的观看,我们的观看没有价值。观看的平等、观看的人工智能走向、观看的走神化,观看的亵渎的后果,双年展没有这种亵渎、没有这种分神、没有打印店女孩子这种观看,双年展是不成功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问题,也是我们一个未来的问题,太重要的。
我在看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双年展是为谁制作的。打印店的女孩付不起30块钱,这个钱她可以买杯奶茶,但恰恰是这种打印店女孩才需要去看双年展,你们去看就太意识形态化了,太被自己脑子里的观念左右了,你以为对艺术家的表达方式、对他们艺术理念的批判,有意义吗?让打印店女孩、儿童去看,他们的批判可能是更加压倒一切的批判。首先,他很刺激,然后他打开了自己最原始也是最具创造性的批判。如果8、9岁的儿童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看双年展,他会做出很伟大的批判。那样的观看那样的批评我认为是更加有效的观看,我们只能学术型、思想型的观看、批判。
龚云斐:双年展其实潜移默化在推进着社会进步,每届双年展都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我看来都是比较有启示性、功能性的,对社会、对人类世是有思考的。我认为还是需要能看懂才有意义。儿童最多是看图像,他们不会有很强的思考冲击,而成年人会有意识地去理解这个作品要表达什么观点,会很有感触,并且联系自己成长过程会有所思索,对人类社会也会有思考。
陆:刚才我们在讲儿童和打印店的女孩子他们看不懂,我们讲的是看不懂不要紧。双年展对你思考的启发可能是第二位的,你从新闻媒体里得不到思考、从这里得到思考,双年展我觉得远远多于这个东西。我认为你这样的观看过程是非常保守,在我看来是反动的观看。你如何很生猛的去看他,对于我们受过教育的人,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受的教育对我们看当代艺术是有害处的,你已经按照惯有思维去看待这些事物,这样是有局限性的。看待本质需要阁悬思维的框架,当代艺术对你的冲击是有很多层面的。
双年展到底要怎么看,抽象的讲,双年展有大量的图像,图像都是垃圾,图像并不是那么高级的东西。如果一个艺术家说我作品很高级,一幅画非常美,你说狗屁,我只是把你当图像而已,你个人拿到图像以后,像玩扑克牌那样玩、搅拌,产生新的东西,这就是你的图像了,这个鹦鹉,这个森林都是你了的。这个时候你发现意义了,这个伟大的意义是你的,不是艺术家的,也不是双年展的,而是你自己生产出来的意义。双年展或者说当代艺术形态这种作品的展览,观众进去以后有100%的权利。
龚云斐:那我觉得在双年展里拍照的参观者也是艺术家,特别的Cristina Lucas的《顺时针》装置,这个装置表现形式极致简约且具有线条及设计感,他其实非常讨巧,人进去以后自己也成了装置画面的一部分,对拍照的人而言,他们在空间中的留影就是变成了一幅专属的新作品,对这样而言在艺术展里拍照的人其实是很沉浸其中的。
陆:刚才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尤其是破坏性的拍摄是非常主观的,把自己很难看或者美丽的脸放在其中,对双年展是有作用的。亵渎的、恋物的、甚至是自恋的自拍,对双年展更有好处。我们的观看都倾向于太卫生、太紧张了,是自己过滤的,其实没有包袱的、那种脏脏的观看反而更好。又比如说欧洲教堂为什么要有穹顶画和彩玻璃,画很多裸体女郎,也是提供给做礼拜的人看的,听不进牧师讲的,就需要观看这些来分神、排挤空虚感。在我看来,越没有艺术素养的人,看得是越珍贵的。
孟迅:我们大众看会看背后的东西,昨天发现有个小孩就专注老鼠的东西,他这种观看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打印店的女孩这些?
陆:不类似,他这个是完全自我沉迷的游戏性的观看。打印店的女孩是分神的、会拐弯的观看,儿童还不会。这个是由消费主义,大众媒体环境造成这样的,现在很多人都说生活碎片化了,其实不是生活碎片化了,是我们的注意力碎片化了,我们碎片化的生活是我们的注意力被碎片化以后去过的生活以为是生活,结果生活中插进了美剧、奶茶、高跟鞋,你的生活只有三分之一的生活,其他都是商品。还有借口、不能实现的欲望,这些是碎片化,并不是生活碎片化了。那个女孩子是注意力碎片化了,但是这个人的观看并不会因此而不好了,在我看来这种观看是更好的、更强势的。很多人会调整、会伪装,她还不伪装,是很真实的观看,你作为艺术家把作品暴露在这样的眼光下面,我认为对你是非常好的一个衡量。
孟迅:或者还有一种他已经不止是注意力的碎片化,他是完全不感兴趣,进去以后不久就出来了。
陆:我认为他不大可能走掉的,双年展这么多作品里一定会有抓住他的东西,双年展是一个嘉年华,他有所有人要的东西还有积木呢,幼儿过去也是可以玩玩的,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双年展是一个非常无耻的装置,是为最低的审美底线的人准备的,我认为打印店的小女孩绝对不是底线上的,还在中间左右这样的水平。双年展艺术关注的幅度宽了很多很多,和一般的展览完全是不一样的。
杨毅:那老师我们看展的时候艺术家表达的意义不重要,那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想传达出创作的东西重要吗?
陆: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艺术家到底要不要在作品里有意义,到底有没有一个态度,到底有没有跟世界的相关性,观众要不要知道这个问题,问题在于他要有好的展览机会,他要被选中,如何被策展人选中,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是无法入选的。但我觉得还不光如此,如果只是一个命题作文把题目选好了,被策展人选中,还是不够的。接下来就是题目的问题,是政治和艺术的问题,关心森林还是艺术家的个人情怀,这2个东西一定要弄上去,还是艺术家的个人审美爱好,他喜欢拍森林,这些东西怎么搅在一起成为一个作品,这就很复杂了,很多人就装逼了。
我热爱森林,我要拍一个森林作品,为什么要拍森林作品?我要展览呀。为什么是森林?因为这个策展人喜欢森林主题啊,我不拍他会选择我吗?三重的虚伪和装逼,很多艺术家这样,但是艺术家装逼不要紧,艺术家可以装逼,他是代理的,有经费。你装逼,阴错阳差被选中,这就是创作。我经常说艺术-政治主题,艺术-政治-审美主题,3-4个主题掺杂在一起,绝对不是命题作文这么简单,后面的东西很庸俗、很装逼、很生产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