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riggerFinger 触发
时间:2019年03月01日
分享人:蒲英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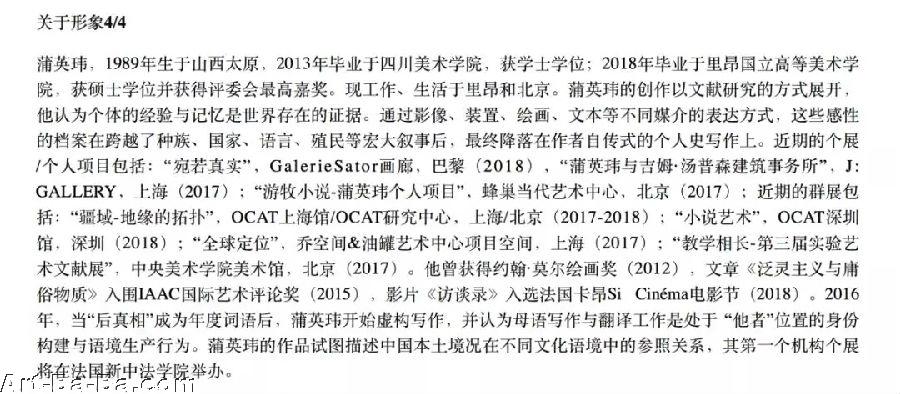
蒲英玮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认为我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艺术家身份的结构。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艺术家CV包含出生年、现居城市、学历、奖项等,但其实我觉得这种职业化的写作简历是非常不完整的,或者说是非常形式主义的,它通过一些展览经历来打空了艺术家本身的东西。
如果CV是一个阐述艺术家基本背景的文件,那么我的完整CV可能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的小自传,例如我的出生环境和家庭生活经历,这些是决定性的,导致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第二部分关于形象,是我用第三人称写的针对我到法国后对身份政治问题的研究,区别于第一人称的我;第三部分更像个宣言,它的目的是希望跳脱民族国家的叙事,用相对自由的叙事来建立一种身份政治。这四个部分共同构成了我所谓的CV,我认为这个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蒲英玮”头像 © 艺术家
这张头像照片来自我的第一个展览,在北京的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当时展出了很多我在法国收集的殖民时期关于黑人或北非国家的名片。其中有一个国外策展人,他非常质疑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不好好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反而去讲别人的故事。1989年后的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在探讨中国本身,在西方世界并没有话语权,但今天西方给了我们话语权,让亚洲人在国际双年展或文献展中有了一个位置,这其实也是一种暴力。
换句话说,作为中国人被强制要求以中国的方式,去讲述中国本土的故事,我觉得这产生了另一种身份政治的暴力:你的身份永远被钉死在了这个民族国家政治的框架下。当时做这张头像相当于是一个玩笑,从2017年开始使用。有趣的是,因为没多少人见过我本人,他们把这张头像和我的作品或写作结合,会觉得非常顺理成章,似乎是一个亚洲跟非洲的混血在研究这个课题。然而意义就在于,当你觉得一切都顺理成章但并不是真实的时候,就会对身份政治叙事的逻辑和局限性产生思考。

关于异域文化的恋物 © 艺术家
展览里所有的物品都来自于这张图像,我把它命名为《关于异域文化的恋物》,这个收藏是我到达法国后开始的。我父亲有收藏的习惯,所以我也自然而然地会每周去跳蚤市场买东西。我在法国读书第三年的时候搬家,把这些收藏全部整理出来了,发现其中没有一份东西是非常欧洲的。它们大部分是关于黑人、阿拉伯人或东南亚人。于是我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会不由自主地对这些东西产生亲切感?后来我得出了一个暂时的结论,那就是我和这些相对白人来说的少数群体是在同一个位置的。
收藏中有很多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殖民时期的明信片,它们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崭新的明信片,展览也以明信片的名字命名,叫《游牧小说》。我在这些明信片上写上自己的故事,然后寄给我的家人。很多人认为这个展览是研究后殖民话题,但其实并不是,我只是把殖民的故事作为一个自我的比喻。
我认为去西方留学是一种当代的殖民行为,因为如果我们想进入当代艺术体系,我们就不得不去某些国家,获取知识和思维去理解当代艺术。每一个到西方国家去学习的人都被会另一种思想所”殖民“。另外,这些明信片经常印有传教士去照顾非洲的小孩或帮助建造房屋的场景,所以”殖民“是一个非常暧昧、复杂的过程,不完全是残忍或暴力的,我倾向于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

威尼斯人 © 艺术家
这张照片是我的手和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中的一页。这个小说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它描述了马可·波罗在向成吉思汗讲述他在旅行中遇到的不同的城市,有些城市非常奇幻,而有些非常血腥。在这一页,成吉思汗问马可波罗:“你给我讲了这么多城市,但是有一个城市你从来没有讲述过,那就是你的家乡威尼斯。”
而马可波罗的回答是:“亲爱的大人,其实在我讲述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威尼斯的影子,威尼斯就像水中的倒影映射在我讲述的每一个城市当中。”我觉得这句话关于另一个思考维度,就是当我去讲述其他群体时,我二十多年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包括一些根深蒂固的伦理或价值的判断,也都会反射在我对表面上看是“异域”文化的实践当中。这可能是我工作的一个位置。
蔡星洋
你谈到了西方当代艺术的话语体系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你的思考方式,这本身是一个后殖民理论的框架。后殖民理论很重要的部分是讨论了地缘政治当中在地文化的丢失。当你接受了这种权利的构架或话语体系时,你就相当于是被后殖民了。那么你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虚构自己的身份而受到争议?我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做这个作品时,可能会被质疑一个黄种人是不是有权利或是立场去扮演这个身份。
蒲英玮
不管我们今天关注的是不是后殖民话题,我们都处在后殖民的框架当中。刚才我说这些项目不是在研究殖民问题,我指的是它们没有那么有针对性,更多的是通过情感来连接。这个作品在法国受到的争议其实还好,因为法国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白人跟阿拉伯人之间,但在美国可能反响会非常不同。之前有一个法国艺术家,他来自阿尔及利亚,也是法国的前殖民地,他在美国就遭到很多争议,说作为一个白人不该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产一种在哪里都适用的“身份叙事”或“身份政治”,“政治正确”这件事不是排在首位的,而是需要被争议的。
我是在2017年做的黑人头像,当时在法国并没有太多争议,仿佛亚洲人跟非洲人是同一战线的。但在2018年的春晚上,有一个小品节目是一个中国人把自己涂黑扮演非洲人,还去唱中国的赞歌,当时西方媒体把这个视为一个丑闻。今天,中国在非洲的行为让中国跟非洲之间产生了一种分野,不管是经济殖民还是资源交换,中国似乎滑向了帝国主义,凌驾于非洲之上。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再回到问题本身,我认为如果要提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某些社会语境当中必然是不成立的。我宁愿一个作品在某一社会语境当中带有针对性和力量,而不是遵从所谓的“政治正确”。
姚依凡
这个作品确实在美国会受到争议,虽然一方面来说,你本身的背景会让你在看另一个文化时产生新的东西,但也正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你所感受到的并不是他们最真实的感受。请问你在做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去做足够的研究或采访让你更接近他们的视角?或者你对其中的差异性更感兴趣?
蒲英玮
首先,一个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追求的是真实,那么我们就会丢失丰富度或多元度。当一个外来族群去探讨另一个族群时,所有东西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相互尊重、诚恳的观看前提之上。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些目光是带有非常多偏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回去反对或抵触。但也有很多来中国的学者,像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弗朗索瓦·朱莉安(François Jullien),他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但从来没有想要完全以中国人的方式思考。相反地,他通过自己的欧洲背景和具体研究,以诚恳的方式来观看中国,这给中国的传统思想带来了新的视角。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目的,虽然我们受到某种身份或族群的局限,但我们还是有权利对其他事情感同身受。
比如说,在2015年的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当时所有人都上街游行去反对恐怖暴行。难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没有权利对法国的事情产生悲哀的情绪?在2016年,法国有一场叫“黑夜站立”的游行示威活动,有一群人在我家门前发生械斗,警察投了带有胡椒面的烟雾弹,我一出门眼睛就被刺痛得不行。那么,难道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我就没有权利去表达我对这个事件真实的情感吗?我觉得这种思考逻辑有点矫枉过正。
目前而言,我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是既能政治正确又能挑战身份政治框架的。但是我有两个初衷:首先,充分尊重及尽可能理解另一种文化;第二,如果在不做和产生争议之间选择,我会选择去做,尽管它会突破边界。
蔡星洋
展览中的杂志是你自己在做吗?你个人还是一个团队的方式工作?
蒲英玮
对,《地缘》是我一直在做的杂志。我觉得出版物在欧洲和美国都非常普遍了,但在国内大家反而不是特别重视,可能因为展览的出版物卖不了多少钱,又需要成本和精力去校正和制作。可是为什么我要坚持在每个展览中都有不同的出版物呢?因为我认为出版物是一个潜在的、非常强有力的媒介,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展览中观众能触摸、传阅和带走的东西。

GEO地缘 © 艺术家
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出版物不完全是关于我的,有时候是关于别人的,比如说这一期是艺术家陶辉。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虽然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时你也生活在某种大背景下。如果某一天你更理解了另一个人,那么你也更理解了你自己。这个杂志命名为《GEO地缘》也是因为我认为人的构成就像地图的坐标系,参考线画得越多就越准确,但你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完全精确。其实到另一个环境中去学习,或是思考另一种文化,也算是在给自己建立参照物,参照物越多,世界可能就相对的越真实。

西方客人·玛丽安娜 © 艺术家
接下来这个展览是在上海西岸的油罐艺术中心,场地的对面就是黄浦江的两岸,然后会有一座桥去连接两岸,所以这个展览是在这种特别庆典的基调下展开的。展览中分别有一些留美的和留英的艺术家,然后我是留法的,所以展览叫《全球定位》,似乎特别地简单粗暴。

《自由引导人民》,欧仁·德拉克洛瓦,1830
当时我觉得,既然我是由于这种身份背景而被选择的,那么我就把它当成作品的上下文关系。我在跳蚤市场上买了一个特别粗枝滥造的铜像,然后编造了一段关于玛丽安娜的故事,还有一些虚构的文献。玛丽安娜是法国自由平等的国家象征,也是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中象征共和制度的反抗人物。
蔡星洋
这个作品的背景内容是什么?除了去虚构了这个场景,它下面的文字和虚构的内容是什么?
蒲英玮
这个文字有五段,每一段分别对应了我在法国的五年,也是五次跟玛丽安娜形象的相遇。第一段是我刚去法国,在卢浮宫看到《自由引导人民》中玛丽安娜特别宏伟的形象;第二段是在里昂的郊区维勒班,那里居住了很多外来人口,法国政府把玛丽安娜铜像安置在那里,象征着法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会同样普照着外来移民;第三段讲述了玛丽安娜铜像在一次混乱的争执当中不知去向;第四段是这个铜像被我在一个废弃的角落里找到;第五段就是玛利亚娜铜像来到了中国。

西方客人·玛丽安娜 © 艺术家
这五段文字是非常象征性地平行于我在法国的五年经历:第一年是刚来到一个欧洲的传统国家,接受到不同的文化;在第二年会发现你在这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其实并不是美好光鲜,它有很多粗糙的地方和潜在的争端;第三段对应的是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爆发的那一年,也就是大家公认的整个欧洲特别向右转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五段是随着不同事件所展开,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呈现了我对西方世界的理解的变化轨迹。
蔡星洋
你作品当中很有意思的策略就是去虚构一个身份,然后用替代性的身份去讨论问题。我在想,因为你的呈现方式很多是文字和长时间对话的影片,对于一般观众来说这会不会相对枯燥、比较难以阅读或接受?
蒲英玮
对,在第一个展览以后,我就做出了调整,之后的展览都比较视觉了。文本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我也在自我调试的过程中。我在第一个展览中直接呈现了文本,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文本在展场中的传递性并不是很强,所以之后文本被做成了出版物,大家会拿起来翻看,使得它更有效。另一种方式是把文字做成墙纸,直接呈现在展厅中。其实我没有太多的主要呈现方式,更多的是比较和分析每一个展览的环境和语境,然后提供一个我认为合理或有效的传递方式。
比如说,如果是在公众微信媒体流量非常大的场地做展览,那么我可能会把文字彻底地转移到微信公众平台。其实今天的展并不是只是现场,还有前期的媒体发布和后期的评论写作,它像是一个在不断传播的事件。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自己的简历做成那样,因为简历在展览中往往是不可见的,但它流通在很多其他领域。所以,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其实包括一个整体的叙事,而不只是展览现场。
徐抒文
你的作品有很多和文本、历史相关的主题,请问你的背景是什么?

新界杂志 © 艺术家
蒲英玮
我之前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的。在一开始我是完全不写东西的,当我到法国后有一年时间在学法语,那一年也没有工作室,很枯燥。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我只能通过写作去创作。后来有一个系列作品叫《新界杂志》,每次我对郊区考察完后都会做一个杂志,算是考察的笔记。出版物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张A3纸的黑白打印。因为当时美院学生打印黑白的东西是免费的,所以我就用这种最低成本、最普通的东西去做一个杂志。当时杂志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不仅仅要有自己的内容本身,也要有我当时工作条件限制的背景。当然它也并不是限制,而是一个创作的出发点。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做作品的。
徐抒文
当时是写法语写还是中文?
蒲英玮
都有。当你没有材料、时间、工作室或其他任何条件去表达的时候,写作就像是来自于你的求生欲。一开始我是写展览,后来希望能有一些自主性,所以别人让我去写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没有去写他的展览,反而是虚构我跟一个不存在的艺术家藏家的对话。当时第一次尝试这种半虚构的写作,它介于艺术界中流通的通稿和创作之间,编辑都特别迷惑。
后来自然而然地,我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了这些半虚构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对现实中模拟化、职业化的艺术家身份的修正。就像是第一次个展中,我没有把我的展览和教育经历写出来,而是放了一段我的家庭介绍。当时大家觉得很疑惑,但疑惑过后他们也都能明白这种置换。我觉得在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流通领域中做出某种改变,可能会解锁一些东西。

告别 © 艺术家
这是我在法国的最后一个作品,是一封信。当时我要参加一个展览,但我的签证要过期了,我必须在签证到期之前回国。所以我给学校的教务处留了一封信,请他们在展览的时候打开这封信,读完以后寄给我。这封信里除了有我对法国老师的告别和感谢,还有一张Carte Vitale,法语中意思是“生命”。它是一张社会医保卡,在法国非常重要,一般人绝对不会把这张卡随便给别人。然而,当签证到期的时候,它就是一张毫无用途的卡片。这也是一件小作品,或者说一种做作品的方式。另外还有个国内展览,开幕时每个艺术家被要求介绍自己的作品。由于当时我在法国无法参加,我给策展人写了一封信,说我这几年并没有主要在中国生活,所以缺席本身反而更符合我真实的状态。这些都是建立一种逻辑关系的方式。
在2017年,我在深圳有个讲座,我知道在场没有一个人见过我,所以我找了一个法国朋友,让他作为主讲人以第一人称去讲,然后我在旁边作为翻译。这个朋友之前完全没有看过我的作品,讲座中如果他突然有一些自己的联想,就会把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同时将我的作品扩充了。我会不停地把自己的身份虚构,或者再拿另一个东西把自己的身份置换掉。在这种反复的置换当中,我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经验,拓展了自己的作品。

蒲英玮与吉姆·汤普森建筑事务所,上海J:GALLERY © 艺术家/J:GALLERY
在展览《蒲英玮与吉姆·汤普森建筑事务所》中,我也虚构了一个叫“吉姆·汤普森”的人物。其实在泰国有一个吉姆·汤普森之屋,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二战前是CIA特工,二战后到泰国成为了一个丝绸商人。他在大概67岁的时候,在雪山旅行中凭空消失了,他是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消失了的人。当时我对两个点非常感兴趣:第一,人们对他消失之后的事没有任何证据,所以展览我是从他的消失写起,因为正是他的消失让我有了自我言说的、虚构的空间;第二,在吉姆·汤普森之屋中有非常多亚洲文化的东西,所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观看东方文化的西方人。某种程度上,我跟吉姆·汤普森的经验是一个镜像。对我而言,这个展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展,因为它不单包含我自己的立场,还包含了我立场的反面,也就是东西文化之间的反复穿插。

重写吉姆·汤普森的消失 © 艺术家
吉姆·汤普森早期在美国学习建筑,所以我把自己对法国六七十年代建筑的研究放在了吉姆·汤普森建筑事务所的这个虚拟框架中。对法国建筑的研究也是我的一个长期项目,它的缘起是一次我和法国朋友去郊区的跳蚤市场,他说他觉得那边的建筑特别丑、特别奇怪。但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反而没有觉得这些建筑奇怪。后来我开始思考这件事,考察了这个郊区的历史——原来,整个区域一直是处在法国左派的政党下,是在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或左派的意识形态下去建造的,它的名字有一种大团结的意思。
由于我在中国的政治集体意识下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并不会觉得这些相似的建筑奇怪。之后我又发现,这些建筑的建造背景是在六七十年代,法国经济恢复后引入了大量移民,当时的社会气氛特别乌托邦化,政府、知识分子、建筑师都想要建构一个中产阶级和外来移民都特别融合的环境,所以造了这种集体式建筑以提供一种社会模式。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白人中产阶级搬离了集体式的建筑,这些地方也基本上变成了所谓的暴力街区。
我感兴趣的点是,尽管所有人都希望建造一个好的东西,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个过程跟我在中国的生活经验相似,因为我的父亲在政府工作,我会通过他了解到一些政府或他作为执法者的立场。这其中的复杂性和现实的忧郁感是我特别熟悉的。然而,就像前面所讲的,我并不是站在一个对异域文化带有猎奇眼光的角度,而是通过我深层次的、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去触碰这些主题。

远东信使 © 艺术家
蔡星洋
你是如何去构建整个展览语境的?
蒲英玮
虚构写作的好处就在于,当你制造一个东西时,你可以通过写作把它加入到历史的语境中。在产生了关于“吉姆·汤姆森”这个念头后,我画了一个纪念邮票,上面有美国的迷彩军事背景,也有似乎是东南亚丛林的潮湿的图样,然后右下角有个小小的美国国旗,它是个虚构的建筑邮票,可能会让大家认为是真正来自于吉姆·汤姆森的个人收藏。整个展览是基于收藏的概念,收藏行为就像是一个幻肢,它早已不存在了,但又似乎在某个地方召唤着。

被收藏家置于水中的石质摆件 © 艺术家
我父亲收藏各种石头和字画,其实他收藏石头的行为跟做艺术是特别相似的。他经常会拿起一块石头,问这个像不像一只鸟,像不像一个菩萨,或者一个佛。他们那代人会把自己主观的世界完全投射在一个物体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也是我在构建我的绘画和装置时的逻辑思考。另外有趣的一点是,我父亲的收藏中既有中国传统字画,也有欧洲古典油画,角落里还有一堆毛主席头像。他在体制内生活,但他也参加过1989年的学潮运动,他们那一代的人并不能真正选择自己的命运,他的收藏也侧面展示了他内心世界的这些冲突。
我觉得他们那代人的特性和力量就在于,他们能把所有的冲突内化吸收或压制,同时过着看似非常日常的生活。可能我的另一个责任就是替他们挖掘他们身上有的不同可能性,所以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我和我父亲的交流,例如那些寄给我家人的明信片。

游牧小说 © 艺术家
蔡星洋
我觉得你作品当中的策略和方法很有意思。
蒲英玮
其实我觉得艺术家的策略是非常本质的,它并不是贬义的。一个艺术家如何分析艺术现状、社会现状和自己的状态,都是有非常多的思考在里面的。今天任何东西都能被媒体迅速地景观化,我要从一开始就拓展开,这也是为什么前几个展览中的风格跳跃性比较大,哪怕别人理解不了。我相信通过三到五年的持续工作,人们会把所有的东西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核心和逻辑,那个时候作品才会真正产生效果。这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说是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