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文:戴西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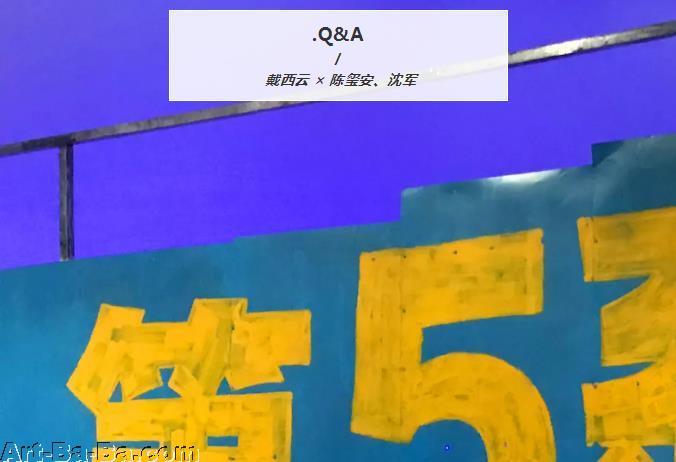
“ 特 区 ” 秩 序 化 的 加 速 美 学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一
2006年4月8日至5月16日
北京长征空间
艺术家:郭凤怡、胡项城、卢杰、邱志杰、王功新、徐震、杨少斌、展望、赵刚
、郑国谷、周啸虎、某匿名艺术家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二
2008年3月1日至4月4日
北京长征空间
参展艺术家:陈界仁、陈杰、陈秋林、何岸、洪浩、黄宽+魏雪冰、黄奎、胡柳、 Ingeborg Lüscher、蒋志、金锋、Soni Kum 、李川、李勇、Lisa Norton、刘韡、琴嘎、邱志杰、邵一、沈晓闽、沈也、苏中秋、唐茂宏 、汤艺、王易罡、卫秉强、肖雄、徐震、杨光南、余极、杨振中、 张鼎、张辽源、章清、周啸虎、朱昱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
2018年7月21日至8月26日
北京长征空间
艺术家:约翰•杰勒德(John Gerrard)、何锐安、刘窗、陆平原、长征集体、SCV、苏予昕、耳石小组、山寨歌词、吴山专 & 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尔(Inga Svala Thorsdottir & Wu Shanzhuan)、汪建伟、王梓、颜磊、郑源(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策展:长征计划
“违章建筑 ”,是一个隐喻。“违章建筑 ”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常用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中的法则用词,针对的是悖于 “统一整体 ”社会规范的某一个体行为或设计。对 “违章建筑 ”的阐释显然是从文化意义上认识 “现代性 ”这个被强加与亚洲的 “世界性统一整体 ”的概念 – 这种从上往下的运动,带来的不仅是对知性认识系统的颠覆,还有自然观与空间观的错位,扭曲的身体经验。阶级之间的紧张没有消失,而是变异和强化。如果说现代性的民主模式是一个世界普泛化必然过程,该如何面对这一模式不可能有的普适性?“违章 ”事实的表面是建立在个体生存的 “必需伸张 ”,其暗藏河床下的是对总体社会建构理想主义美学的具体反叛和颠覆,在今天,从出生就面对着失败、临时性的 “违章建筑 ”,其悖论也表现在超越物质和建筑概念之外的社会和政治、文化领域。我们都知道,违章建筑无处不在。“违章建筑 ”是文化意义上的泛指,以一个 “错误 ”去颠覆另一个 “错误 ”的荒谬性体现为对秩序的有意识直觉反抗,“违章 ”在这里已经不存在是非判断基础,它实际是一个自我建构的代词。而且是无所不在的非中心化的、可视或不可视的、已知和未知的日常经验,关于差异性的无意义的审美态度。(节选自2006卢杰《违章建筑》)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 ”是延续自2006年及2008年系列展览的最新一期,项目以违章的临时性作为隐喻 ,发展出各种感知当下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现实的视觉工作方法。“违章建筑 ”在这里并不是建筑形式的指称,它泛指各种运用非常规的策略来对应新的社会情况的生命形式。这些自发性的精神建筑也许原本仅仅是应急之用,但在后规划的时代中,非正式和不稳定性反而成为常态。而 “违章建筑 ”系列主张以下具有生产性的观点:应该将违章建筑的非常规状态和永久性建筑的常态关系两者反转看待。这种永久的非正式性其实就镶嵌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和资本的增速当中,“ 特区 ”便是一个典型的非常规试点成为常态的例子。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 ”是 “违章建筑 ”系列的进一步尝试。一系列对改革开放、当代技术及资本速度的思考以视觉展示、读本、表演现场以及视听采样四个独立又互补的文本呈现。
对此,我们特别邀请了艺术写作者戴西云,与 “长征计划 ”研究员陈玺安、“长征计划 ”项目人沈军,就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 ”从2006年至今的研究发展及形态演变,进行了深入的对谈。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展览现场,2018,长征空间,北京
图文资料由长征计划提供
摄影:ARTEXB
戴西云(以下简称“戴”)
陈玺安(以下简称“玺”)
沈军(以下简称“沈”)
戴:
“特区”是“长征计划:违章建筑”项目的第三次展览,是什么促使你们选择延续“违章建筑”这个主题?它与前两次展览有着怎样的联系?
玺:
从2002年开始的“长征计划”有几个不同的线索,除了“违章建筑”以外;主要是2002年在旅行中所进行的“长征计划”,里面一些子项目后来被单独拎出来做,比如“长征计划——延安”(2006-2007),“长征计划——延川剪纸大普查”(2004-2009)……这些项目虽然都是在“长征计划”这个大框架下,但节奏、形式还有体量都有不一样的发展。“违章建筑”在2006和2008年两次的策展则是想要就当代生活空间里面的各种非正式性、非常规性进行实验。在别的领域里面可能会谈论“非正式经济”,一种没有被写在法律里面,不被正式认可,但是它又是一种很普遍的经济形式。这两次展览要求一种转换式的思考,当你把常规跟非常规的主客次序倒过来看时会发现,非常规的事情远比常规的事情还要多。只是我们自己会把它正常化、合理化,所以“违章建筑”作为一个引喻,其实就是在指艺术家怎么去调动这个主客转换的想象。这几次展览中都不乏这种转换很巧妙的作品,尤其是委任作品,杨振中的作品《长征总闸》(180×90×45cm,2008)将长征空间所有的电路系统都接到他的那件作品上,观众如果误触的话整个空间的电闸都会被关掉,你可以看到艺术家是怎么去运用这种杠杆的。另外一种杠杆就是“特区”,在最开始的时候,它的合法性一直在公共领域中被辩论。但这个局部试点中的经济形态最后扩张到了整个中国,所以“违章建筑”是在历史性的去看这个“改革开放”的“建筑”,但这个“建筑”当然不是直接指那个建筑,是指整个基础。

杨振中,《长征总闸》,装置,2008,展于“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二”现场
图片由艺术家和长征计划提供
戴:
展览发生时的社会背景在十年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否谈谈这三次“违章建筑"展在语境上有什么不同及相似之处?
玺:
我觉得其中一个区别可能是“长征计划”在06、08年的时候,相对来讲产量特别高,“违章建筑”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主线,而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线索,这里“实验性”是指它比较多弹性,并没有聚焦在摘出一个叙述或论述。“长征计划”之前还有“装修展”这种玩的比较开的展览,档案是我和沈军一起在整理,在我们俩看来“违章建筑”不算是一个最严谨的,有很多要求的系列,所以在做第三次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压力,况且我们俩第一次做就做的是“三”。
沈:
相对来讲, “长征计划”的主体项目可能有更宏大的体量跟研究视角。而“违章建筑”它能够涵盖的多样性是更宽松自由的,同时它也是从横截面式的观察角度去做展览。所以作为比较年轻的“长征计划”团队,“违章建筑”就变成我们相对容易去切入“长征计划”的整个体系的一个点,去做一次实验,也是一次提出语境的尝试。这次北京的展示结束后,“违章建筑三——特区”项目会与广东时代美术馆合作推出巡展。一方面我们与时代美术馆合作和讨论,基于区域的状况与语境上的差异调整了北京展示的部分参与者及作品,另一方面也发展了北京项目,希望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示中国本土对于科技增速发展的一种反思视角。展览将于9月15日开幕并持续到11月11日。

"装修 – 生产关系"展览现场,北京,2005.12.17 – 2006.2.26
戴:
前两次“违章建筑”在形式和美学上似乎有种违章建筑式的视觉张力,爆破感。本次”特区”展却恰好有种秩序感,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前期调研,以及最后的展示形式。如果我们联系这个现象去看深圳的华强北,当年那个非常“乱”的,聚集着许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作坊的地方,现在已然变成了秩序井然的商场式的东西。这非常符合“违章建筑”的自我生长,自发的东西逐渐被梳理和归类的概念。
沈:
我觉得你的观感很有意思,因为我也听到很多看过前两次展览,再来看18年这次展览的观众反馈,简单来说就是06、08年在视觉上是很有冲击力的,或者是看起来就是违章建筑的形态,但是我们这次是更静更沉下来的,然后更缓慢的进入一个展览的过程。其实我们在策划展览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去塑造展览本身的“违章”形态,但是我觉得得到这个反馈的意义在于引导我们回看这个问题,不同的观者对于“违章建筑”的理解,包括它跟现在语境和艺术生态的直接联系。而且这次展览里的阅读体验比视觉体验要更多一点,我觉得我们有特别尝试去分开这几个层次,就是究竟你从哪个层面去进入展览,可以是视觉展示,你也可以听SCV和长征计划声研单位帮我们特制的歌单,然后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表演讲座的现场,同时你还可以深入到读本的研究线索。我们并没有预设观众的体验,而是自然的把这几个层面分开。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一”现场
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二”现场
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玺:
作为“长征计划”的新团队,我们也有特别去思考长征的思想和方法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是寻找当下国际紧急议题在本土的论述切口。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少有人谈论加速主义,我和刘窗的论文(《特区:一个修正主义加速主义的案例》,2018)试图打开这一个缺口: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中国当下的,往往是一种冲动而不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对未来的一种想象和憧憬,或者说是一种对于技术的过度认同,看作是一种加速主义的想象。我们想要去谈这种中国对于科技的幻想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同时,想要把这一个论述与国际上对于加速主义的广泛讨论甚至批判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展览现场,2018,长征空间,北京
图文资料由长征计划提供
摄影:ARTEXB
戴:
说到文本,你能展开谈一谈这次展览的核心作品,也是你跟艺术家刘窗的一次合作,以及那篇文本(《特区:一个修正主义加速主义的案例》)的创作,里面提到修正主义不是苏联的那个修正主义,你是怎么把这个修正主义放到加速主义里面来讨论的?
玺:
其实修正主义、加速主义这两个字被放在一起是有点文字游戏的,它们肯定是共产主义的传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次是马克·费舍尔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试着把它背后的概念政治化,虽然它看起来是非政治化的。
戴:
什么看起来是非政治化的?
玺:
比如说在马克·费舍尔的概念里,今天的所有你看到的事物都是资本主义建构的。它已经自然化了,所有事情都是资本主义,以至于你不会觉得资本主义存在于你的生活中。所以他谈什么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你的现实,你的现实是有一个脉络的。所以其实“修正主义加速主义”想要认真谈的是到底“加速主义”有没有一个历史?因为加速主义很多的论述其实是对于未来的投射。它其实有一些不太愿意谈论的东西,譬如说高科技的废弃物或者高科技将自己装点成高科技的这段历史。另外,加速主义这个论述必须透过很多层次的简化,才可以达到你所看起来的论述上的赛博朋克美感。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切入点是因为,很多加速主义者或是说很多书写到思辨理论的学者会将邓小平视为加速主义者。他们往往基于邓小平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技术冲动,以及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很自然的视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我试着不以赞叹其加速度的方式来理解这两个词汇的关联性。而是思考改革开放生产出来的技术观点是什么。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 视觉读本(电子版截图)
图文资料由长征计划提供
戴:
把这来两个词编制在一块,想给它一个所谓比较逻辑性的或者历史性的角度?
玺:
对。当你认真的把邓小平视为一个加速主义者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很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会如此认同于科技进步,而且只是一种类型的科技,譬如说AI、大数据等等,就是全世界都在讲的这种,你可以说今天的技术论述是没有想象力的。
戴:
我们可以说这个技术本身被资本垄断了?
玺:
大家不会去谈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这个技术的论述,怎样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去做。即便在西方,加速主义通常都有一种特定的美学,反正我们自己在调研的时候也会留意,但并没有特别追溯这个东西。我们也会收到反馈是说,改革开放不是加速,是减速。这其实很好理解,你只要用西方左派的论述来看,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你买一台汽车,它可以让你的移动时间更短是吧?但是你如果把它保养、停车等成本全部算进去,你会发现其实是比你没有车的移动还要慢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加速主义它其实是通过很多的排除法达到的加速,你完全也可以这样去批评改革开放,或者是新自由主义。其实我不觉得我和刘窗很认同加速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也没有特别地要把自己摆在一个认同的位置或某一个位置。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展览现场,2018,长征空间,北京
图文资料由长征计划提供
摄影:ARTEXB
戴:
所以加速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这个展览的立足点。
玺:
对,不会让作品全部都在回应加速主义。
戴:
感觉加速主义在西方基本上都是艺术圈在聊,也许就像你说的它有很多可以猜想和幻想的空间,它没有马克思主义那种传统理论的严谨的逻辑性。回到这次展览,能具体谈一谈加速主义和你文章中的“改革开放”的加速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
玺:
这次展览里只有刘窗直接提这件事情了。我自己从策展人的工作角度的理解是,这两者基本上是共享一个对于技术的意识形态,就是他们理解技术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或者说我们在理解技术的时候有一个参数,就是技术跟人的关系,技术、人、自然三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基本上加速主义跟“改革开放”对于人跟自然关系是一样的,我是我自己的资源,自然就是可以被我用技术去掠夺的自然。“改革开放”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引进外资,那引进外资怎么去让利?它让的利就是用很便宜的自然资源和很便宜的人工去交换资本和技术,这个交换里的设定是直接让你的劳动力跟自然资源变成被剥削的对象,然后你再最大化那个剥削。那加速主义对于人跟自然的想象,简单说就是普罗米修斯主义,没有什么伦理观可以限制人去获取最大的技术,以至于技术让人跟自然的关系失衡,于是你可以做人造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它在为技术开绿灯。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展览现场,2018,长征空间,北京
图文资料由长征计划提供
摄影:ARTEXB
戴:
除了加速主义,在你和刘窗的文章中还回应了另外一个点——“山寨”,你在这里的回应与陆明龙在《中华未来主义》中的回应有什么不同?
玺:
我觉得陆明龙的工作更多的是在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盛象锁定在中国,或者说“山寨”这两个字本身就是被第三世界化了。有个词叫“counter engineering”就是反向的工程,这是个冷战时期就很普遍的词,比如我看到一个飞弹,然后我把飞弹搬回来去研究它到底是怎么做的,然后造出一个飞弹,这个是冷战的产物,所以你其实很难说“山寨”就是很中国,“山寨”这个词是2004年以后才出来的,当英文都用“shanzhai”这个字来说这个东西时,这种抄袭就变成是中国特有的。所以《中华未来主义》在复制这个东西,讨论这种离散身份,他会假想自己的文化去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提供一个语境。但是“特区”这次展览比较像是一种对文化身份的溶解和分裂的工作。譬如说作品《山寨歌词》,其实是想要内爆一个逻辑,针对整个全球的服装产业,只是它用的方式是从这种最低端的产品,也就是山寨衣入手。包括Ackbar Abbas在2002年写的那篇《论盗版》, Ackbar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收集假表。对Ackbar来说,山寨逻辑就是全球化的这个商品速度,山寨只是这个逻辑里最快的一个反应,只是它没有一个合法性而已,但它是一个全球化的逻辑,它是全球化的一个影子经济。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 视觉读本(电子版截图)
图文资料由长征计划提供

“长征计划:违章建筑三——特区” 视觉读本(电子版截图)
图文资料由长征计划提供
戴:
有些受到加速主义影响的作品,包括这次展览中的耳石小组,如果我们暂撇开加速主义不谈,作品里有一种对未来的想象。这些作品,或者说这些实践,经常预设一个未来以及未来中的生物或者人,再返回到现在的现实中去探讨。对未来的想象有很多种,加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比如当年的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包括现在的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都是不同的对未来的想象,你对它们有什么看法?
玺:
其实这一次展览大家都没有刻意的去刻画一个很具体的未来,也就是说他们不做这种科幻小说习惯做的工作,把未来想象出来给你看,当然最后未来也不会变成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大部分艺术家是在做对于未来的一个提醒,譬如这次John Gerrad的作品他就是在告诉你,即便档案这件事特别重要,但也一定要有电力才会有data,data才会存在,data的运转不是靠时间、空间,算力好需要的是电。所以John Gerrad的作品一直在裸露电力的建构,比如说这一次就是比特币的建构。何锐安强调的是中国今天在做的“一带一路”会不会在重复过去,金融危机是亚洲经济奇迹的老路,对“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的想象和视觉语言的提取,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在什么样的方面被今天的一带一路重复了。邓小平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真的很有想象力,他可以想象出各种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而且是在七零年代,锐安其实是在讨论“一带一路”的想象力够不够,如果我们不程式化的去理解想象力这个词,他还谈金融危机跟金融奇迹背后是为什么,有哪些想象。所以大家是在通过各种方式对未来做出一些提示,耳石小组这次的作品《诅咒》其实在谈的是有没有一种慢的科技的想象,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暂时性?譬如像小米和其他科技品牌都会做这种科技想象,简单一点的像乌托邦啊,或者是一种AI形象,基本上是那几种套路,但是要怎样用一种很慢的方式去描绘未来,而且是几乎冥想式的,就比较少人在做。所以都是在尝试怎样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做,譬如谈“改革开放”,其实是在谈未来。

耳石小组,《诅咒》,2011,高清录像,彩色,立体声,36’51"
图片由长征计划提供
摄影:ARTEXB
图片资料由长征计划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