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y官方 文:袁佳维
1957年出生的胡介鸣与1990年出生的胡为一是中国数字媒体和影像装置领域的先锋人物。他们作为各自同时期艺术家中的代表,对观念创作中的时间基础与叙事线索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对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父子向来独立工作,又不时介入或参与到对方的作品中。父亲与儿子的身份在缠绕历史、记忆、城市、身体等主题里相互印证,诉说着个人与集体、存在与事件之间的种种联系。近期他们在香格纳画廊新加坡空间共同完成了首次双个展“想象就是现实”。值此父亲节之际,由 Artsy 发起的“胡式”父子谈将从两位艺术家各自在“前艺术家”阶段的经历开始,逐渐深入到他们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体察与感知。

胡介鸣,《儿子》,2008年,黑白摄影。图片致谢艺术家和香格纳画廊
Artsy:让我们从一些生活场景切入,不妨先谈谈老胡和小胡都是怎么会成为艺术家的呢?我很好奇老胡从艺的道路是如何开启的?又是怎么慢慢影响小胡的?
胡介鸣(以下简称“老胡”):这个说起来要准备好纸巾的。我是从文革当中过来的,当时没有艺术家这个词。我在中学阶段参与一些宣传工作,画工农兵之类高大全形象的宣传画。当时没有正规的学习基础,都是照样子临摹。这应该是我最早和美术发生的关联。中学毕业的时候是1975年,没有考大学,但上山下乡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当时最好的选择是参军,第二选择是当工人,第三是去农场。我还不错,我是第二选择,成为了工人,被分配到上海的一个建筑单位做木工。做手艺是我从小喜欢的,木工也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动手的能力倒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养成了,没事的时候就画画。过了两年恢复高考了,我开始报名,打听到要画石膏像,就去文化馆里学习,就慢慢走上了这条路。在中学时理科成绩比较好,如果没有文革,我可能成为科学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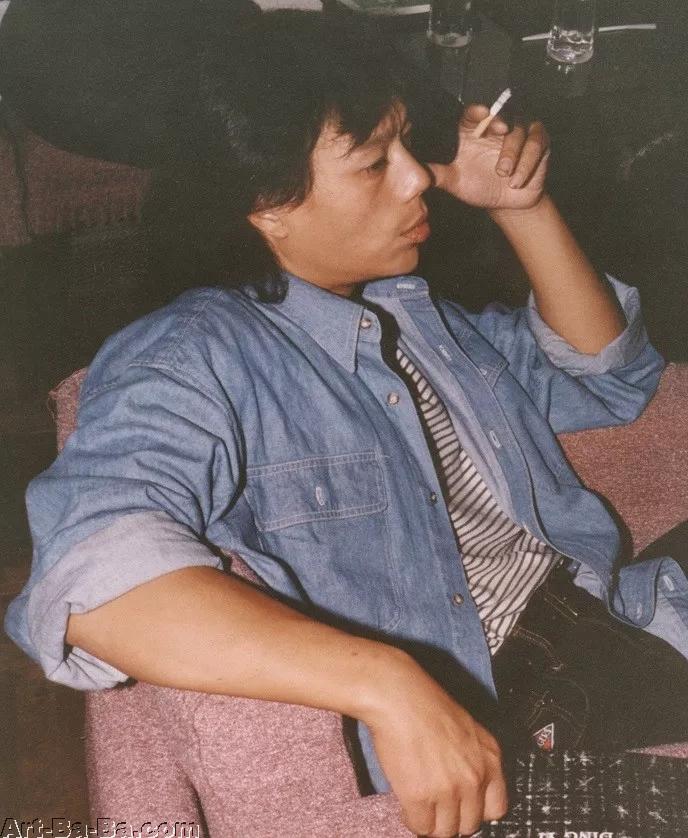
胡介鸣,1995年
Artsy:那么进入职业艺术家的状态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九十年代初,也就是胡为一出生的时候,你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开始做影像了吗?
老胡:我做影像是在九十年代。张培力更早,但当时我们还不认识。我在90年代初看到 Bill Viola 和 Gary Hill 的信息才知道艺术原来可以这样做,然后慢慢自己摸索技术。胡为一是在我的工作室里长大的,从小接触各种材料。

胡为一和他的第一件艺术作品
胡为一(以下简称“小胡”):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工作室里有各种各样的纸和笔,甚至可以直接在墙上画画。但我爸倒是没有送我去上美术班,而是去学习航模,参加了许多比赛还得过名次。总之小时候我有多动症,但还是尽我所能地上了一些重点学校,当过宣传委员、画黑板报,也跟着我爸到处看展览、吃开幕饭。后来意识到大学也要考不上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了前途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学画了,而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学画就是要搞艺术,其实就当成是一张考试通行证。进入中国美术学院之后,本科先学公共艺术,研究生再学新媒体,现在比起绘画我更喜欢具有手工感和体积感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是基本在做装置民工了。

“想象就是现实”展览现场,2018年,香格纳画廊,新加坡。图片致谢香格纳画廊
Artsy:今年早些时候在香格纳新加坡的双个展“想象就是现实”是你们的首次合作吗?这个展览的缘起似乎是一个东南亚驻留项目?在此之前有没有过在创作轨迹上的交汇?
小胡:开玩笑的说就是接了一个画廊的活儿出国打工,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出机会,也十分感谢画廊能给予艺术家创作上的各方面支持。其实作为艺术家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驻地式创作的,换句话说是一种被动的创作方式。因为驻地本身会给予艺术家一个不可回避的在地性命题,例如这次的项目就是要和东南亚有关,而如何把被动授予的命题转化成主动出击就显得格外具有挑战性了。我特别不喜欢有些艺术家在驻地期间还在重复他原来的创作,说难听点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做,或者说放一点肤浅的当地特色进去。比如我的《低级景观》系列作品,它的主要概念是在皮箱中搭建一个电影的拍摄现场。如果我到东南亚还是做那么一个皮箱,而只是把里面的东西换成在东南亚收集的物品,那结果就一定很无聊并毫无意义。我还是倾向于到了现场随后直接抓取灵感,虽然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会更加具有趣味性。在东南亚的旅行过程中我和父亲基本上是分开行动,因为不想让这件事变成非常有计划性的工作。在创作的过程中把缅甸、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都跑过了。

胡为一,《低级景观6》,2017年,视频装置。“身体·媒体II”展览现场,2017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图片致谢艺术家
老胡: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做作品的机会,我经过规划之后重新拿起了一些拍摄计划。因为前期拍摄耗费太大,我差不多有十多年没有拍摄了。这些年来我做后期比较多,后期是靠人力和技术,这一块我自己能掌握,在创作成本上就可以控制。在东南亚我拍了近两个月。拍摄方案基本是在旅行过程中产生的,比如《乌节路》这件作品的想法是去了之后形成的。我在日常中行走,针对乌节路这个场景进行时间性的记录,发现了人流与车流之间的相对秩序,然后用决定性的瞬间把它凝固下来。




胡介鸣,《乌节路》,2018年,摄影。图片致谢艺术家和香格纳画廊
Artsy:老胡其实抓取的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但小胡在这批作品里是找了演员?
老胡:他是观念先行的做法,我这次没有这样做。
小胡:因为到后期时间紧迫,我只能把很多细节想得很完整、很精确。在创作《疑影》和《姿态研究》的过程里,我和当地人配合得很好,用他们的身体说话,效率非常高。起先我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但逐渐变得越来越敏感。《除了雪,这里拥有一切》其实来自我在航空杂志上看到的一句话,这是一篇推销东南亚旅游的广告标题,我觉得它特别能勾起人们对于东南亚浪漫且空洞的想象,于是我就开始在东南亚拍摄的纪念碑照片上制造虚构的雪景,雪是东南亚人的想象产物,而纪念碑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景观,两种想象在画面中的交汇构成了新的现实风景。至于展览标题“想象就是现实”,你可以反过来读成“现实就是想象”,这是我和我爸的默契。之前我们有默契的情况多半是一起参加群展或对一个策展理念作出的回应,很多策展人觉得把我们放在一起是一种两代人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下。但其实这条轨迹到底在不在,我也不敢确定。只是觉得如果光靠做一个展览就能去捕捉、印证这种轨迹的存在是不充分的。有时候作品就是独立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在语言和表达上重合的地方,但是我们不会去用作品特意强调或者营造这种轨迹。



胡为一,《姿态研究2》,2018年,摄影。图片致谢艺术家和香格纳画廊




胡为一,《除了雪,这里拥有一切》,2018年,摄影。图片致谢艺术家和香格纳画廊
Artsy:2016年底在瑞士苏黎世Helmhaus美术馆的展览“山外有山”对你们来说就是这种情况?
小胡:没错,那次策展人直接选了我爸过去的几件作品,而我创作了几件新作品来回应他。其中我的《窥视》是一个搅拌装置,搅拌杆上的摄像头捕捉着被随机打散的网络照片,直到最终其被搅拌成抽象的粉末。但我爸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他主要是对现成照片进行篡改,直接在档案的概念上做文章。我可能还没到这个年龄,没有这样的底气去碰触这个语境。另一件《复眼》是把证件照中每个人的眼睛看成是历史影像里的象素点,这是我对历史的直觉,不同个体被集体意志操纵而使得对历史的诉说变得不可描述,这些作品都不是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与档案本身。

胡为一,《窥视》,2016年,视频装置。“山外有山”展览现场,2016年,Helmhaus美术馆,苏黎世。图片致谢艺术家
老胡:我主要展示了《残影》和《共时》。《残影》就是胡为一说的“篡改”,我运用一些后期技术改动家庭照片等历史图像,将它们放在陈旧的档案柜中,这些图像看似被激活了。这个系列被展示了好多次,包括我在香格纳北京的个展“共时”和当年的釜山双年展。

“共时”展览现场,2016年,香格纳画廊,北京。图片致谢香格纳画廊

胡介鸣,《残影2016-No.16》,2016年,视频装置。图片致谢艺术家和香格纳画廊
Artsy:让我们回到媒介问题上,影像装置(或称视频装置、录像装置)可以说是你们的主要媒介。最近在上海保利时光里的个人项目“超图像”中呈现的《太极》可以说是老胡的代表作,庞大的机械骨骼唤起了某种深刻的集体潜意识,与夹缝中的面部表情投影形成叙事。这个媒介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有认知度和接受度了?
老胡:影像装置做的人多了就有接受度了吧,这个媒介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给它一个界定,可能是因为时间还没到,一般都会认为张培力在1988年创作的《30×30》是一个开端。我的创作是综合性的,并不只是集中在影像上。大家现在都聊新媒体,不管怎样,艺术家还是要看自己对运用的语言体系是不是熟练。


胡介鸣,《太极》,2014年,视频装置。图片致谢艺术家与香格纳画廊
小胡:我其实对时髦的新科技没有太大的感觉,我对技术的了解都是被迫的,不像有些人是技术控。可能我天生就质疑这个东西吧,在利用它的同时又始终伴随着警惕。因为它们都太嘈杂了,会分散艺术家的注意力。如果一个所谓的新的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艺术家表达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工具本身是有能量的。我需要的新技术是一个能创造出非常好的环境的“孵化器”,然后把我要表达的东西一点点的烘托出来。因为有时纯艺术创作是一个非常脆弱、腼腆且柔软的过程,一不当心就会流产的,而科技又常常带有棱角和噪音,两者的结合不像一般人想象的这么简单,这是新媒体所要面对的本质难题。
Artsy:主题呢?我观察到你们的创作内容牵扯到一些相同的关键词,比如时间与叙事。老胡这边更偏重记忆,甚至是宏观历史性,小胡可能关注到的是更个人化的表述。
小胡:我也会关注到大范围的混合时间。
老胡: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对时间感到焦虑,不知不觉年份变成我很多作品中的一个元素。数字所代表的信息对我而言特别可信,一个人的出生年份和死亡年份就已经确定了他的生命在历史中的时空位置,《残影》涉及的年份就是我的个人生命时空,以我的出生时间作为开端,现在仍然在推进这个系列。
小胡:我没有那么焦虑,但是我对这个时代的效率感到震惊。被消耗、被消费的感觉一直都在,仿佛缺席就是犯罪。可能是为了缓解这种快速前进的时间压力,我喜欢看上去更破旧而不时髦的东西。我认为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而他们正在被这个时代挤压到了角落,就算如此也不能代表他们就是过时和淘汰的代名词,有时只是我们自己的无能,没有办法去解码这些信息从而和它们对话。

胡为一,《日出计划》,2016年,摄影(艺术微喷)。“例行公事”展览现场,2016年,东画廊,上海。图片致谢艺术家与东画廊
Artsy:小胡太谦虚了,2016年在上海东画廊的展览“例行公事”就有成功破译至少一部分吧!特别是《日出计划》?
小胡:《日出计划》那是当年我参加格兰菲迪艺术家驻村计划时候完成的作品,和在苏格兰的生活状态有关,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和这些自然元素对话。平时在城市当中连地平线都看不到又怎么能想到跟土地对话呢?我在那里推开窗户就是地平线,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和落下,我觉得自己也可以介入到这个时空游戏里去。时间出现在我的头顶而不是显示在手机屏幕上,所以我试着模仿自然也给自己制定一个规则并且重复下去,我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拍摄每天的日出画面,随着日夜时长的变化,我记录下了太阳不停往下掉的过程,拍的是日出,最后它却变成了日落。人为模拟自然制定的规则和真正的自然规律在此相互错位,这样的反差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Artsy:小胡的《日出计划》把客观的物理时间变成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老胡的《残影》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反过来扩大为集体时间甚至是一个时代。更有意思的是,老胡曾经在《儿子》这件作品里让小胡担任自己的模特?背后的创作初衷是什么?父亲和儿子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情绪?
老胡:《儿子》是在2008年拍摄的,当时胡为一还在读高二。我让他站在我曾经迷恋的楼顶眺望的位置上,俯身看周围的街道和来往的车辆并摁下了快门。而我在他背后的凝视又是一种历史绵延的感觉。



胡介鸣,《儿子》,2008年,黑白摄影。图片致谢艺术家和香格纳画廊
Artsy:这是唯一一次小胡给老胡做模特吗?
老胡:2004年创作的一部片子《水中物》里有他,他在浴缸里面游泳。2000年的“美多撒”系列中也有他,当时他还穿着校服呢。
Artsy:这么性感?
小胡:嗯,裸泳,为艺术献身。







胡介鸣,《水中物》,2004年,PAL制式单频录像(有声、彩色)。图片致谢艺术家
Artsy:这里又有一个关联,刚刚老胡说《儿子》表现的是个体成长与城市变迁的对照,儿子是一个活的参照物。小胡的作品《植物简史》中也存在这种对照,但作为参照物的是一根树干而不是另一个“小胡”。所以小胡会不会认为自己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创作有所继承?
小胡:这件作品也和在格兰菲迪做的驻留有关,我用当地的一棵树去叙述当地的历史。树本身能作为时间的物证因为其自身不断生长的线性结构,特别像是在剪辑过程中的时间轨道。安在轨道上的摄像头在手轮的控制下将树枝的表皮记忆与周围景观的片段剪辑叠加,它们之间会有一种张力。你平时不会凑那么近去看一棵树,有些非常小的陌生细节和你生活城市的神秘边界似乎又联系在一块儿了。在这点上,我和我爸就撞上了,他利用我去贴近这个城市,我又去贴近了其中的一棵树,而这棵树中又有另一个城市。

胡为一,《植物简史》,2016年,视频装置。“上海星空II”展览现场,2017年,余德耀美术馆,上海。图片致谢艺术家
Artsy:小胡会反感媒体强行把你和老胡或者你们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吗?
小胡:我觉得没问题,作品和人就是要不断被他人提及才能生产新的意义。
Artsy: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如果把父亲理解成父辈,把儿子理解成整个年轻一代,比如有学者想通过你们两个之间的线索去反映大环境的变化,像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线索,你们会如何回应?
老胡:当然我们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这肯定会反映在各自的作品里。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比性,但想想也有意思,我们在做同样一件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完全是遗传、基因、血缘、亲情。设想如果不是父子,我们也可能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Artsy:作为父亲的老胡看到自己儿子现在的工作状态还算满意吗?作为儿子的小胡会有压力吗?
老胡:是值得庆幸的。他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还做得不错。我们都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
小胡:我的压力大概还是同龄人带来的,做职业艺术家竞争多大呀!
Artsy:最后的最后,小胡有什么想对老胡说的吗?
小胡:有点艺术人文频道的意思?我和我爸都非常信任对方。在艺术上面,我爸属于那种少数在他这个年纪没有吃老本,还在继续向未知推进的。我觉得与其说我们作品上的不谋而合,不如说是状态上的不谋而合。我们站在同一个前线,并且还没有被市场规训为艺术品生产型选手,比如有了一个受到认可的创作模板就不停复制。我们都把工作室当成是自己的阵地,每一次创作都会有新的战况。我在我这个年龄应该是这样,但是我爸在他这个年龄还是这样的状态是非常难得的。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对父子的特点吧!
Artsy:老胡,小胡在夸你!
老胡: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