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基宇:王道之外,没有任何道——《乐本篇》的意图与意外
http://site.douban.com/widget/notes/852552/note/206487475/
王基宇:王道之外,没有任何道——《乐本篇》的意图与意外
2012-03-23 20:20:30
王道之外,没有任何道
——《乐本篇》的意图与意外
2012-03-23 08:49 (分类:默认分类)
当谈到城邦护卫者的教育时,格劳孔装内行,苏格拉底也为后面的四德结构做铺垫,音乐的作用却被作为一个比喻的“和谐”一笔带过;苏格拉底只说智慧、节制、勇敢要如音乐一样和谐,最后可达正义。
当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谈论着调式、乐器、歌词、节奏的时候,他们是心虚的,他们根本不理解音乐的本质,他们只是使用话语,因为人灵魂的本质早已预设——理智、血气、欲望,即使作为一种教育技术,音乐也与三者隔着一层,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分析出可以用理念保存住的音乐逻各斯,只能比喻。
之后马上四德也遇到了问题,勇敢是残忍与懦弱的折中,节制是奢侈与吝啬的折中,正义是得到全部与失去所有的折中,最后智慧却并不是任何事物的折中。对血气和欲望的节制都依靠理智,但理智本身又用什么节制?最终结果不是正义最高,而是智慧最高,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来折中智慧。
智慧的实在——哲人——把自己放在最高点,统治着城邦的美德——勇敢、节制、正义,折中着它们,折中着他们。但是哲人毕竟与智慧的理念形式还是不同,哲人仍然有身体,有身体就有所得、有所失,就面临正义的折中;哲人的身体拥有的太多,一般的太多可以节制,以理智节制,但是没有人比哲人更理智,你怎么节制哲人?
哲人唯有一死,失去身体,折中其于城邦中最高之所得——失去全部所得、失去全部所失,到冥府去当哲人王,也就让城邦平等、正义。
孔子在《中庸》里一遍遍地悲鸣,欲哭无泪,其他的”过”与“不及“似乎都好说,”知(智)”的”过”与“不及“却是最可怕的——“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这怎么可能呢?中庸怎么可能呢?正义可以折中而出(可均也),节制可以折中而出(可辞也),勇敢可以折中而出(可蹈也),折中者怎么可能折中自己而出(不可能也)?
这是美德的死胡同,所有的美德都需要被一个主体设计控制,而最后这个主体必将无处藏身,在通天塔的顶端等待自己随时可能的失控,等待道德通天塔再一次的倒下。
于是苏格拉底走向了冥府,以自己的牺牲换来“哲人(智慧-最高折中者)-幽灵(无身体-无所得、无所失-逻各斯-回忆)-立法(正义-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城邦-幸福)”的三位一体;也是保罗之后基督教的形态,“象征主义者”、耶稣、尔撒、“我是真理”失去了他的身体,在道说与回忆中维持住了那个最高折中者、善的赐予者,正义的逻各斯也就可能被建筑在地上之城了。
但正义又是什么呢?对于地上之城,正义仍然是”助友害敌“,只有对无所得无所失的无身之人(苏格拉底),正义才是”助友不害敌“。
被害者,就是正义理想国的“它者”。外邦人。异教徒。
能带来无外的,能终结他者悲惨命运的,只有弥赛亚,只有无身体无所得无所失的天国降临,只有按需分配无所得无所失的共产主义社会。
或者天子之眼,看向无外天下的眼光。
“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 秋,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
美德的死胡同,必须有路走出,孔子走出了“理念”的封闭性,走向了“意外”,走向了苏格拉底的敌手,立法诗人“模仿之模仿”最终本源的理念空无之中,从理念的“是”走向“谓之”,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模仿”二元走向心性秘密的内部,走向还原重现而“谓之”,走入了“乐”。
“乐”是等级,“乐”是最好的,“乐”是权力意志。
庄子害怕这无端而出的“有”,害怕“无”被吃掉,于是在“渔父”篇中,隐藏于“意外”中的智者顺水而来:
“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官治其职,人忧 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属,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 之忧也;廷无忠臣,国家昏乱,工技不巧,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礼乐不节,财用穷匮,人伦不饬,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
好个”天子之忧“、”诸侯之忧“、”大夫之忧“、”庶人之忧“。齐物而观之,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品质的不同,君主与草民平等,都统一于一个”忧“字主权之下,犹似霍布斯所谓”对暴死的恐惧“;但这不忧国忧民,只忧自己本位分工的理智,却仍然是圣人建构起来的,人人畏惧圣人言说的道理,虽然平等,但”有道者“圣人却高居之上。有道者必不畏道,圣人必须退出,隐于山水之间,天下才能”忧而治“。
尼采于《敌基督》中怒斥作为奴隶宗教的基督教,消灭了所有主人的身体,只留下唯一的基督徒——没有身体的耶稣本人——在地上众人的回忆中。
忧而治,同样有外邦人,那就是乐者,就是主人,他们会被忧者的怨恨杀死。我们都忧,凭什么你乐?正义就是助友害敌!
天下之外,乐者可存;天下无外。
公孙尼子传孔子之道,作乐官,又作《乐记》,由技进道;刘向删《乐记》二十三篇为十一篇,取道去器。开篇第一,谓之《乐本》,《乐本》何处结束?曰“王道备矣”。
道者,以本达末也,《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既云《乐本》,所生应为“乐道”,何以“王道”作结?王道者,治天下也,天下无外,无外方为大道,“真理是普遍的”,故乐道非道,剑道非道,物理心理,皆非真理。天下无外,而天下之本何也?必曰《说剑篇》中庄子以斗鸡解蔽,斗鸡而庶人,庶人而诸侯,诸侯而天子,天子之剑出,王道备矣。天下之本,存乎斗鸡之中,形于人心之内。
自尧舜始,人心道心,允执厥中。道心则微,人心则危;大道之微,存乎斗鸡之中,人心之危,形于天下之内。欲察道心之微,必格物而致知,欲防人心之危,必反躬而求诸己。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乐而安,安而可使政和,政和而可使天下治。本立而道生,知人心感于物而乐本出,天下治道,此为一也。
知乐者,必能乐之,反求诸己而所能知之也;乐之者,未必能知乐,反求诸己,必先乐于道,不乐于道则无所知之亦无所求之也。
“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乐者从来是少数,伴随着乐的永远是人的不平等;乐的权利性自命出,是心性自然,是人间的自然等级。知乐的君子就可以按此自然等级立法,建立人间秩序——有等级的王制。如果庶民承认自己高于禽兽,那也就必须承认君子高于自己,因为这个高于的理由是相同的。
《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跟师襄学弹琴,反复琢磨,而以闭眼之看见文王,后知所弹即为《文王操》。庶人知音,君子知乐,孔子鼓琴而见文王,此人心之别,道心使之然也。
理想国当然是最好的(哲人自己论证出的),但不是无外的,无外的大同世界,并非需要平等,需要的是最高折中者以乐折中自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乐并非理智、血气、欲望,并非一种力量,而是一种看见,一种置入,一种意志,一种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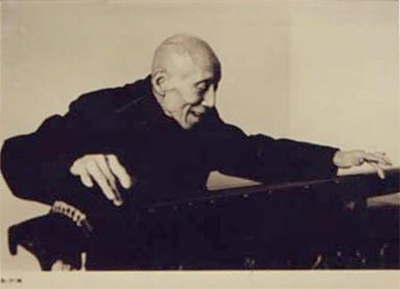
有时看起来像福柯的张龙翔

有时看起来像曹操的张祥龙
王基宇:王道之外,没有任何道——《乐本篇》的意图与意外
2012-03-23 20:20:30
王道之外,没有任何道
——《乐本篇》的意图与意外
2012-03-23 08:49 (分类:默认分类)
当谈到城邦护卫者的教育时,格劳孔装内行,苏格拉底也为后面的四德结构做铺垫,音乐的作用却被作为一个比喻的“和谐”一笔带过;苏格拉底只说智慧、节制、勇敢要如音乐一样和谐,最后可达正义。
当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谈论着调式、乐器、歌词、节奏的时候,他们是心虚的,他们根本不理解音乐的本质,他们只是使用话语,因为人灵魂的本质早已预设——理智、血气、欲望,即使作为一种教育技术,音乐也与三者隔着一层,他们的知识不足以分析出可以用理念保存住的音乐逻各斯,只能比喻。
之后马上四德也遇到了问题,勇敢是残忍与懦弱的折中,节制是奢侈与吝啬的折中,正义是得到全部与失去所有的折中,最后智慧却并不是任何事物的折中。对血气和欲望的节制都依靠理智,但理智本身又用什么节制?最终结果不是正义最高,而是智慧最高,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来折中智慧。
智慧的实在——哲人——把自己放在最高点,统治着城邦的美德——勇敢、节制、正义,折中着它们,折中着他们。但是哲人毕竟与智慧的理念形式还是不同,哲人仍然有身体,有身体就有所得、有所失,就面临正义的折中;哲人的身体拥有的太多,一般的太多可以节制,以理智节制,但是没有人比哲人更理智,你怎么节制哲人?
哲人唯有一死,失去身体,折中其于城邦中最高之所得——失去全部所得、失去全部所失,到冥府去当哲人王,也就让城邦平等、正义。
孔子在《中庸》里一遍遍地悲鸣,欲哭无泪,其他的”过”与“不及“似乎都好说,”知(智)”的”过”与“不及“却是最可怕的——“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这怎么可能呢?中庸怎么可能呢?正义可以折中而出(可均也),节制可以折中而出(可辞也),勇敢可以折中而出(可蹈也),折中者怎么可能折中自己而出(不可能也)?
这是美德的死胡同,所有的美德都需要被一个主体设计控制,而最后这个主体必将无处藏身,在通天塔的顶端等待自己随时可能的失控,等待道德通天塔再一次的倒下。
于是苏格拉底走向了冥府,以自己的牺牲换来“哲人(智慧-最高折中者)-幽灵(无身体-无所得、无所失-逻各斯-回忆)-立法(正义-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城邦-幸福)”的三位一体;也是保罗之后基督教的形态,“象征主义者”、耶稣、尔撒、“我是真理”失去了他的身体,在道说与回忆中维持住了那个最高折中者、善的赐予者,正义的逻各斯也就可能被建筑在地上之城了。
但正义又是什么呢?对于地上之城,正义仍然是”助友害敌“,只有对无所得无所失的无身之人(苏格拉底),正义才是”助友不害敌“。
被害者,就是正义理想国的“它者”。外邦人。异教徒。
能带来无外的,能终结他者悲惨命运的,只有弥赛亚,只有无身体无所得无所失的天国降临,只有按需分配无所得无所失的共产主义社会。
或者天子之眼,看向无外天下的眼光。
“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 秋,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
美德的死胡同,必须有路走出,孔子走出了“理念”的封闭性,走向了“意外”,走向了苏格拉底的敌手,立法诗人“模仿之模仿”最终本源的理念空无之中,从理念的“是”走向“谓之”,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模仿”二元走向心性秘密的内部,走向还原重现而“谓之”,走入了“乐”。
“乐”是等级,“乐”是最好的,“乐”是权力意志。
庄子害怕这无端而出的“有”,害怕“无”被吃掉,于是在“渔父”篇中,隐藏于“意外”中的智者顺水而来:
“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吾请释吾之所有而经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官治其职,人忧 其事,乃无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征赋不属,妻妾不和,长少无序,庶人之忧也;能不胜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 之忧也;廷无忠臣,国家昏乱,工技不巧,贡职不美,春秋后伦,不顺天子,诸侯之忧也;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以伤庶物,诸侯暴乱,擅相攘伐,以残民人,礼乐不节,财用穷匮,人伦不饬,百姓淫乱,天子有司之忧也。“
好个”天子之忧“、”诸侯之忧“、”大夫之忧“、”庶人之忧“。齐物而观之,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品质的不同,君主与草民平等,都统一于一个”忧“字主权之下,犹似霍布斯所谓”对暴死的恐惧“;但这不忧国忧民,只忧自己本位分工的理智,却仍然是圣人建构起来的,人人畏惧圣人言说的道理,虽然平等,但”有道者“圣人却高居之上。有道者必不畏道,圣人必须退出,隐于山水之间,天下才能”忧而治“。
尼采于《敌基督》中怒斥作为奴隶宗教的基督教,消灭了所有主人的身体,只留下唯一的基督徒——没有身体的耶稣本人——在地上众人的回忆中。
忧而治,同样有外邦人,那就是乐者,就是主人,他们会被忧者的怨恨杀死。我们都忧,凭什么你乐?正义就是助友害敌!
天下之外,乐者可存;天下无外。
公孙尼子传孔子之道,作乐官,又作《乐记》,由技进道;刘向删《乐记》二十三篇为十一篇,取道去器。开篇第一,谓之《乐本》,《乐本》何处结束?曰“王道备矣”。
道者,以本达末也,《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既云《乐本》,所生应为“乐道”,何以“王道”作结?王道者,治天下也,天下无外,无外方为大道,“真理是普遍的”,故乐道非道,剑道非道,物理心理,皆非真理。天下无外,而天下之本何也?必曰《说剑篇》中庄子以斗鸡解蔽,斗鸡而庶人,庶人而诸侯,诸侯而天子,天子之剑出,王道备矣。天下之本,存乎斗鸡之中,形于人心之内。
自尧舜始,人心道心,允执厥中。道心则微,人心则危;大道之微,存乎斗鸡之中,人心之危,形于天下之内。欲察道心之微,必格物而致知,欲防人心之危,必反躬而求诸己。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乐而安,安而可使政和,政和而可使天下治。本立而道生,知人心感于物而乐本出,天下治道,此为一也。
知乐者,必能乐之,反求诸己而所能知之也;乐之者,未必能知乐,反求诸己,必先乐于道,不乐于道则无所知之亦无所求之也。
“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乐者从来是少数,伴随着乐的永远是人的不平等;乐的权利性自命出,是心性自然,是人间的自然等级。知乐的君子就可以按此自然等级立法,建立人间秩序——有等级的王制。如果庶民承认自己高于禽兽,那也就必须承认君子高于自己,因为这个高于的理由是相同的。
《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跟师襄学弹琴,反复琢磨,而以闭眼之看见文王,后知所弹即为《文王操》。庶人知音,君子知乐,孔子鼓琴而见文王,此人心之别,道心使之然也。
理想国当然是最好的(哲人自己论证出的),但不是无外的,无外的大同世界,并非需要平等,需要的是最高折中者以乐折中自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乐并非理智、血气、欲望,并非一种力量,而是一种看见,一种置入,一种意志,一种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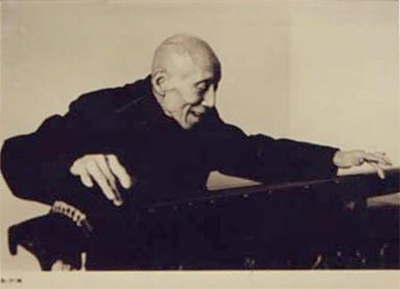
有时看起来像福柯的张龙翔

有时看起来像曹操的张祥龙

可参照阿甘本的那篇艺术/不作为/政治,艺术最终是真正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