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时代美术馆
全球及本土语境下的第三届哈瓦那双年展
文 | 哥拉多‧墨斯凯拉 Gerardo Mosquera
译 | 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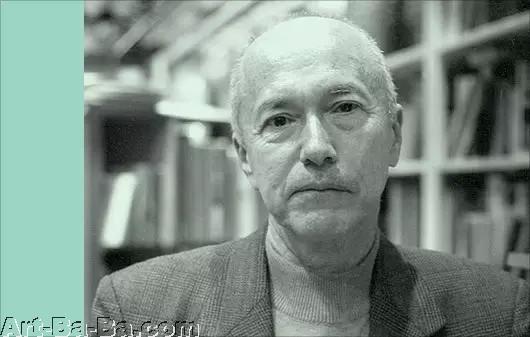
大家对哈瓦那双年展的历史性角色一直有着错误的认知,的确令人震惊。这一盛会最近迎来了它的二十五周年纪念,可以说是驰名国际,且还因其举办地的特殊性,颇具相当的性吸引力。然而除了它的规模巨大之外,通常都被认为是非主流且有些混乱的双年展。大家对它在引领国际艺术圈向今日更宽广领域的转型中所担当的开创性角色知之甚少;是它挣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处的封闭境地,改变了主流的传承。展览研究的发展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将扫除“静的成规”- 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所说,双年展也备受煎熬,可能是由于它的边缘处境,以及它多方面都过于革命的缘故,还有一点就是双年展是在古巴举办的。
鉴于我是双年展的创建人之一,由我来弘扬表彰它的重要性似乎并不合适。我1989年双年展结束之后立即就辞职离开了双年展的组织团队,使得事情更糟,这也是我在这里将要分析的内容。做出这个决定部分是因为我不赞同双年展规划设想的方式,同时我也担心后冷战停滞时期它的未来,还有古巴的官方保守主义,以及针对重要古巴艺术家日渐严格的审查制度。因此,我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甚至有些矛盾的位置上来探讨1989年的双年展。除此之外,我对哈瓦那双年展最近一期的发展方式持有非常批评的态度。由此,评价1989年及其先前的各界双年展就像说:我所参与的前三届双年展是很好的,而我之后的,则流于俗套。这不是事实。然而,退一步想,我在双年展中的参与及双年展的各项事业都使我坚信,你们必须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
双年展的创立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本人提议的,他对双年展并没有一个全面的概念。这是古巴近年聚焦拉美和所谓的第三世界所举办的最具雄心的国际文化事件。古巴本身就以组织国际会议,论坛以及各种会议而闻名世界,在所有领域将此作为一种手段来宣传自己并打造出一个良好的形象。对于古巴政权来说能够表现自我一直是居于首选,但很多举措已经超越了这个国家的规模和经济能力。在举办双年展之前,曾有过文学颁奖会,歌剧节,电影节和音乐节以及各种文化出版物,某些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以开始举办。许多到现今还在举办,拉美电影节一直保持着它在该地区乃至国际上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初期,一些机构例如拉丁美洲之家(Casa de las Américas)和古巴艺术和电影业研究院(ICAIC)对拉美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在创办双年展之前,古巴还未举办过视觉艺术方面的大型国际活动,只是有一些拉丁美洲印刷和摄影比赛,以及多年来由拉丁美洲之家一直组织的展览活动。
1982年林飞龙(Wifredo Lam)之死引发了双年展的创立。作为古巴黑人妇女和一个广东移民的儿子,他是一位使用现代主义推动第三世界想象的艺术家。拉姆是激发这次活动的一个完美的种族、文化和艺术的象征。在林飞龙过世之后,古巴政府急切的利用他的名字,并通过一个决定,即在哈瓦那创建维夫里多·拉姆当代艺术中心(Centro de Arte ContemporáneoWifredo Lam),其使命就是研究并推动所谓的第三世界的艺术生产。双年展是该中心的主要工作。1984年第一届双年展,在Beatriz Aulet指导下由文化部视觉艺术局组织,进展的非常迅速,其原因在于当时的林飞龙中心还仅仅只是在法律意义上存在。该双年展由此在威尼斯、圣保罗和悉尼之后成为第四个双年展,也是除上述几大双年展以及卡内基国际(Carnegie International)和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之后第六个定期举办的国际艺术盛会。
这个双年展和其他几个国际文化活动一样,是由古巴政府出资支持的,实质上即是得到了苏联的资金支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是由国家运转的集权式经济体系,更易于利用政府资源来组织这样的大型活动。古巴政权愿意在文化活动方面大量投资花费的原因主要是在国际领域投射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思维。但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认为它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反击美国对古巴施行的政治隔离,显示国家的良好形象并取悦古巴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对它的看法和思考就会受到局限。自1959年革命之后,古巴因其地理位置和政治上弥撒亚主义的特点,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哨。古巴革命一直都具有扩张的目标,并卷入了革命战争和世界各地的颠覆活动。除了一些其他的明显差异以外,古巴的艺术路径也都具有类似的侵略性。双年展便极好的利用了古巴为推行国家地缘政治目标而建立的设施和网络,尤其是它覆盖世界各国的庞大使馆网络,这一网络在规模上堪与世界强权相媲美,完全超越了国家本身具有的规模和资源。这一网络,包括它的外交系统,建筑,交通,交流以及通信设施,都被用于双年展的组织工作。如果可以说,在某些时期,古巴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政治自治,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它则完全倒向了苏联阵营。然而,古巴却是该阵营中奇特的一员:一个具有非常独特文化的加勒比国家,多数讲西班牙语同时却具有最多非洲裔拉美人的国家,距离美国仅仅九十英里远,钟表显示的是和纽约相同的时间,具有发轫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很长且一直延续的现代传统。古巴革命产生出一个最为强韧也最极端的政权,但是,由于革命是发生在一个以其美妙的音乐和夜生活而闻名的加勒比国家,正如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一句名言: 开着聚会搞革命(revolution with party)
而且,古巴具有真正的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文化以及政治意图,这点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教条格格不入。由于古巴一直扮演的共产主义和苏联政策的桥头堡的角色,从而与中国形成了竞争关系,中国一直反对苏联阵营并努力担当这个角色。这种对抗的结果就是中国以及华裔艺术家未被邀请参加第一届双年展。因此,一方面,出于历史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因,古巴倾向于加勒比,拉美和第三世界文化,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倾向为苏联阵营所支持利用,从而赢得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影响力。
这一背景使得双年展扮演一种历史性角色成为可能。古巴政权带着政治目的创办了这个活动,无视它的艺术和文化范畴及重要性,只是很聪明的把它的组织工作交给了视觉艺术领域的专家团队。政府给参与进来的策展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空间,自己只做产生直接政治影响力的决定,例如排斥中国的参与,但接纳北朝鲜的艺术家,尽管北朝鲜的极权政府仅仅只是在做政府宣传而已。这是革命后古巴政府的典型政策之一:基本能够给予艺术和文化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但时不时的会有一些镇压的插曲。同样很明显的是为了组织这样一场多国大量艺术家参与的盛会,政府就不太可能严格的使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例如,在第二届双年展的目录中就有一段文字以安拉开篇,标明伊朗穆斯林艺术家的主要目的是通向神圣的状态(access a divine condition)[2]。双年展向来自非洲,亚洲,加勒比地区,拉美,中东以及向欧洲和北美移民的当代艺术家,评论家,策展人以及学者提供了巨大的开放空间,互相之间了解熟悉各自的作品以及思想,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隔阂。双年展同时对于来自边缘地区(世界多数地区)除其本地背景之外毫不知名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研究和宣传的平台。当然,政府这样做就成功的达到了它成为第三世界领袖的政治目的。但同时,这也同样满足了非主流当代艺术的急迫需求,给予那些自认为站在全球重要性视角上进行创作的双年展策展人一个广阔的空间。由此政府的政策和展望未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改变当代艺术流通、知识和合法性的想法融为一体。
林飞龙中心直属文化部。中心的领导也即双年展的领导都是文化部信任的G。C。D党员。但她本人,策展人和其他专家都可以按自己的概念来策划双年展,在实际操作中也享受相当大的自由。Llilian Llanes Godoy 自1986年第二届双年展起到1997年第六届为止一直担负指导责任。文化部创建于1976年,奉行一套自由政策,部分引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古巴新一代视觉艺术家和评论人发起的一场深刻的文化革新。这场所谓的新古巴艺术彻底改观了那个时代风行的意识形态挂帅、保守的官方文化[3]. 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视觉艺术到其他艺术领域倡导了一种批判的、后现代的、国际开放的模式,并一直延续至今。双年展的建立正应和了这段时期古巴艺术的革新浪潮,新自由的环境对该活动的本质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1984年第一届哈瓦那双年展规模巨大,但仅限于拉美地区的艺术,原因在于物流和组织的问题,对于组织者来说是一场测试和培训经验的积累。1986年的第二届双年展涵盖了所有第三世界范围。这是一场举办过的最大的全球性的当代艺术展览:规模宏大,形式多样,甚至有些杂乱不堪,举办了50多场展览和活动,共展示了来自57个国家690名艺术家的2400件作品,双年展多种多样的结构使之成为了一场真正的都市节庆,一场全城参与的泼蹡格舞[4]。
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次来自这么多国家地区的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和学者在同一“地平线”相遇:有来自贝鲁特,布拉扎维,不宜诺斯爱丽丝,雅加达和金斯顿,只是点出一部分地区。使这次双年展青史留名的并非它的策展本身而是它的策展思维。如果策展受到了要求庞杂且时间紧迫的任务的拖累,以及我们缺乏知识,准备和组织的影响,那么活动的策展立场则是明确的朝着当代艺术国际化的方向的指导思想行进和实践的,一直到今天。如果我们亲眼目睹了当时乃至今日作为后殖民遗产遗留下来的南南之间联系和互动上的缺失,我们就更能清楚的发现这一开创性活动的重要性。全球化激活了文化流通并使之更加多样化、国际化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它很大程度上是在全球化经济设计的模式下进行的,在重整权力结构下进行的。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隔离是视觉艺术系统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定期的国际艺术盛会早已展开,从威尼斯双年展到卡塞尔文献展,远远不算是国际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参与的艺术家都主要来自西方国家,而且这些展会的艺术观念都局限于西方的主流思维,他们的组织者都对其他地区正在进行着什么并不感兴趣。因此双年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成为巨大的落选者沙龙,得到世界绝大部分的参与,具有实践的精神。如果在当时双年展仅仅包括了第三世界的艺术家,双年展的设立则是为了解决他们受到孤立,缺乏交流和互动机会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活动的组织者认为与西方艺术相对还存在着一种鲜明的本体类型的第三世界艺术。正如路易斯·加姆尼则(Luis Camnitzer ) 所说,双年展不是关于他者,而是关于它性[5]。双年展当然是发现并强调艺术和文化的差异的,但是在一个共享的后殖民的当代艺术实践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它预见到了今天国际上艺术创作和消费的方式。矛盾的是,由于关注于当代艺术,双年展被批评为太西方化了。
第三届双年展比原定计划晚了一年,举办于1989年。尽管这项盛会名字是双年展,但实际上更像是三年展,几届展会都由于组织问题和经济紧缩而推迟。对于1989双年展来说,延误是值得的。那届展会受到了调控,规模尽管仍然很大,但已削减到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共有来自54个国家538位艺术家参与进来[6]。其目录归入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为 Llilian LlanesGodoy, Nelson Herrera Ysla 和我[7]。
然而自双年展开展以来一直都受益于其广泛的团队工作。总策展人去往世界的各个不同地区旅行,带回信息和建议。以我为例,我曾于1987和1988年访问过17个撒哈拉南部国家,并受邀到当地讲座,参加会议或参与其他活动。我同时也访问过美洲的其他国家。出于组织的原因,全球由双年展的策展人根据各自的擅长领域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策展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一种间接的方法,即通过研究拉姆中心收集的大量文献来完成,另外就是通过检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应组织方的公开召集而发来的申请作品。
中心策展人Leticia Cordero, Magda Ileana González-Mora和NoraHochbaum积极地参与到了1989年那届双年展的过程之中。由于双年展集合了不同的展览,会议,研讨会,座谈会以及跨领域活动,这些年轻的策展人也与总策展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投入到了组织工作之中(José Manuel Noceda 和Hilda María Rodríguez),同时也都归入到目录之中。这种团队精神不仅仅存在于拉姆中心工作人员之中,我们也积极的咨询其他国家的策展人,评论家,学者,艺术家以及其他各类专家,以及古巴和其他国家的研究机构。我们不仅用眼睛看着来策展,同时也注意用耳朵来聆听各种建议。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准备不足之处和策展精力匮乏的情况,尤其是在主展的时候,作品的演示非常糟糕,缺乏连贯的展览设计。共产主义国家典型的技术低下短缺的现象也影响到了策展的进程。
自1984年至1989年,所有的双年展都是由林飞龙中心的人员进行策展工作。这一系统从那时起延续至今,更突出机构匿名和集权的风格,主要由中心主任负责。这种方式复制了古巴国家自身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中表露出了组织者对于外国策展人参与程度的理解。双年展在矛盾中成为一场全球活动,总是由那个不变的古巴官方团队来策展。现今,相对于当代艺术展馆,大多数的国际双年展在展出中都尽量少的采用教条的方式,更多的提供主动的空间,邀请策展人在他们的组织中发挥作用,减少机构性,采用更灵活的框架模式[8]。 不过哈瓦那双年展并不是这种模式。并且,它的集中主义使双年展倾向于一定程度的集权主义、官僚主义甚至压制性的立场上,间接或直接的审查活动在最近几届双年展中也时有发生[9]。
第三届双年展,与第二届类似,我认为并不能被当做是一个展览而应是一个有机体系,包含了展览,活动,会议,出版以及不且实际的项目。它囊括了 一场规模巨大的国际展,11个主题群体展览(3位来自古巴8位来自其他各国的艺术家),10个个展(2位古巴艺术家以及8位其他国家的艺术家),2个国际会议以及8个国际研讨会。在这些主要的项目活动之外,还有整个城市中的许多博物馆,画廊,大学,文化之家和社区机构主办的各种眼花缭乱的展览以及艺术,文化和教育活动。这种模式的目的,可能比较理想化,是在一个大的方向上能够有更多的展览方式,同时在各个专门的活动中保持一个特别的主题、艺术和文化侧重。它也希望能够脱离19世纪那种类似市场的双年展类型,构建成为一种用于国家展示,沙龙风格的大型展会,反对将双年展看做一个直接涉及市场反响的大型场面。然而,双年展不可能放弃已经约定成俗的大型重量级展会,这被许多人认为才是真正的“双年展”,周围聚集着各种小型的活动或展览。
双年展的前几届采用了开放多样的组织结构,也是想寻求一种广泛的社会和教育影响力,能够让整个城市更多的参与进来。双年展的门票的是免费的,整个活动在媒体以及学校里都是讨论的对象。尽管有很多不切实际的项目,但更重要的是,双年展存在于城市的每个角落。艺术家和评论家在城市周边的文化中心里工作,在平民聚会中和人们一起讨论、跳舞,一起活动,谈情说爱,帮助布展或参加活动的学生志愿者也参加进来。
大多数的当地艺术家,即便是并未参加双年展的展出活动,他们也以其他方式参与了进来。双年展活动项目在早先的时期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元素-酒吧。
我们一直都在考虑为来自各大洲的参会者在进行非正式会议和交流会时提供一个合适的空间,他们多数都是在比较闭塞的环境中工作。这在1989年的古巴并不容易,之前还没有开放旅游业。即便有几个酒吧,咖啡馆和餐厅向公众开放,也通常是可怕且人满为患的。为双年展而建的两个酒吧位于展会的两条主要大街上,甚至都被写入了第二届双年展列明展览活动的长长的名单之中。这两个酒吧被称之为“会议地点”。酒吧可能是双年展主要的成果之一:构建了一个可以相聚并分享知识的空间。
1989年双年展相对于前几届来说做出了深刻的变革。颁奖和代表国家的展览都被取消了[10]。一个大的主题的方式被引入进来。整个活动的主题是传统和第三世界艺术设计的当代环境。第三届双年展进一步拓展了展览和讨论,引入了国际设计和建筑,但这一举措之后又被取消了。尽管活动的主题太过泛泛,但还是适当其时的分析了对当时“边缘”和后殖民时代艺术的预测,那时正是开始面对全球化的时刻,双年展自1986年起就开始就关注到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说,根据它的想法和实践,第三届双年展的主题就是双年展。这个盛会一直关注着现代和当代艺术,发掘活跃的现代主义多样性的涵义,非常少的关注传统或宗教美学象征的作品,而这在当时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经常当做真正的艺术创作而不是一种模板,而其他作品则被认为是劣质的西方化的作品。
第三届双年展带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那些具有第三世界移民背景的欧洲和北美艺术家也参与进来,例如有些将自己归入英国黑人艺术家,其中有来自圣地亚哥和Tijuana的Border艺术工作室(BorderArt Workshop)。 这个重要的举措目的是为了开阔我们第三世界的地理概念,应该包括移民以及文化变化带来的多样性。这是远离路易斯·加姆尼则(Luis Camnitzer ) [11]所定义的困难的第一步:双年展在越来越多的跨国界市场上仍旧思考着国际化的问题。然而,今天看起来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是必须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才能采用的。在两个问题的处理上一直长期存在着不情愿:“西方化”的危险。双年展更甚一筹,使用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开放给那些早已有能力在国际上流通他们作品的艺术家。
双年展的国际性从这样的事实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即古巴艺术家在展览中所占的数量非常少,从未超过世界其他国家艺术家的数量。我们努力在双年展中展出那些改变古巴文化状态的新兴艺术家,而不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具有官方色彩的艺术家。古巴的新兴艺术家给来访的策展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还被邀请去海外展出[12]。当然,很多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从而证明了双年展是一个很好的空间,那些通常被忽视的“边缘”的艺术家得到了来自其他“边缘”以及艺术“中心”的策展人和评论家的重视。然而,由于来自“中心”的策展人拥有资金和活跃的机构的背后支持,他们比他们少有支持的同行更有能力物色到人才。
这种境况也感染了整个双年展,使之很快成为面向欧洲和北美策展人,画廊和收藏家展出的第三世界艺术展,古巴则又重走老路以旅游为契机发展自身经济。如路易斯·加姆尼则所说,双年展已经从拉美的引领地位演变成为一种Ospaaal的艺术形式,成为一个交替上场的独立论坛,最终变成国际市场的主办人[13]。
1989年新兴古巴艺术家不断的逾越古巴政权早已预备忍受的极限。他们对古巴社会的批判以及他们对官方华丽辞藻的质疑对于一个集权的军政府来说简直就是异端。即便双年展因其具有的国际性背景而应是一个特别提倡宽容的空间,在第三届双年展中古巴艺术家还是因强烈的批判作品而被贬低,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一些漫画家,其中一些是代表官方,一起举办了名为“幽默的传统”的集体展。这是高层指示做出的决定,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转变或减少艺术家在双年展中的社会和政治冲击力。这是古巴正在进行压制和鞭笞的一个信号,很快一些展览就受到了非常严格的审查。同时文化部的自由化的官员如副部长Marcia Leiseca 和Beatriz Aulet被撤职。最严重的压制事件是对艺术家ángel Delgado在一次表演后因涉嫌公众丑闻而被判入狱6个月的处罚,从中可以看出似乎是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一个清晰的警示。其结果是“新兴艺术家”在80年代末大量逃亡并定居海外[14]。古巴艺术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即使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逃离,古巴文化当局也未将他们的政策调整到更加宽容的程度,对于激进的艺术家的限制措施变得非常明显。对我而言,在这些发生之后,感到非常矛盾,很难继续双年展的工作。尤其是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我还曾经是一位新批判艺术的倡导者。这是1989年双年展之后引退辞职的原因之一,同时还因为其他一些事件,我感到对我的信任也与日剧减。 即使我一直都是双年展团队中比较激进的一派,我的逾越精神还是不断升级,越来越与当时普遍的观点趋势相左。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对我而言主要的问题如下:如果我们是在组织一场开拓性的双年展,一场完全不同以往、极力开创新空间挑战主流的盛会,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现有的普遍组织结构呢?为什么要旧瓶装新酒呢?为什么不能因应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综合展出的需要而开创一个特点鲜明的展会呢?
双年展从未做到这点。尽管它已经沿着这个方向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但事实是拉姆中心从未完全掌握展会的优先权。相反的,双年展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标准的国际艺术展,而不是努力寻求新的方式和战略来检验并推出某些措施,从而改变展会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双年展从未在脱离大型展会的模式上走的更远,甚至它得到肯定的多样化的结构在最近几届中也被摒弃了:工作室,会议,讨论会,发布会以及不切实际的项目都被缩减甚至消失了,展会与整个城市的大规模互动也不复存在。
最近几届双年展主要都是由拉美艺术家参与,已经放弃了创造一场全球性展会的努力。
如果说最初的双年展在哈瓦那城市且比较分散,最后几届双年展最有意思的几个方面是由艺术家和年轻策展人在从画廊到私人房屋中的各种空间中组织的多选一, 自治或半自治的展出和活动,目的是为了利用双年展所创造的一展风采的平台和机会。
这些活动太丰富也太分散,非常难于控制和压制,尽管如此官方政权引起的一些事件还是时有发生。这种影子双年展(Ghost Bienal)通常比官方活动更加有趣,集中且更活跃。尽管2009年的第十届双年展中这种非正式活动开始登记、公示出来,从而双年展组织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配合他们的指派,这些活动还是保持了它们部分的棱角,尽管不是那么自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塔尼娅·布鲁格拉(Tania Bruguera)的例外状态 (State of Exception, 2009), 一个由参加塔尼娅·布鲁格拉的Cátedra Arte de Conducta’ (‘Art of Conduct Chair’)的年轻古巴艺术家组织的历时九天包括表演、展览和活动的项目,而塔尼娅·布鲁格拉的Art of Conduct Chair 则是开始于2002年的哈瓦那,是一个历时4年之久的独立讲座。
我坚信双年展已经失去了它的特点和各种可能性。古巴不可能在后冷战时代重塑自身,古巴政权还存活着并通过一些微小的变革仍保持着一人独裁的权力系统,所有的事物还是一样,并没有什么应对这个崭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最终,双年展还是没有足够的独立性,逃离这个创办它的国家赋予它的意志。
[1] 编者注:这篇文章最初作为一篇论文刊载在Afterall和TrAIN(跨国界艺术、身份和国家研究中心)2009年4月3日组织的论坛展览和整个世界(Exhibitionsand the World at Large)上,名为哈瓦那双年展:一个具体的乌托邦(The HavanaBiennial: A Concrete Utopia)的缩减版文章之后在Elena Filipovic,Marieke van Hal 和 Solveig steb(ed.)出版, The Biennial Reader, Bergen and Ostfildern-Ruit: Bergen Kunsthalland Hatje Cantz Verlag, 2010, pp.198–207.
[2] 匿名的,哈瓦那第二届双年展的伊斯兰艺术(‘Artin Islam’),’86: 总目录 (exh.cat.), 哈瓦那: 拉姆中心, 1986, p.413.
[3] 见哥拉多-墨斯凯拉 “新古巴艺术” Ales Erjavec (ed.), 后现代和后社会主义状况: 晚期社会主义的政治化艺术, 洛杉矶, 伯克利和伦敦: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3年, pp.208–46; 和路易斯·加姆尼则, 古巴新艺术, 奥斯丁: 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关于示范性的公众参与,我尤其有印象的是JulioLe Parc和一群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室,位于El Vedado附近公园由可玩的且能互动的活动组成。还有参加Marta Palau工作室的年轻古巴艺术家对装饰艺术博物馆,即小特里安农宫的眺望台的空间所做的改观,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称为Telarte的项目,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服装展,模特们都穿着古巴艺术家设计的布料做成的服装,活动在晚间的老哈瓦那一处殖民广场上搭建的舞台上进行,观众则是周围居民,参观者和本地的艺术家们。
[5] 路易斯·加姆尼则, 关于艺术、艺术家、拉丁美洲以及其他乌托邦(ed. Rachel
Weiss), 奥斯丁: 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 2009, p.217.
[6] 仍是描述第四届双年展的比较小的数字(来自40个国家的150位艺术家)
[7] 见哈瓦那Tercera 双年展 ’89 (exh. cat.), 哈瓦那: 拉姆中心和古巴录放剧场, 1989, p.9.
[8] 见,如, CarlosBasualdo, ‘不稳定的机构’, Paul O’Neill(ed.), 策展主题, 阿姆斯特丹: 当代艺术阿佩尔中心, 2007年, pp.47–52.
[9] 一个发生在2003年针对柯斯达黎加艺术家Priscilla Monge的作品的著名事件,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并促使荷兰的克劳斯亲王基金会(Prince Claus Fund)取消了对双年展的资金支持。
[10] 几乎比圣保罗双年展早20年,该展2006年第27届展会中取消了国家展出
[11] 路易斯·加姆尼则, 关于艺术、艺术家、拉美以及其他乌托邦op. cit., p.225.
[12] 例如José Bedia因在1986年双年展上的表现被邀请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馆拉美1920 –1987 “Art of the Fantastic”,
[13] 路易斯·加姆尼则, 关于艺术、艺术家、拉美以及其他乌托邦, op. cit., p.223. OSPAAAL 是创建于古巴的一个政治组织,支持第三世界极左运动和组织
[14] 见塔尼娅·布鲁格拉, Memorias de la postguerra, 11月,1993, p.12.列出的那个时期从古巴移民的100多位年轻艺术家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