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天中土

洛伊在新德里家中
“我一直都有点烦那些说‘你已经不再写作了’的人,好像我那些非虚构作品就不是写作一样,”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说。
时值7月,我们坐在洛伊的起居室里,紧闭的窗扉把德里夏日的炎热阻挡在外。这里是上流住宅区约·巴格,坐落在16世纪墓葬群“罗迪花园”对面;近日来德里或许被缓慢发展的经济、对妇女犯罪的上升与即将到来的选举弄得颇不安宁,但这里却是风平浪静。洛伊收养的流浪狗菲尔茜睡在地上,肚皮有节奏地上下起伏。一阵忧伤的鸟鸣从空中传来,“那是犀鸟,”洛伊若有所思地说。
洛伊或许是因为她的《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而广为人知的,这部小说描写了跨越种姓、阶级与信仰的两段感情,一段导致了谋杀,另一段在乱伦中达到顶峰,直至近日,她才重返虚构写作。那是一部小说,但她至今仍对小说主题秘而不宣。此外,她还在努力摆脱自己二十年来行动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并且要略带勉强地摆脱一项“最后的任务”。这举动比她抨击印度占领克什米尔、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的战争,乃至裙带资本主义等等还要大胆。这一次,她的目标直指圣雄甘地。
一个名叫《新工具》(Navayana)的印度小媒体要她为新版《种姓的灭绝》(The Annihilation of Caste)写一篇介绍文章。《种姓的灭绝》是进步领袖B·R·安贝德卡(B. R. Ambedkar)1936年的著作,他曾起草印度宪法并皈依佛教。这篇文章或许是当代对印度种姓制度最著名的一篇檄文,其中指责甘地只想废除贱民阶层,不想废除种姓制度。安贝德卡认为整个种姓制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是不民主的。读过安贝德卡和甘地的往来争论,洛伊对甘地的倒退立场深感失望。这篇为《种姓的灭绝》所写的短小介绍开始在她头脑中扩展,“几乎成了一本小书。”其中涉及甘地的部分,她也不打算手下留情,这样便很容易引发争议。就连安贝德卡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他的观点被认为是挑衅的,因此只能自费出版。洛伊愈说这个话题,似乎就在这个“最后任务”的复杂困境中陷得愈深。
洛伊带我来到隔壁房间,书籍和杂志散乱地摊在她用来当书桌的一张餐桌上。大量安贝德卡和甘地的论战文集堆积如山,书页间还夹着书签。摊开的笔记本上,可以看到洛伊用工整的小字写着零散想法,在两个巨人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中间充当微妙的中间人。
“过去我因为自己的非虚构写作陷入了麻烦,”洛伊说,“我曾对自己发誓‘今后再也不写任何带脚注的东西了’。”迄今为止,她并没有兑现这个誓言。“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想法,和各种问题搏斗,被我读到的东西所震惊,”当我问她是否已经开始动手写这篇文章时,她说,“我知道,文章一旦发表,就会发生很多事。但这是我需要去做的事。”
洛伊在年近不惑之时成了印度最著名的作家。《微物之神》于1997年出版,同年亦是印度独立50周年。那是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阶段之初期,洛伊被视为印度品牌的代表。那部小说是她的处女座,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赢得布克奖,卖出了600多万册。英国小报发表令人困惑的特写,诸如《泡菜厂弃儿写出价值50万英镑的书》;在杂志为她拍下的照片上,她留着浓密的波浪卷发,有着高耸的颧骨,背景是印度喀拉拉邦天然纯净的河流与繁茂的绿叶。当时喀拉拉邦刚刚开始成为旅游者的目的地,洛伊小说中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洛伊的国民偶像生涯在一年后戛然而止。当时印度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这在认同印度教国家主义的印度人当中引发了广泛赞许,其中很多人都属于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洛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想像的终结》(The End of Imagination),她谴责核试验的支持者们沉迷于炫耀武力——正是对沙文主义的信奉令印度人民党在印度独立之后第二次掌握权力——但这些支持者们却对大多数印度人所生存的苦难环境漠不关心。这篇文章还同时刊登在《展望》(Outlook)和《前线》(Frontline)两本英语杂志上,标志着她公开成为一个政治作家。
洛伊的政治转变令许多和她同属上层种姓、说英语的印度城市读者大为震怒,但也有许多人喜欢她的转变。她的新拥趸之中,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她的小说;他们也不说英语,在这个国家因为信仰、种姓或种族被边缘化,被印度的经济增长大潮所抛弃。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洛伊的文章,它们通过未经授权的翻译得以传播;洛伊有演讲时,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去听。“对《微物之神》的普遍愤恨是可以理解的——有这么一个人,用英语写作,还赚了那么多钱,”洛伊说,“所以当《想像的终结》出来的时候,情况逆转了,愤恨开始在说英语的人群中滋生,但这篇文章却被其他人所接受。”
这些剧烈的反响令她惊讶。“《微物之神》和我这15年来的政治写作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洛伊说,“这是我本能的领域。”的确,她的小说中也探索了社会公正问题。但是对于她的批评者们来说,没有了角色与情节的支撑,她的文章似乎有些迂腐,或者说,根本就是错的,只是对充满活力与意志的印度的廉价攻击。就连那些同情她观点的人也经常质疑她的名人身份,觉得她在政治写作领域只是玩票。但洛伊从没考虑过只把政治写作当成副业。“如果当时我不就核试验说点什么,那就好像我在为它唱赞歌一样,”洛伊说,“那时候我经常出现在各种杂志的封面上。对此一言不发也会产生一种政治效果。”

2012年,洛伊从提沙监狱出狱后。
其后,洛伊的目光转向了纳尔马达河上修建的一系列大型水坝。许多因这项工程要被迁走的村民展开抗议,就连印度最高法院批准水坝建设继续进行后也没有放弃。洛伊赶到那个地区参加抗议活动,写下若干文章批评法庭的判决。2001年,一群男人控告洛伊和其他激进分子在最高法院外面围攻他们。洛伊向法庭申诉,要求驳回控告。法庭同意了,但被她的申诉中所用的言辞所激怒——她指责法庭试图“扼制异见,骚扰和恐吓意见不同的人”——于是判处她蔑视法庭。“为示法律的宽宏大量,同时考虑到被告是女人,”法官读道,“希望被告在将来获得更多理智与智慧,为艺术与文学事业服务,”洛伊被判处“入狱一天”以及缴纳2000美元罚款。
BBC电视台2002年的纪录片《水库/时代》(Dam/Age)中拍下了洛伊在城堡般的提沙监狱服刑前后发生的戏剧情景。第二天她出狱后便彻底脱胎换骨,从印度偶像变成了严厉的国家批判者。她把自己的头发修剪成极为朴素的样式,令人不安地联想到一个被放逐的女人,乃至好斗的女权主义者。一家印度英文媒体嘲笑洛伊对大坝的批评,他们认为大坝是印度崛起的证据。其后她所有的作品都受到攻击,她的谴责对象包括2002年古拉吉特邦对穆斯林的屠杀、一家名叫“吠檀多资源”的伦敦公司在奥里萨邦(如今的奥迪萨邦)开采铝土矿的计划、印度中部对土著人及纳萨尔派极左武装游击队采取的准军事行动,以及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军事行动,当时有50多万名军人进驻克什米尔,制止那里占多数的穆斯林人口谋求脱离印度的行动。
印度迄今共经历过四次战争,其中有三次是同巴基斯坦争夺克什米尔,它成了洛伊的关键论题之一。2010年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有几个十几岁男孩与军人对峙的情景,洛伊公开称:“克什米尔从来就不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说,印度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概念,和巴基斯坦一样,只是印巴分离的产物,这番话越线了。印度的大多数改革分子也没有走得这样远。洛伊很快发现自己成了一场全国性风暴的中心。乌合之众向她抛石头、电视台的报道车跟在她身后,出现在她门前。保守派电视台“Times Now”用慢动作播放她访问克什米尔的短片,片中她迈着舞步般的步伐走过一条小道,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镜头回到德里,“Times Now”召集了一群人,由电视台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阿纳布·格斯瓦米(Arnab Goswami)主持,讨论是否应该以煽动罪逮捕洛伊,节目中除了新闻标题和新闻,“愤怒”和“阿兰达蒂”是最常出现的两个字眼。讨论组中唯一的一个克什米尔穆斯林哈米达·纳伊姆(Hameeda Nayeem)指出,洛伊所说的一切都是大多数克什米尔人普遍相信的东西,这时她的话被格斯瓦米打断了。在班加罗尔和昌迪加尔都有人对洛伊发起诉讼,控告她“反国家”、“反人类”,人们普遍认为她有一篇文章里写道:“克什米尔应当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印度人手中取得自由。”
7月份我到洛伊家中采访她,她的公寓占了一栋三层楼的整个顶层,这座楼拥有一切上流阶层住宅的附属设施——四周环绕着草坪、有高高的围栏,还有一个小电梯。屋中能表明异见者身份的迹象寥寥无几,她门上的贴纸写着“最近这些日子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起居室里有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爱德华多·加利亚诺(Eduardo Galeano)的作品,这些书在印度都不常见,家里没有佣人,她完全一个人生活。或许最有说服力的是洛伊如何决定住进这栋房子,以前她每天都要骑着用一个卢比租来的自行车路过这里去上班。
洛伊原名苏珊娜·阿兰达蒂·洛伊(Suzanna Arundhati Roy),1959年出生于印度东北边境的山地小镇西隆。她的母亲玛丽来自喀拉拉邦一个团结紧密的叙利亚裔基督徒社区。她的父亲拉吉布是来自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印度教徒,在西隆附近一个茶园当经理,酗酒。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洛伊两岁的时候,她和一岁半的弟弟拉里斯同母亲回到喀拉拉居住。他们不受母亲娘家的欢迎,搬到了泰米尔纳德邦的奥提,毗邻喀拉拉邦,住在洛伊外祖父的一栋乡间小屋里。
“后来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洛伊说着笑起来,“我妈妈病得很重,非常严重的哮喘。我们觉得她要死了。她会让我们带着一个篮子到镇上去,商店店主们会在篮子里放上食物,大都是大米和青椒。”直到洛伊五岁,全家人都住在那儿,外祖母和舅舅一直逼他们搬出房子(在叙利亚基督徒中,继承法严重偏向儿子),他们拒不服从。最后,洛伊的母亲搬回喀拉拉,借当地扶轮社的场地开办了一所学校。
作为单亲母亲的孩子,洛伊和传统叙利亚基督社区相处并不融洽,而是和那些低等种姓的人或达利特人相处更好。基督徒和高等种姓的印度教徒通常对这些人避而远之。

洛伊在电影《安尼为此而付出》中。
“我的许多想法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她说,“没有人注意我,要费心给我灌输什么东西。”后来她被送进劳伦斯学校,那是一所由英国军官创立的寄宿学校,校训是“永不屈服”。到那时再进行灌输教育或许已经太晚了。洛伊当时十岁,她说自己关于劳伦斯唯一的记忆就是,自己在那时迷上了跑步。她的弟弟目前在喀拉拉邦经营一家水产出口公司,他对姐姐那个时期的回忆有所不同。“上中学时,她在高年级男孩中很受欢迎,”他笑着告诉我。“她还是个非常优秀的辩手。”
洛伊承认那座寄宿学校也有好处。“它让我逃走的时候更轻松了些,”她说。她父母的婚姻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之后的离婚更是耻辱,因此周围的人们期望洛伊有比较谦逊适中的抱负。从她就读的第一所大学可以看出她的前景——那是一所由修女经办的学校,提供秘书培训。但是,16岁那年,洛伊搬到德里,进入建筑与规划学校学习。
洛伊选择建筑,是因为这能让她在入学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但也是出于理想主义。在喀拉拉,她结识了在英国出生的印度建筑师劳里·贝克(Laurie Baker),他以设计成本低廉、结实耐用的建筑著称,于是她也想做类似的工作。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在学校里学不到这样的东西。“他们只想让你当个承包商,”洛伊努力思考的问题是教授们无法解答的,“你的审美标准是什么?你为谁而设计?就算是室内设计,那么住在里面的男人和女人们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城市变得愈来愈大,应当如何规划?法律为谁服务?什么样的人才可被称为公民?到最后,这一切对于我而言变成了非常政治的东西。”
做毕业设计的时候,洛伊拒绝设计一栋建筑,而是写了一篇论文:《后殖民时期德里的城市发展》(Post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in Delhi)。“我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学了什么。我不想让你们来告诉我我在这儿学了什么。’”洛伊从身边的同学们当中汲取反主流文化的营养,几年后用在了电影《安尼为此而付出》(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 1989)中。剧本是洛伊写的,还参与了影片设计,并在片中亮相,饰演一个精灵般的角色,头顶巨大的非洲式卷发,名叫拉达,放弃建筑行业从事写作,但是没写完第一部小说就淹死了。
当时洛伊和家庭断绝了关系。没有钱住在学生公寓,便和男友格兰特·达·卡纳(Gerard da Cunha)搬进了附近的贫民区。为了顺应贫民区保守的风俗,他们假装已经结婚。“当一个想体验贫民区生活的年轻人是一回事,”洛伊说,“对于我来说又是另一回事。那里什么人物也没有,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东西,那里是我的大学,那段时期你会从绝对弱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些影响至今还留在我身上。”
毕业后,她和达·卡纳在他的故乡果阿短暂同居了一段时期,两人分手后她回到德里。她在城市事务国家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Urban Affaires)呆了一段,认识了独立电影人普拉迪普·克里什纳(Pradip Krishen),他邀请洛伊在电影《梅塞·撒伊卜》(Massey Sahib, 1985)中担任女主角,影片发生在殖民统治期间的印度,洛伊饰演一个牧羊女。洛伊后来嫁给了克里什纳,两人其后合作创作了一系列项目,包括26集系列剧《巴尔加德》(Bargad),反映印度独立运动,但一直也没有拍完。此外还有两部电影长篇,《安尼》(Annie)和《电子月亮》(Electric Moon, 1992)。
克里什纳的背景与洛伊截然不同,他是来自贝列尔学院的学者,前历史教授,鳏夫,与父母和两个孩子住在时尚的卡纳克亚普利一座大宅里。洛伊搬进来后,他们住进了楼上一个独立住宅。洛伊和德里的独立电影界打成一片。那些前卫的电影题材深深吸引着她,但那是一个由精英家庭的后代主宰的圈子,她很快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她用愈来愈多的时间教授有氧操,为自己赚钱,和在学校里认识的艺术家们呆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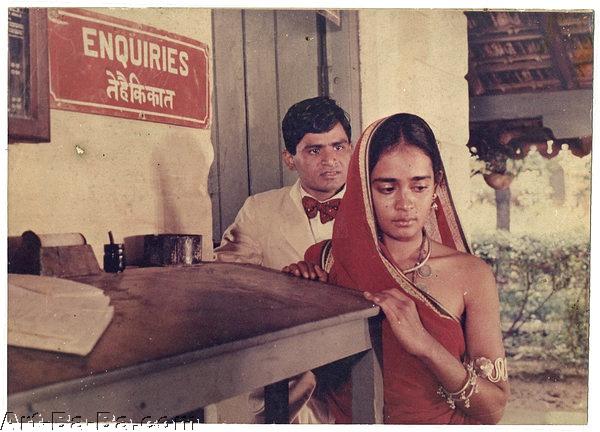
洛伊在电影《梅塞·撒依卜》中。
当她开始写自己的小说时,正赶上电影《土匪女皇》(Bandit Queen)上映,它是根据女土匪普兰·黛薇(Phoolan Devi)的生平故事改编的。黛薇出身低等种姓,后来成为著名匪帮头领,经历了匪帮的强暴,后来被捕入狱。片中把她塑造成一个牺牲品,决定了她人生的是被强暴的经历,而不是反叛精神,洛伊对此感到愤怒。“看着部电影时我非常生气,部分是因为我是在喀拉拉邦长大的,看多了这种马拉雅拉姆语电影,每部电影——每部电影里都有女人被强暴,”洛伊说,“很多年来,我相信所有女人都会被强暴。后来我看到报纸上普兰·黛薇说看了电影,感觉像是又被强暴了一遍。我看了电影改编依据的原著,发现拍电影的那些人自己添加了强暴戏。我想,你们把印度历史上最著名的土匪改编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强暴受害者。”洛伊对该片的影评《伟大的印度强暴骗局》(The Great Indian Rape Trick)刊登在如今已不存在的《星期日》杂志上,痛斥《土匪女皇》的拍摄者,指出他们根本就懒得和普兰·黛薇本人会面,也没有邀请她参加放映式。
这篇文章令洛伊的许多共事者逐渐疏离了她。克里什纳和洛伊分手后,还对她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说这篇文章看上去像是对德里团结紧密的电影圈的一种背叛。洛伊则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媒体的运作方式。“我密切关注着普兰·黛薇身上发生的事,”她说,“我看到媒体是怎样挖掘你,把你掏干,然后就丢在脑后。我幸运地从这件事中学到了这一点。所以等轮到我的时候,就提前做好了防备。”
第一次采访相隔几天之后,我在新德里机场再次与洛伊见面,她在人群之外徘徊,不理会投向她的目光。她拒绝了在克什米尔一次公共集会上的演讲,但到那里去旅行仍然具有政治色彩,因为一周之前,那里有八名印度士兵在伏击中被杀。洛伊和我在航程中遇到的旅客大都是去瞻仰阿马尔纳特神殿的印度教朝圣者,他们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在小飞机里,他们不时举起右拳,同声呼唤“Bom Bhole”,或“赞美湿婆”。在印控克什米尔的首府斯利那加,洛伊经常被克什米尔人拦下,他们想感谢她那些对抗印度政府的言论,还希望与她合影。通常她都会配合。
但大多数时候,她都躲避公众的目光。洛伊呆在一个记者朋友的家里,他和另一个记者在讲手机,说着关于阿马尔纳特朝圣者与克什米尔服务人员之间爆发的争斗。洛伊分发着从德里带来的拉瓦萨咖啡,心不在焉地听着。后来,她拒绝了参与拍摄一部关于纳萨尔派游击队的新纪录片的邀约,她宁愿去写自己的小说。
洛伊来克什米尔主要是为了看望朋友,但很难从这里的冲突中脱身。几天后,我们开车行驶在乡间,溪流在绿色原野和鹅卵石之间闪现,不时出现身披伪装、携带枪支的身影。有时是印度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分遣队,有时是地方警察,偶尔也会看到镇压叛乱的拉什特里亚步枪队,可以从他们扁平的帽子看出来。“我第一次到斯利那加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掩体,”洛伊说,“现在他们在城市使用电子监控,公开的警察力量都在乡间。”
这一周的早些时候,在斯利那加,警察的监控已经非常明显。洛伊被邀请参加库尔拉姆·帕尔维(Khurram Parvez)组织的集会,他是查谟与克什米尔公民社会联盟的成员,这个组织曾经大量报道克什米尔的万人坑与非法杀害事件。集会上,40余人盘腿坐在地上——他们是社会活动者、律师、记者和学生——帕尔维要他们关掉手机,把手机放在“腿部”,以免有人录像,交给官方。
洛伊戴上眼镜,她面前有一摞书,是过去15年间她的非虚构写作精选集(由印度企鹅出版社出版,是盒装的五本书,糖果色封面),给集会带来一种即兴的学术气息。洛伊要观众们说出他们的想法。一个在距离斯利那加30英里外的乡村长大的年轻律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女人被士兵强暴后,整夜都在两个浴室隔间里发抖,因为羞耻,不敢回家,听着对方哭泣。洛伊认真地倾听着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类似故事,偶尔把话题引向克什米尔之外整个印度的分裂与分歧,包括印度中部的森林,2010年,为了创作新书《破裂的共和国》(Broken Republic, 2011),她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星期,访问极左游击队以及他们的部落联盟。

阿兰达蒂·洛伊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家中。
“当我在印度旅行,看到克什米尔人加入边防安全部队时,感到非常悲伤,”她说,“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做的,从国家的这一部分征兵,然后把他们送到国家的另一个部分去打仗,对抗表面上和他们不一样,但其实与他们面临类似压迫的人们,所以对话才如此重要。”
她拿起面前的一本书,是柠檬黄色的《聆听蚂蚱的声音》(Listening to Grasshoppers),从《自由》这一章中找出一段。在这里,她描写自己在2008年在斯利那加参加要求从印度独立出去的集会。“这句口号像刀子一样刺穿我,”她用安静而清晰的声音读道,“就是这句:Nanga bhooka Hindustan, jaan se pyaara Pakistan。”——印度是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国家;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比生命更重要。“从这句口号里,”她说,“我可以看出受害者是多么容易变成加害者。”
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话题扩展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其后变化,之后又回到克什米尔。克什米尔人对巴基斯坦有认同感吗?有些人有,有些人显然没有。女性在克什米尔自决的斗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她们在这个屋子里的发言都让人很难听清,她们该怎样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顶着夏日的炎热,这个团体分裂成几派,变得愈来愈疲惫和激动。洛伊决定用“巨蟒”(Monty Python)的电影《万世魔星》(Life of Brian)里的一个笑话结束讨论。
“电影的主角布莱恩问一群游击队员,‘你们是“犹太人民前线”吗?’”洛伊模仿着英国口音,“对面其实是反对组织,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绝对不是。‘我们是“人民反犹太前线”’”这个笑话巧妙地讽刺了种族党派之争,让洛伊自己开心地笑起来,也改变了室内的情绪。我们走出房间,走在小巷里,不同的小组似乎相处得很融洽。后来,一个刚读完虚构写作学位的年轻人告诉我,这场谈话无法被写下来,令他感到很失望。
除了甘地的书,还有很多事令洛伊从小说创作中分心。5月,纳萨尔游击队杀死了至少24人,包括一个组织了残忍的右翼民兵组织的议会政治家,洛伊曾在新书中批评过他。媒体很快要求她发表评论,但她拒绝开口。“于是他们发表了我的一篇旧访谈,假装是新的,”她说。
“我需要直接说出的东西都已经说过了,”她说,“现在我觉得,如果开口无非是通过不同的细节,再次重复自己。”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她顿了一下,知道下一个问题是问她的新小说会有多么政治化。“我不是那种会使用小说党手段的人。我觉得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不像电影,它不是政治宣传册,不是一句口号。我过去在政治领域思考的方式如同必须被打破和遗忘的蛋白质,直到它成为皮肤上冒出的汗珠。”
但最近的印度,出版也成为充满风险的行当;法庭法令被用来阻止图书出版,或强迫下架,就算显然非政治的书籍也会遭此待遇。最近,印度企鹅出版公司受保守印度教团体压力,把温迪·德尼格(Wendy Doniger)的《印度教徒:另一种历史》(The Hindus: An Alternative History)全部化为纸浆,该团体对该书发起了诉讼。企鹅公司也是洛伊的出版商,她觉得有必要抗议。
洛伊对最好的朋友也不愿透露新小说的内容,但她坚持说,这本书象征着她与自己所有的非虚构写作以及她的第一部小说彻底决裂。“我不是在试图写另一本《微物之神》,”她说,“新书里有更多概念性的困境。写一本关于家庭的书要容易一些——《微物之神》就是这样的——会有更清晰的心绪。”在着手写作安贝德卡与甘地的文章之前,她正开始为小说而画画,这是她在创作的早期阶段喜欢做的事,通过画画来理清结构。然后就通过手写来写作。然后坐在厨房的桌边,在笔记本电脑上修改,她把这个步骤称为“打磨”。
“我不去什么特殊场合,”我问她写作时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程序,她答道“我只是不想感觉到有人在我身边呼吸”。
《微物之神》出版后,她开始把一些版税送出去。她的父亲看到她在《梅塞·撒伊卜》中出现后重新和她取得联系,不排除动机是想从她这里弄些钱,她把他送进了一处养老院,他于2007年去世。2002年,洛伊收到了一份蓝南基金会的奖金,她把这35万美元捐给了全印度的50个小型组织。2006年,她和朋友们兴办了一份信托基金,她将自己非虚构写作的全部所得投入进去,支持印度全国的各种进步事业。
“我对成为职业作家根本不感兴趣,不就是写了一本书,还不错,然后就一本一本接着写,”洛伊思考着《微物之神》如何限制了她,又令她获得自由,“我有一种恐惧:因为你出名了,或者因为你做成了什么事,所有人就希望你一直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人,把你冻结在时间里。”洛伊是指她生命中的那个时刻,她厌倦了自己的那些形象——从迷人的印度偶像到迷人的印度异见分子——于是她剪掉了头发。但你可以看到,站在新立场上,她说的还是同样的话。关于甘地和安贝德卡的文章意味着她在转向新方向之前,先要把过去的抱负做个完结。“我不想要那么沉重的包袱,”洛伊说,“我想轻装出行。”
本文作者Siddhartha Deb是《美丽与诅咒:新印度的肖像》(The Beautiful and the Damned: A Portrait of the New India)一书作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3月9日。
中文版地址《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