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赴台和著名诗人余光中会诗
地下的蓝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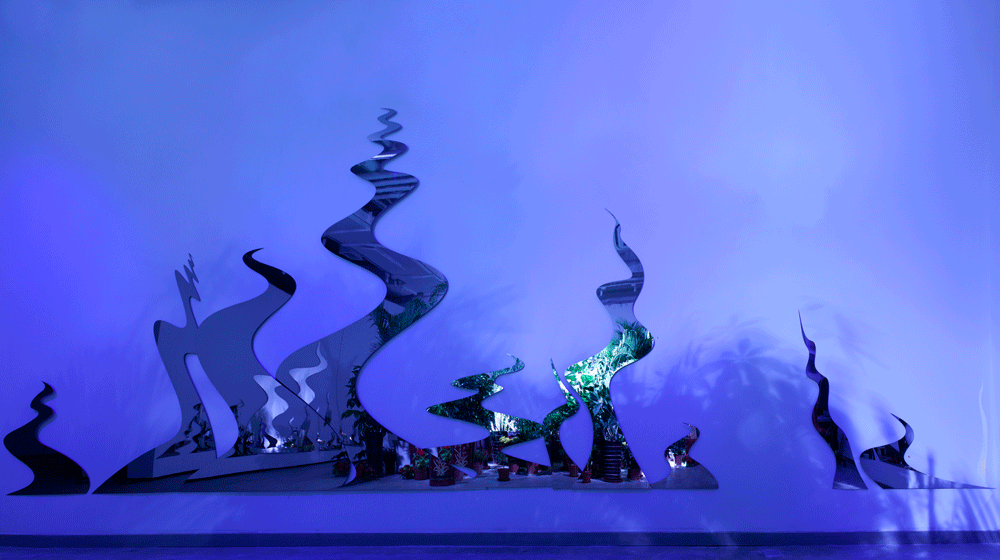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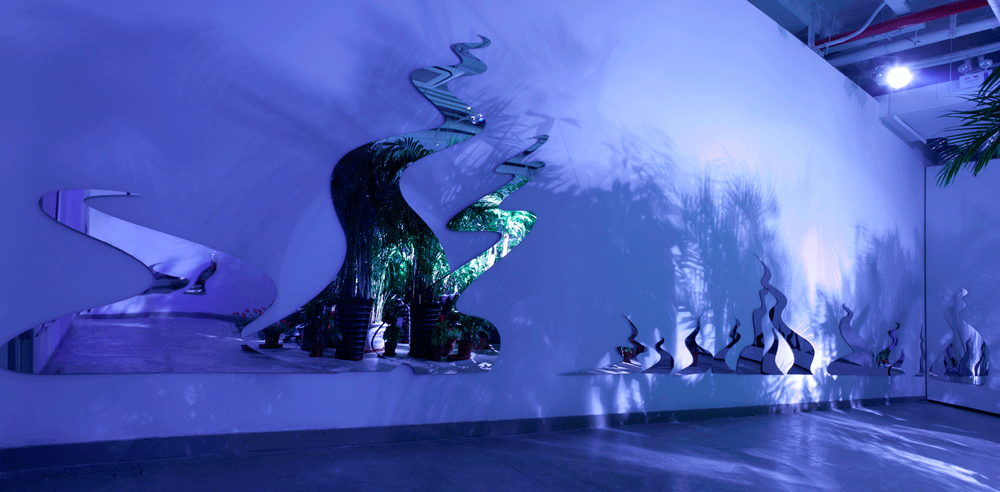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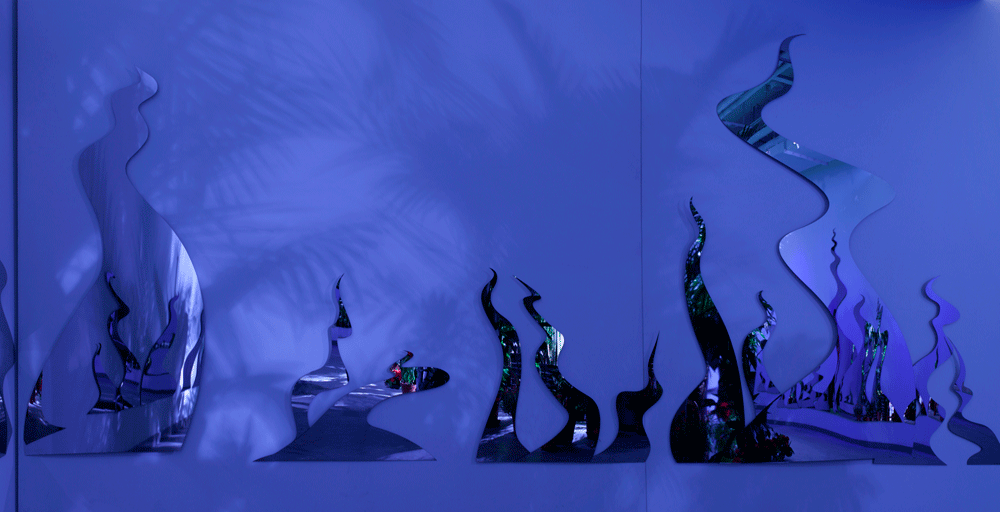

射云

无法命中的标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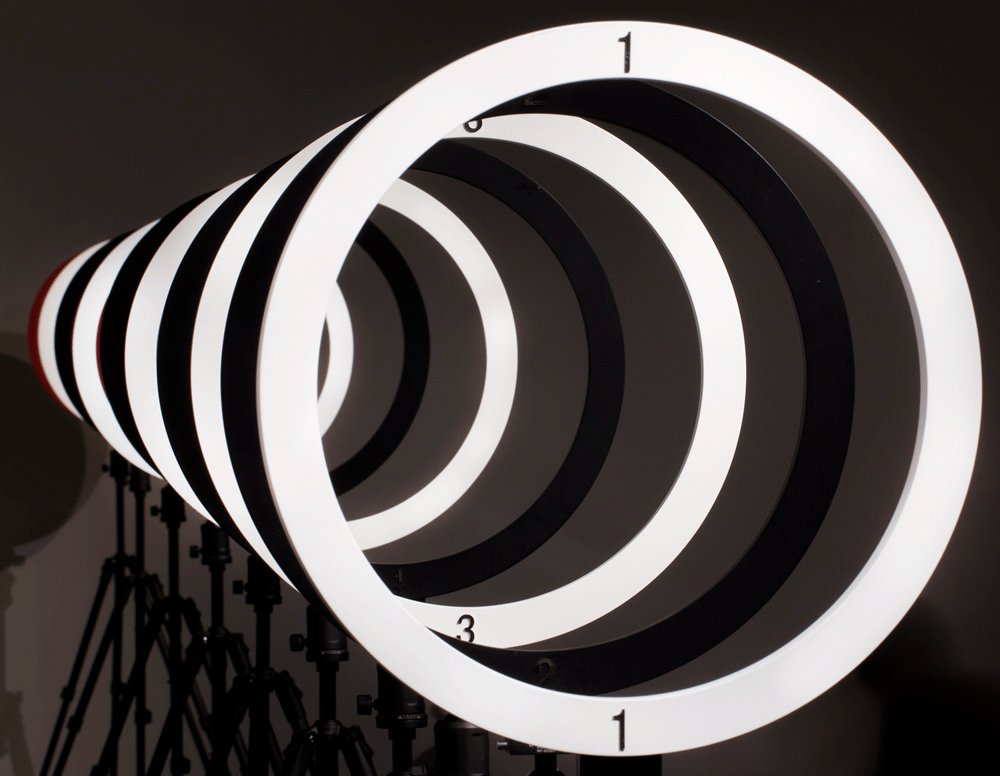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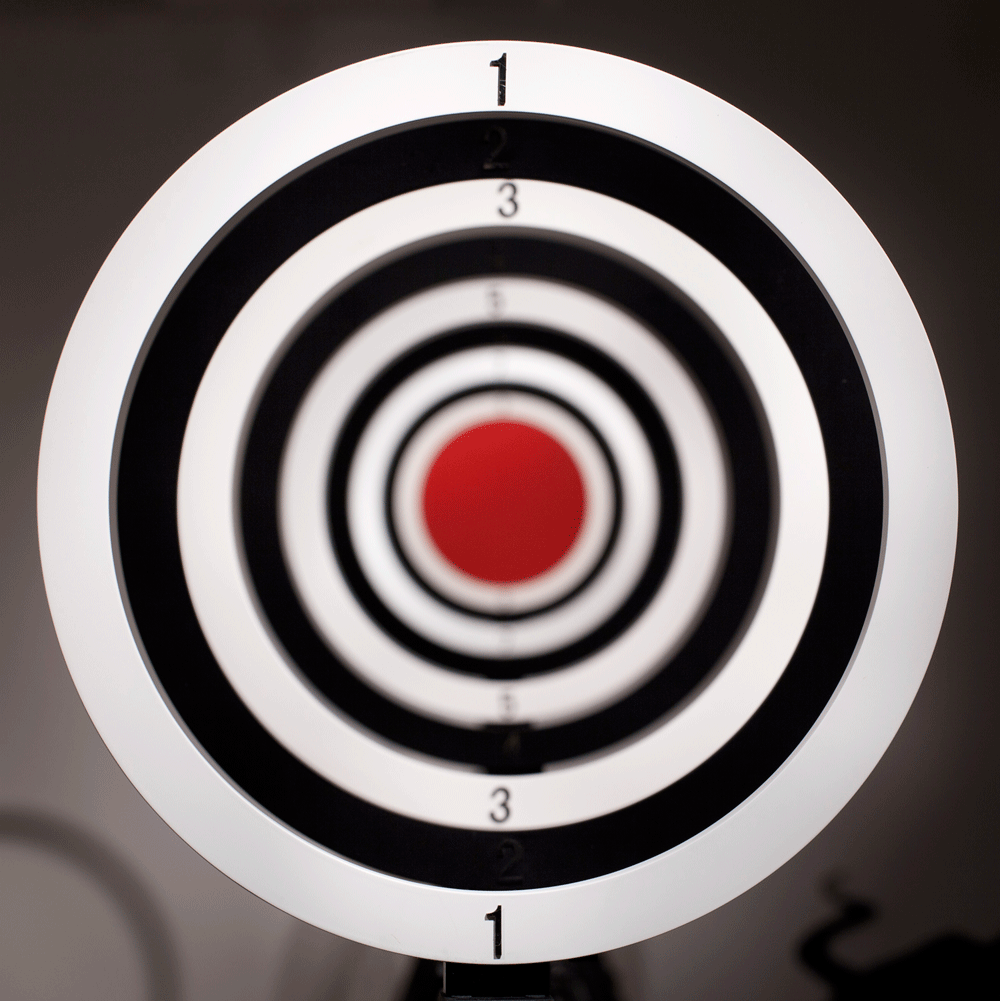


楼上
把弹簧切成上下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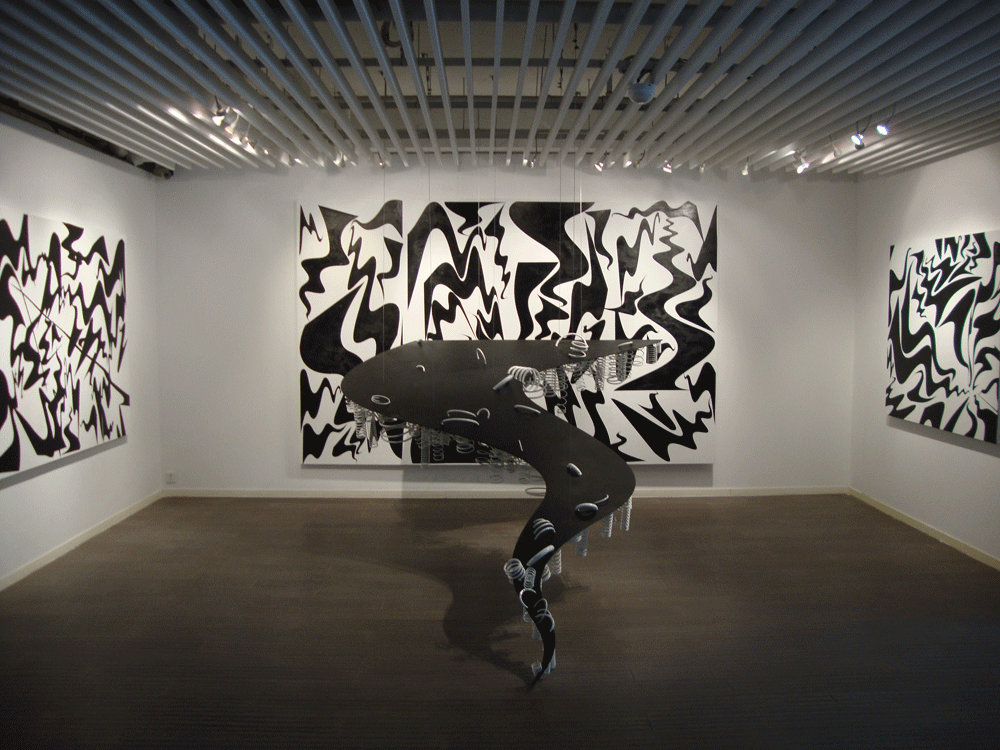


还有几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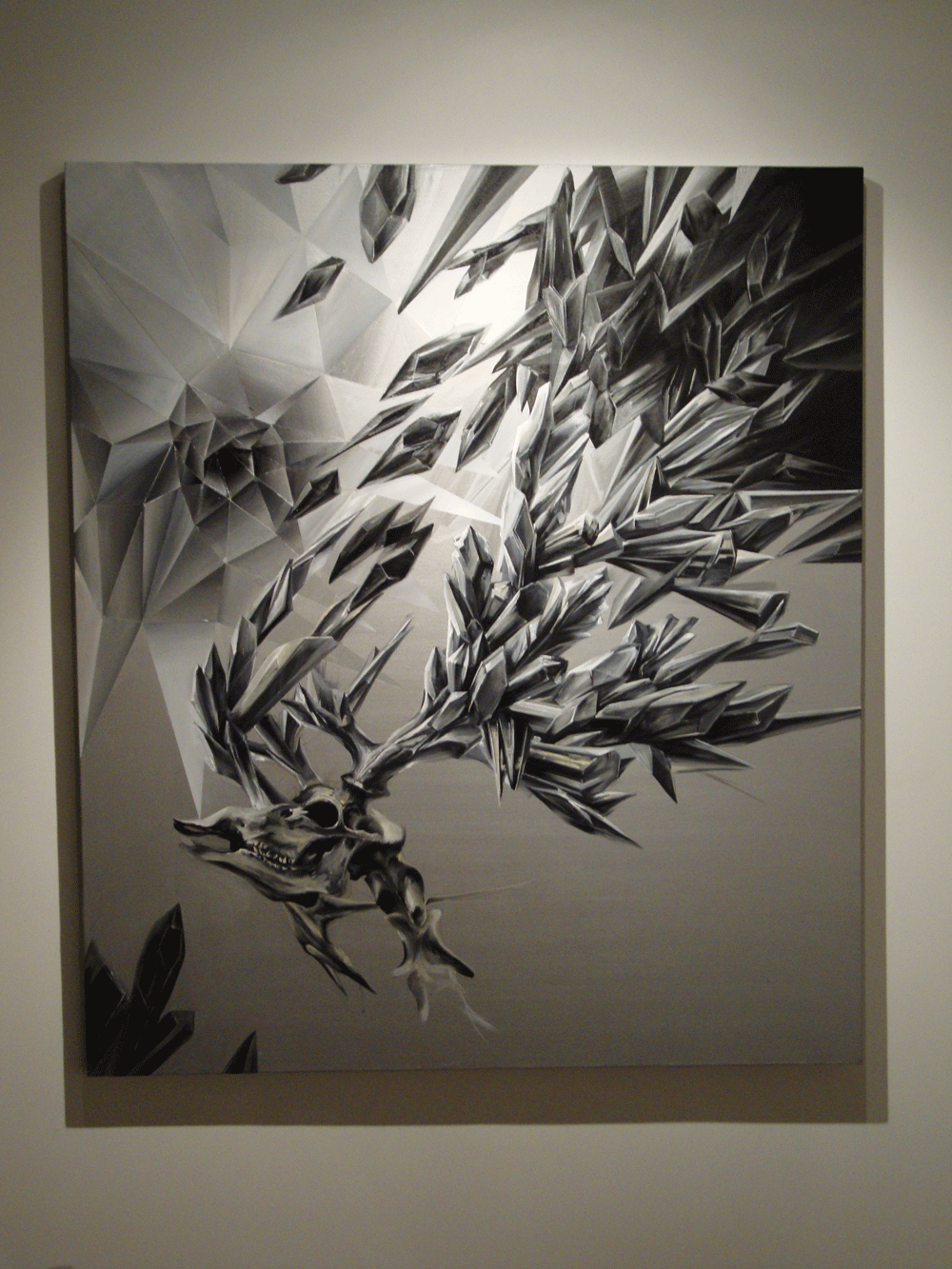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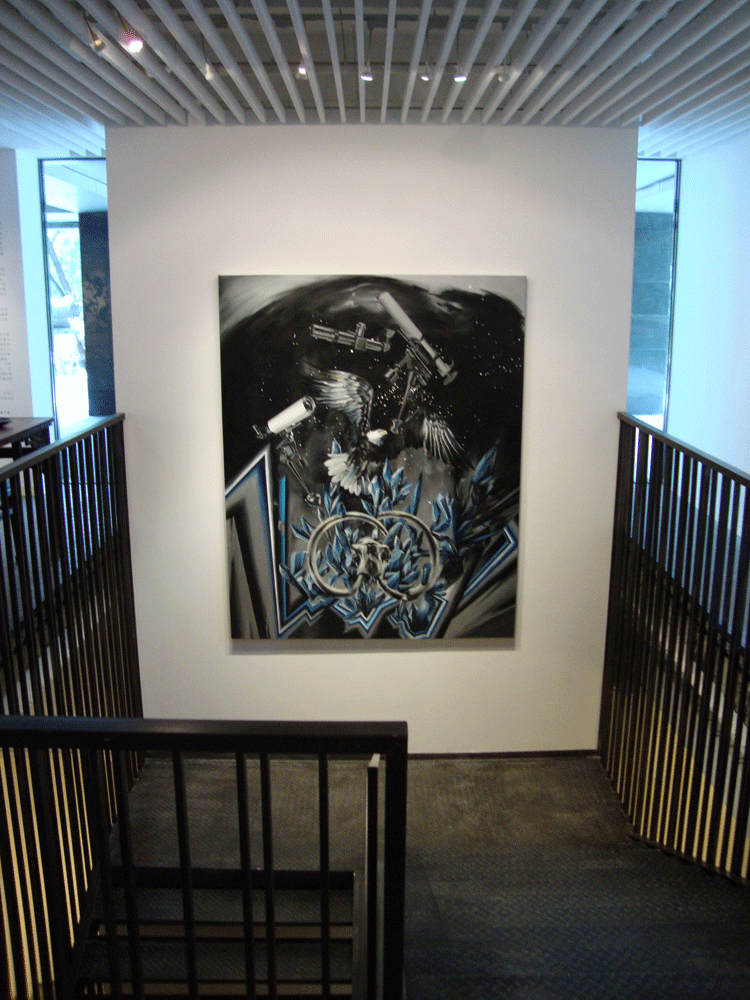

不锈钢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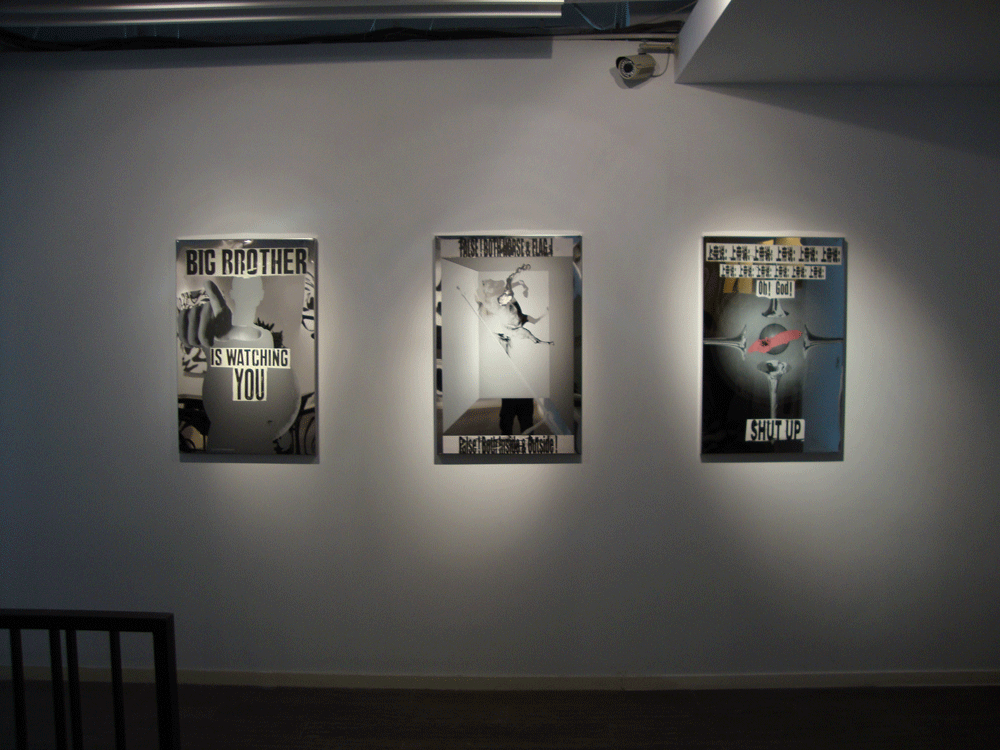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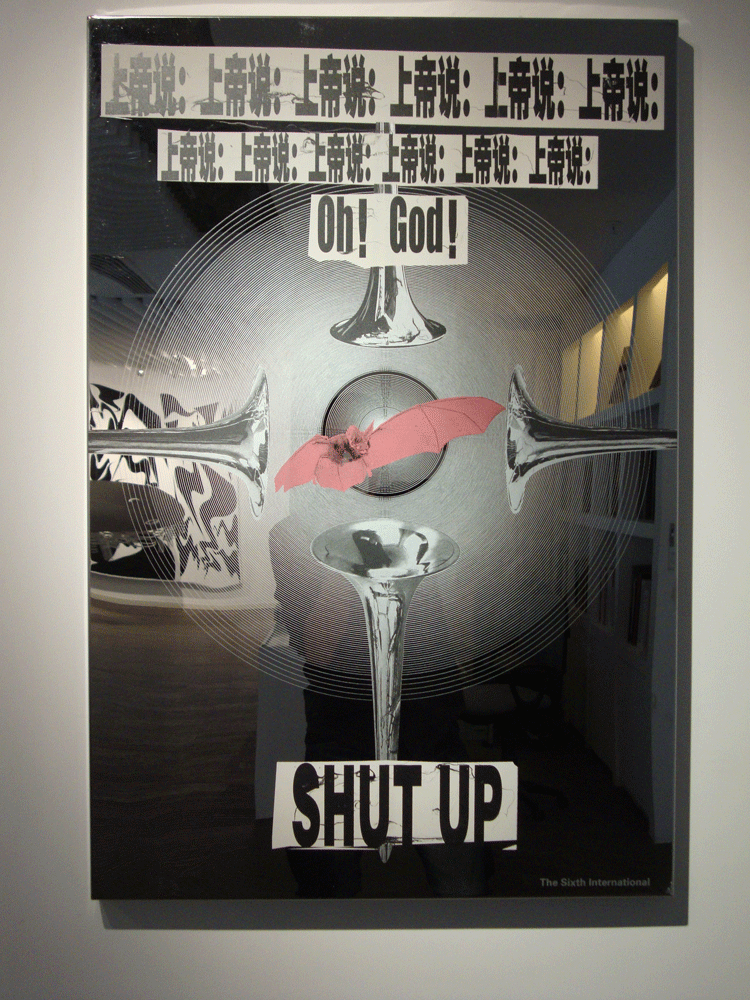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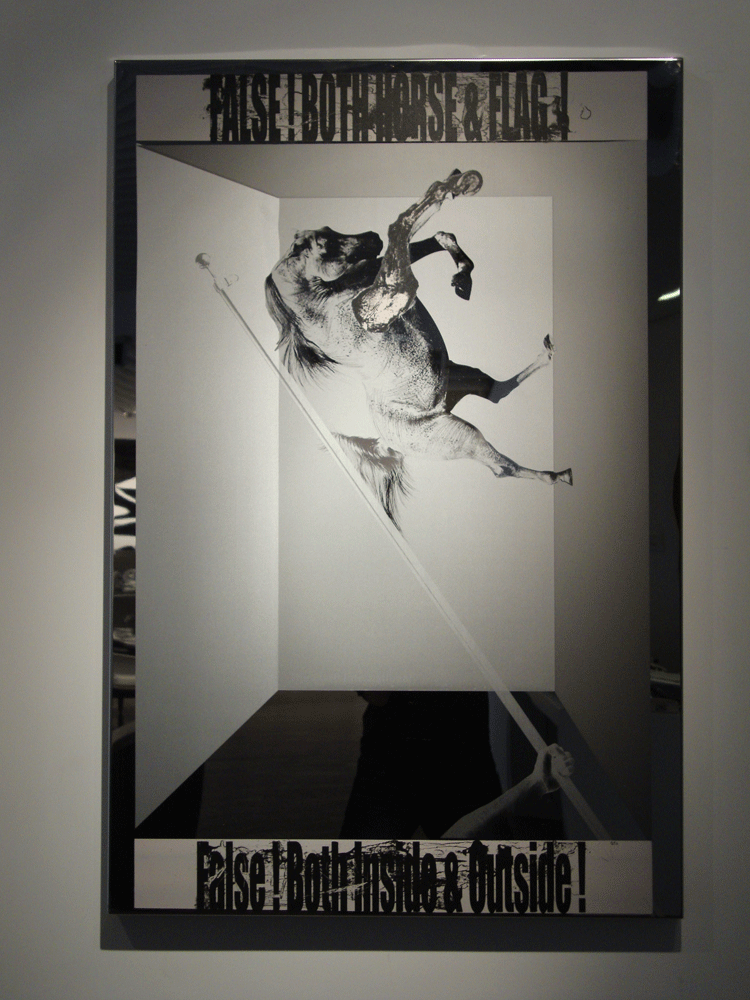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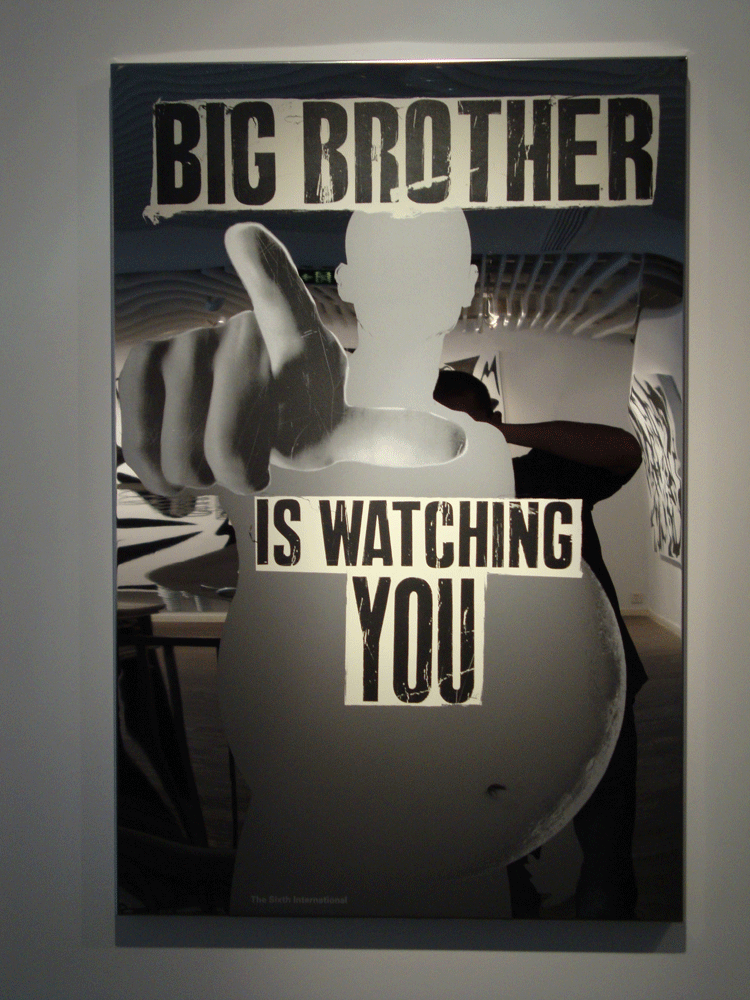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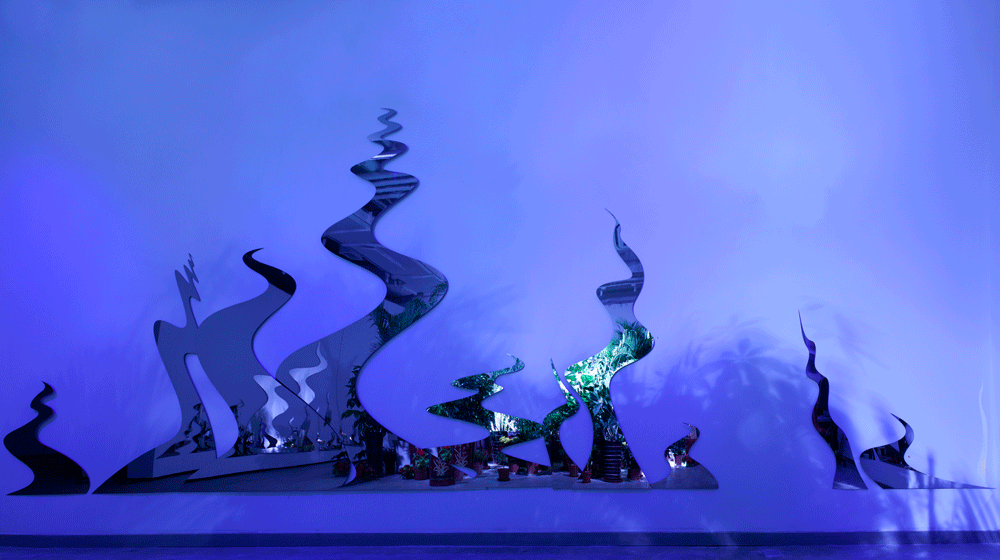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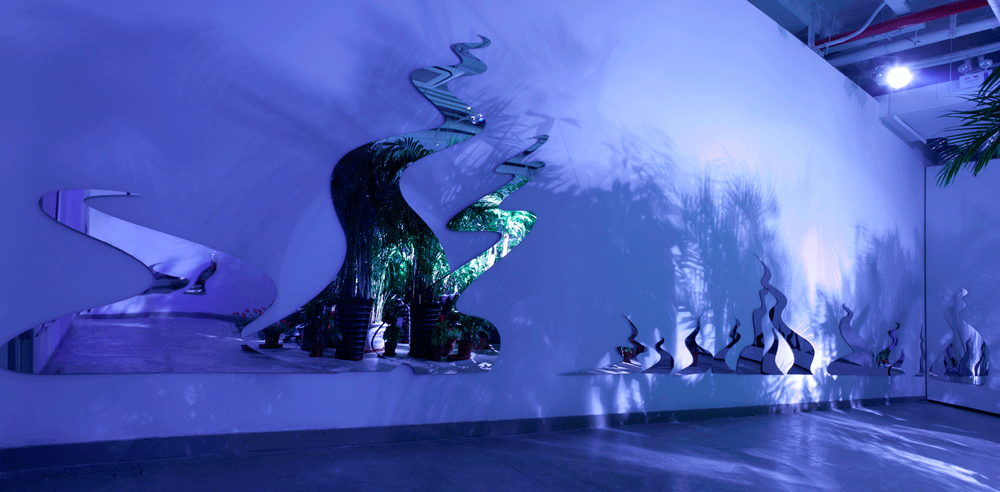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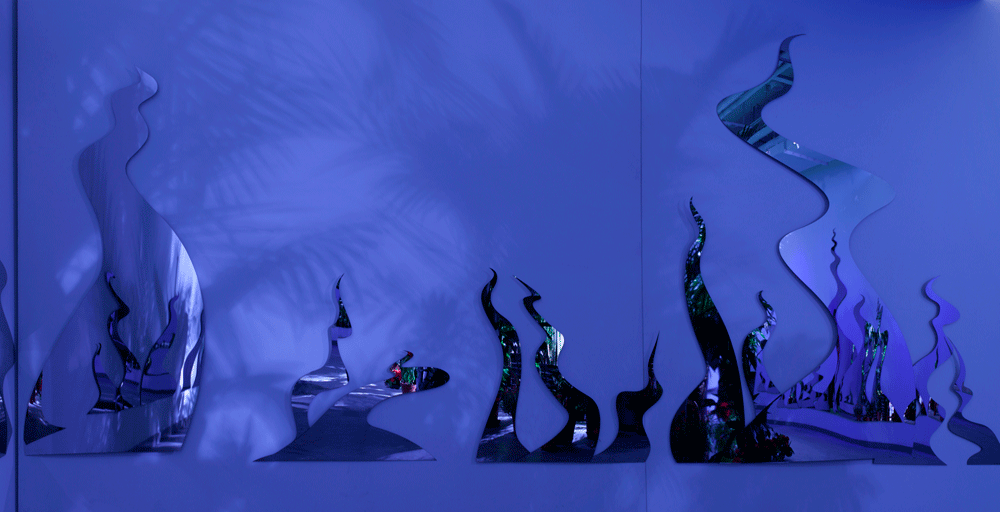

射云

无法命中的标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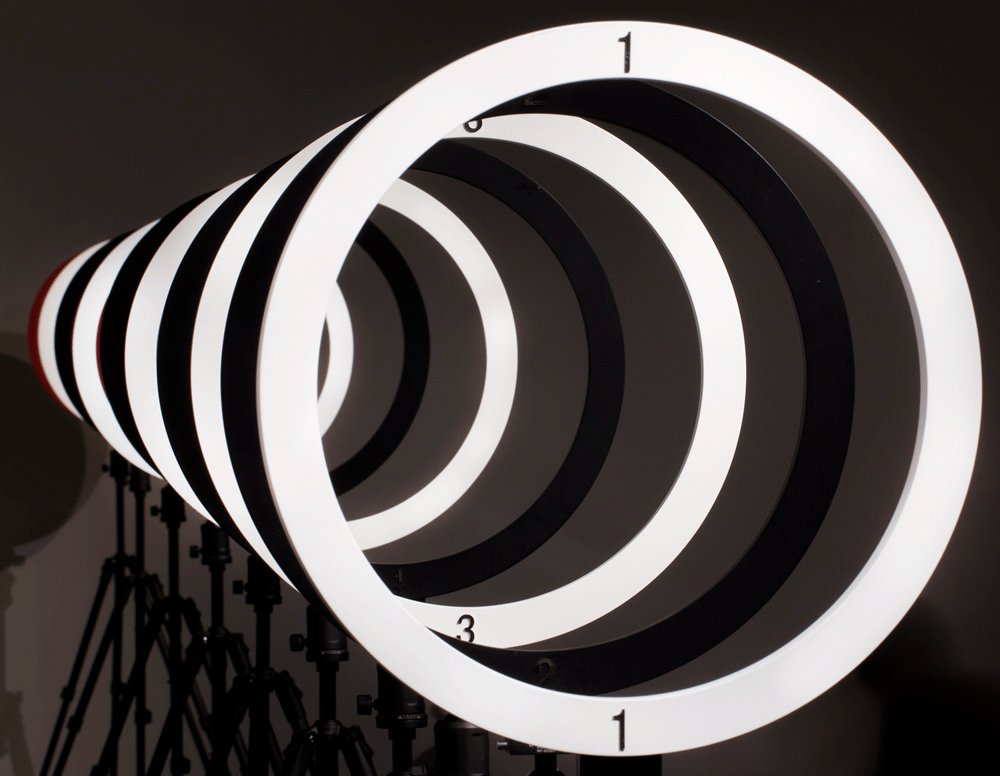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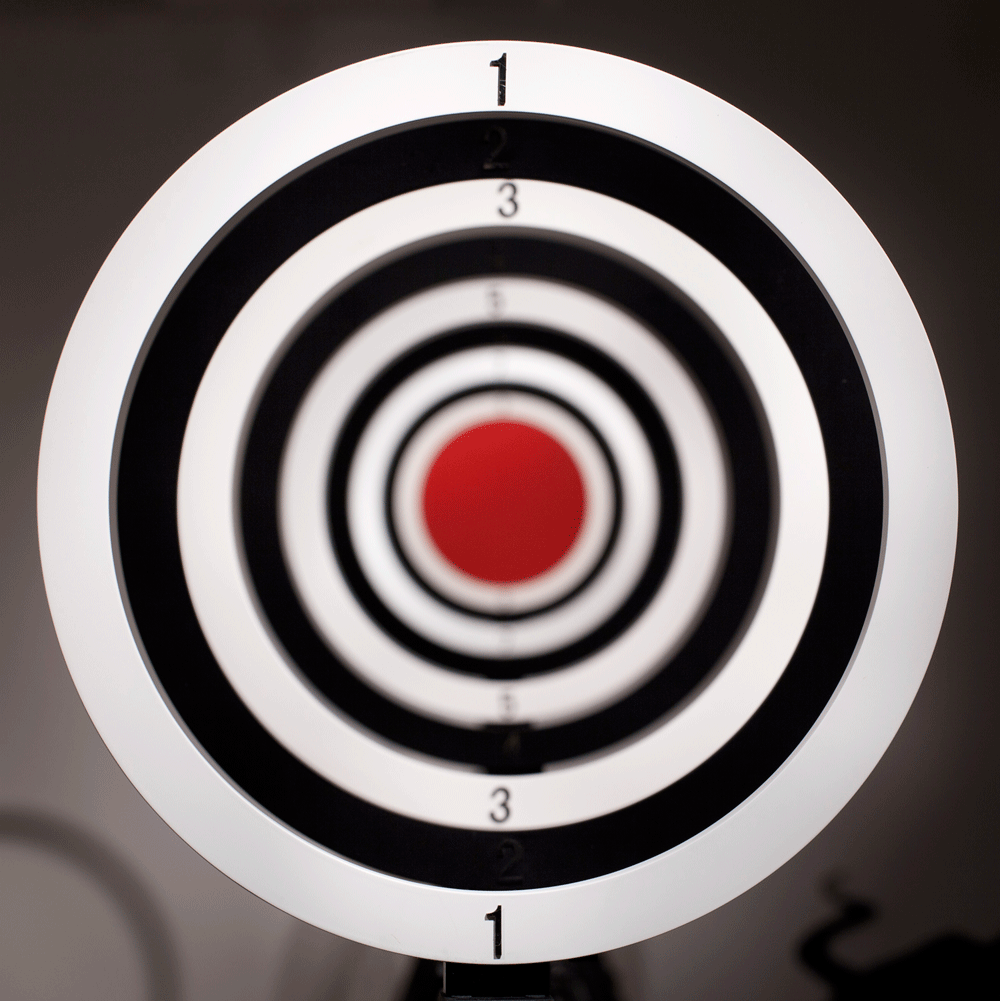


楼上
把弹簧切成上下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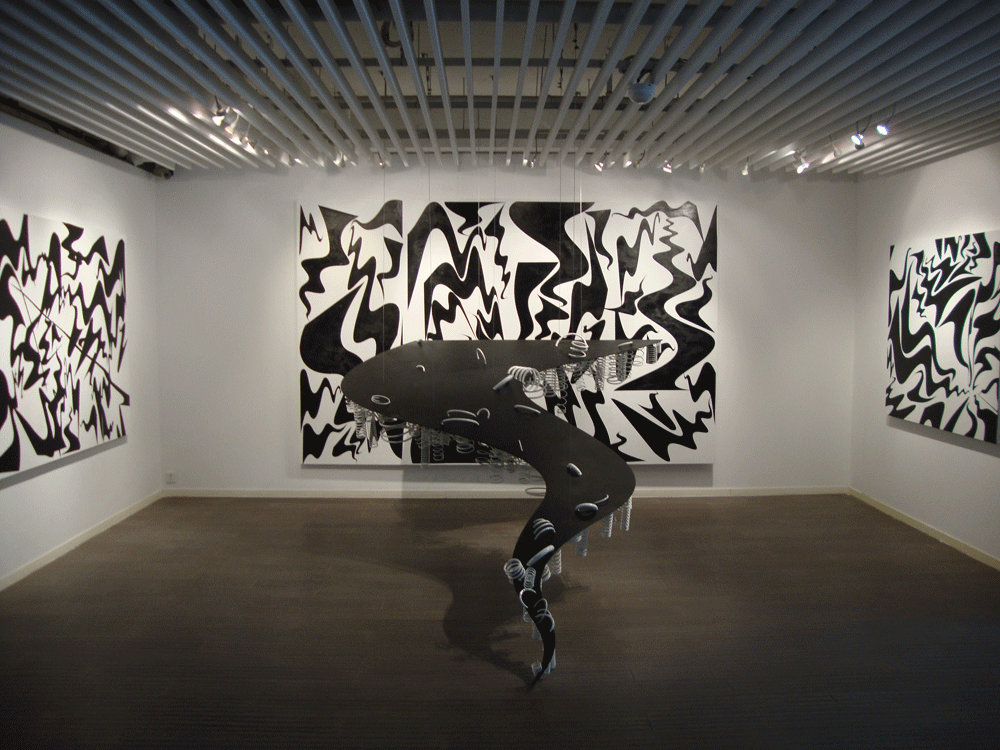


还有几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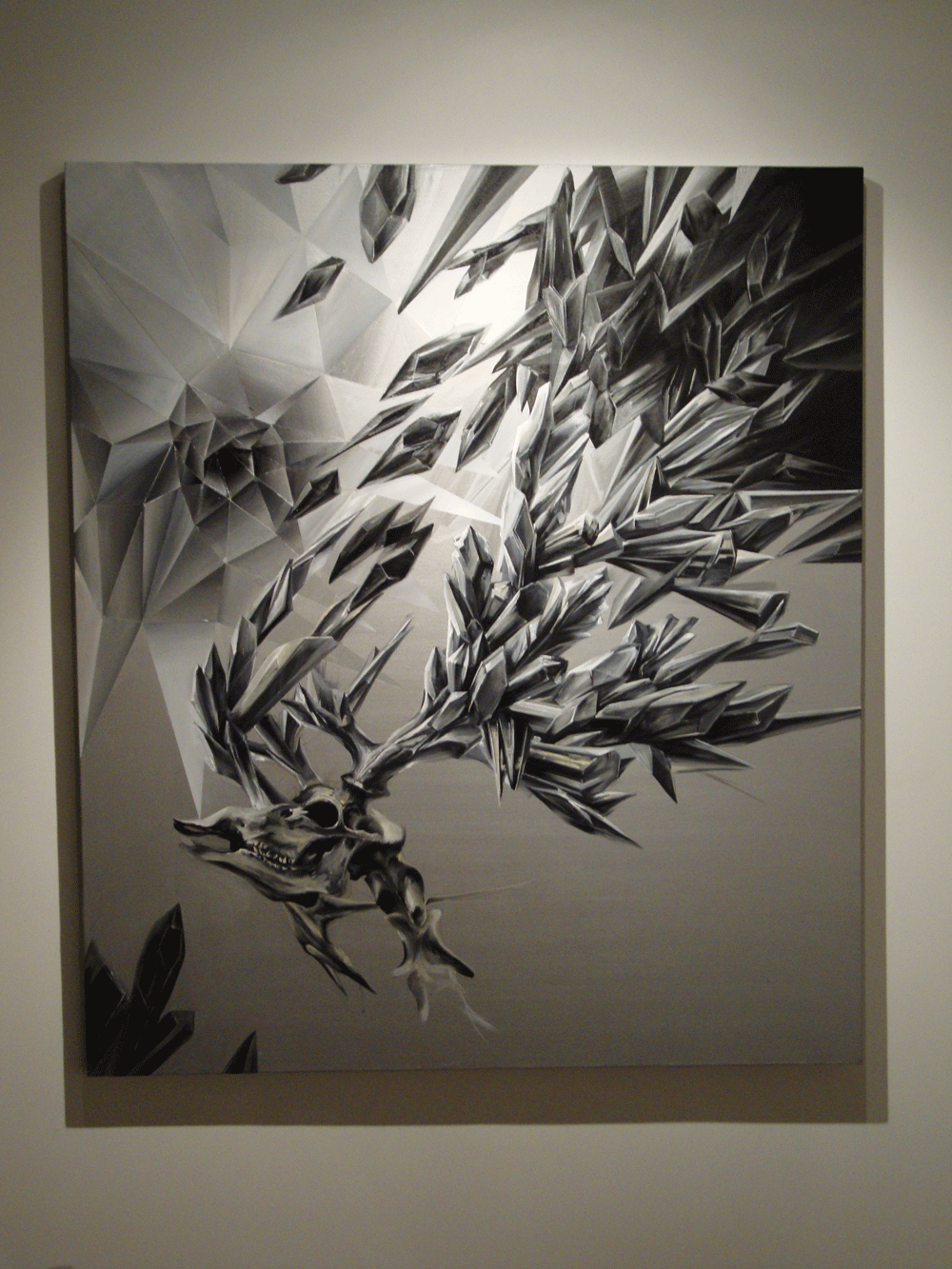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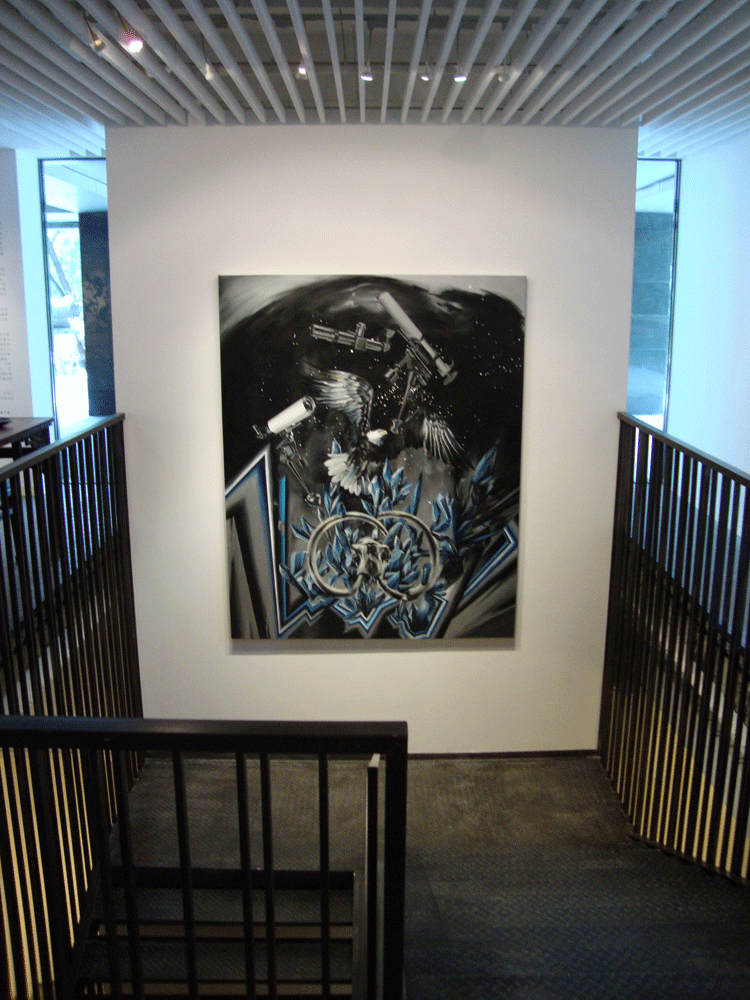

不锈钢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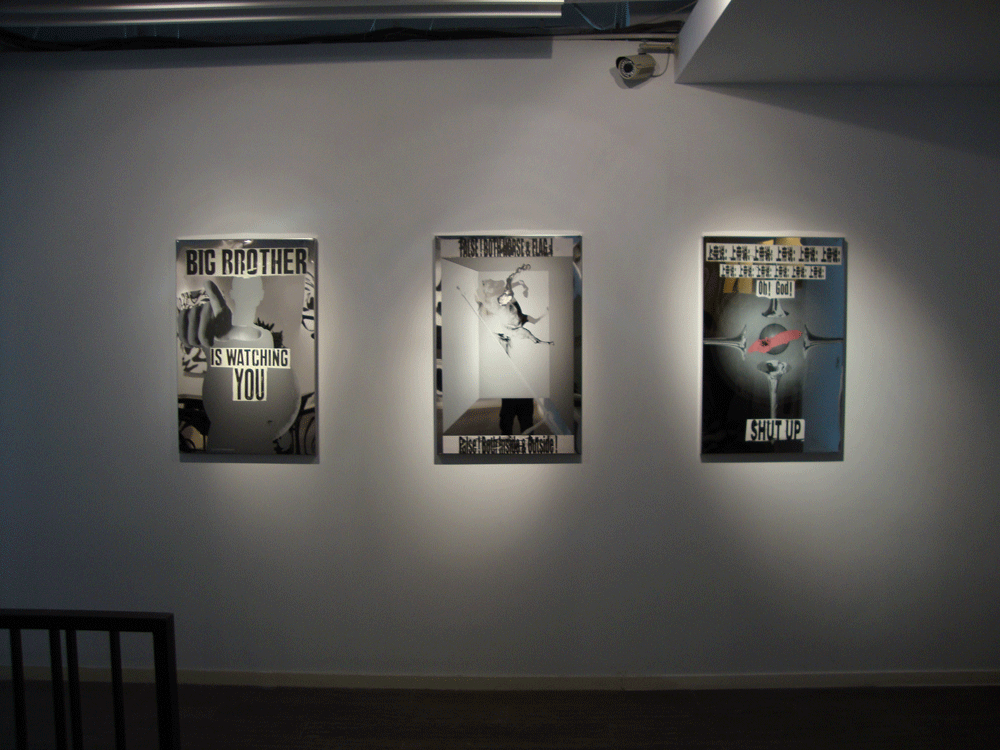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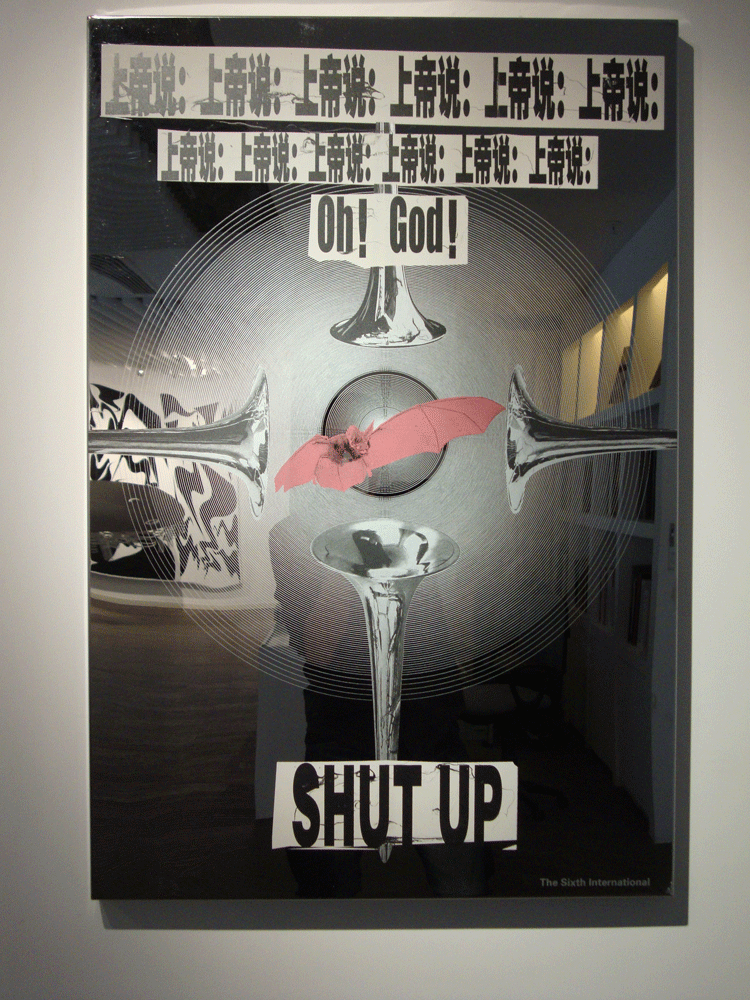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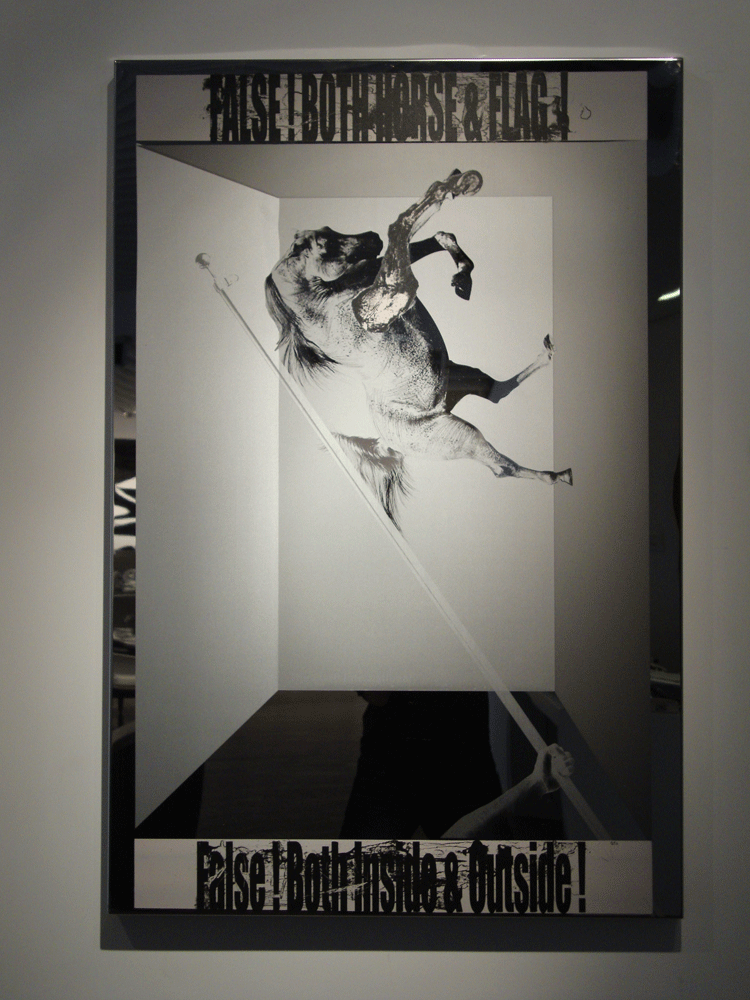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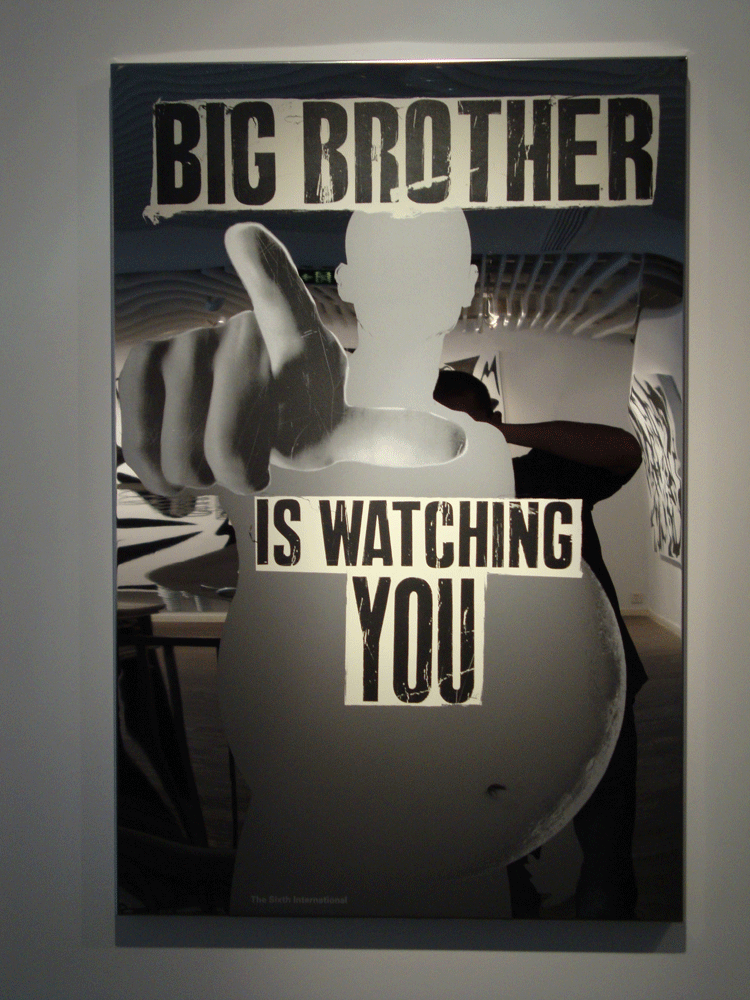
“射云”好作品,很智慧
蜿蜒zigzag
蜿蜒的道路把山川和湖泊,激进和保守分开成为左右,走在路上的行者总是得激励自己不断向前,社 会进化论犹如我们征服世界的圣经,把世界把分成了前和后,蜿蜒向前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分化我们站立和奔跑的地基。
而道路的追寻者和建造者多少由于形势所迫和对利益的追求罔顾对风险和方向的评估而一往无前,蔓延和扩张是前进的代名词,当道路一夜之间横亘大地之上,无数历史的细节和痕迹,无数个人的故事被这些抹去特征的荒芜之地瞬间覆盖,它来不及喘息就转身去开辟新的战场,而忘记去调理道路及其两边的关系。而且往往两边也是过于权益的划分。我们只见到蜿蜒的网络遍布世界,裹挟着某些非凡的创造力和别有用心一厢情愿给沿途带去了改变的力量,而另一些人则带着无知的热情和脆弱的理解接受他们还来不及消化的现实。太多的发展是没有结果的烂尾楼,更多的是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暴力,是知情者的圆滑纵容。高速发展的叙述并不能掩盖对代价的漠视,一些人的标准生活也不能替代未雨绸缪的风险评估,这社会总是能生产些好的,但是剩下的也不能都以灰色地带概之,更耐心的逐一去对每条道路做规划报告也许才是当下的理想主义。我不知道我是否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但是被围困在重重道路之际我也做了一些不知是否用的笔记,以此分出三个方面的作品:
《地下的蓝色》:在这个装置里森林和道路成为互为映像的无限世界。森林最终成为道路发展的模型,而道路也终将成为一片荒芜的森林蔓延开去。红黄绿的规则在这里成为活眼,他是道路的规则,在森林中却无奈的失效,而在无线扩张的道路/森林体系里面,他变成了体系的共谋者,变成一种带有装饰性的策略。在深夜无人的路口,我们依然停下车等待那还没变绿的红灯,我们等待的是什么?体系在幕后,道路成为一种标准化的监狱。一切都是陌生之地,一切似乎又家族相似般的亲切。
在大未来画廊的地下,我建构出一片蓝色的森林,美丽而脆弱,蓝色在此成为遥远的关怀,有待每一个来访者的猜测。
《把弹簧切成上下的道路》将道路和弹簧纠结在一种陌生的关系中,黑色的道路如此尖锐,把弹簧分成上下,枯骨还未成灰,地下依然蠢蠢欲动。观者在S路的尽头看向的是过去,它通向一个充满着变数的森林。这个尖锐的突出也许只是迷宫中一条没有特征的小径,在那里你是我的迷宫,我也成为你的迷宫。不管谁是谁非,我们最终会为自己亲手建造的迷宫买单。
《无法命中的标靶》和《射云》都指向了目标的不可能性。既定目标成为一种虚妄的历史决定论在云和同等大小的同心环中失去了准心。不,连关于射中和准心的这套叙述都是一种陷阱,总是有人在不可能提问之处提出一些假的问题。而身处这套系统中的人总是被鼓励去回答这些不可能的问题,这是我关于系统的恒久主题,我的工作的一个方面也正是扮演这样一个见缝插针、声东击西的黑客,对那些互相勾连的系统发出我的声音。
最后是几张我也难以把握的绘画,他们更多的偏离了我的设计在笔下自在发展,也正如我描绘他们的初衷。
他们不是细胞分裂的无限生殖,也不是道路般的蜿蜒穿梭,更不是人类爆炸式的蔓延和扩张,他们是结晶,是聚合,是沉积,是缓慢的力量,几万前他们是别种人生,几万年之后,他们尖锐而晶莹,他们是锻造和生长的雌雄同体。在这个什么都赶不及的时代,耐心是对效率的真正反抗。
为这些图像建立的联系打破了我习以为常的创作思路,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形式中,这些形式必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生长,最终沉积结晶。
道路依然在大地上蜿蜒,我们可以想像我画中那些黑色的小路最终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所有角落,只是 希望我们声称的那些未来不要随浮云一般在一阵狂风过后烟消云散。毕竟总有些事物会结成晶体带着信息将他们传播到远方。
这么牛B的艺术家怎么没人顶?妈的,你们还有点儿良知吗?
有几件精彩,最主要的部分还是图解
林天民眼光太烂,没办法,曹辉,引招洋都上了,这个小制做烂展也就那样.
你丫眼光好,你做了啥子好作品?
[quote]引用第6楼guest于2011-9-21 12:52:59发表的:
你丫眼光好,你做了啥子好作品?...[/quote]
我一直在画《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