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里没钱的日子懒得出门,走在路上心特别地容易发慌。做贼的感觉,心虚。找朋友借钱,他顺口说了句,你还帮人要债吗?我这儿有一2张借条。算是给我提了个醒,去重操旧业?不行了吧。但也不能让自已穷死,虽然这是暂时的境况,熬不过了,就得去找生路了。政府曾经关心过我,为我在小区保安队伍里谋取了一个维生的位子。我说,我这一生怕的就是坏人来抓我,那还有胆去赶小偷,别为难我了,最终背了个包庇\或同伙罪之类的,钱没赚,却又身陷囹囫了。
也罢,看看闲书,睡睡觉。半夜里出门,兜里放上平日里存下的小钱,往街头大排档上一蹲,喝点小酒,看看夜风景,谁也碍不着谁。
下午,乱翻罗兰巴特的书,从<恋人絮语>-到-<脱衣舞的幻灭>。首先是趣味性。别人的视角,就在这里面体现。所谓独特,我的理解决不是和行为乖戾有啥纠缠不清的暧昧。独特就是纯粹与拒绝的媾合体 --罗兰 巴特在<脱衣舞的幻灭>里讲"与一般成见相反,从头到尾伴随着脱衣舞表演的舞蹈,绝不是一种色情因素。也许正相反",涉及文学的评论家认为;在罗兰巴特看来,文学阅读如脱衣舞,读者对文本应该达到一种境界——巴特意义上的读者是很职业的:即一次次地对本文“出”“入”自由,本文好比脱衣舞表演,不应有很高的门槛,一般人都能“进”去,但如何接受却是由高门槛的;细读文本,把阅读的感受当作做爱的快感,把尽量高潮延后,拉长快感的享受时间,让快感阵阵播散于感官之中,在一次次的插入和抽出中体验文之悦;没有中心,脱衣舞的世界里没有中心,脱衣舞演员不是、脱衣舞本身不是、观众也不是,去除了中心的国度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参与者都是中心,文学阅读即把这种非中心化的思想发扬光大,把传统阅读里的主题、人物、情节、结构、思想统统解构掉,任凭语词、快感、能指的狂欢释放;阅读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抓到了中心以及与中心相关的连续、统一等诸要素,脱衣舞的世界里只有断裂(意义的断裂)、漂移(语词联系的打破)、悬浮(感官的持久上浮)。
类似的诠释,还有马尔加斯略萨,他认为,写作是一种颠倒的脱衣舞,把经验的世界一件件地穿上衣服,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在舞台上富有风格地表演出来。
色情,是用来界定心理状态时的一个概念词。 也许正相反,,我想到了自疗。我唯一有过的一次看脱衣舞的经历,(不在大陆,在朋友的私人领地,书房里) 。舞者,不是专业的脱衣舞蹈者,好象是学过表演的。因地适宜的即兴式表演,有着模仿的痕迹。但肯定与个人专业的阅读经验无关或共鸣,朋友是做摄影的。我在现场观赏时的冷静,出乎我的意料。到了最后,我总结了一句,这就是脱衣舞吗?不象啊。经验的误区,便是我们对每件事物的结果,寻找自圆其说的定性。艾柯的小册子《误读》里有篇叫《苏格拉底式的脱衣舞》他在里面讲,典型的脱衣舞关系(许看不许摸)中,决不允许享用那个已充分展露自身满足欲望能力的女人。所以就心理学而言,脱衣舞是一种受虐与虐待的关系。就社会学而言,这种受虐与虐待的关系是教育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脱衣舞在不知不觉中,教育了那些追求挫折、接受挫折的观众,让他们明白自己无法掌控生产资源。),“过于人们会在大庭广众面前掩盖的东西,现在成为大众娱乐的源泉”经验,应该是以自疗的方式重新开始。这也应该是艾柯的《误读》里想要讲明白的事儿。
看正文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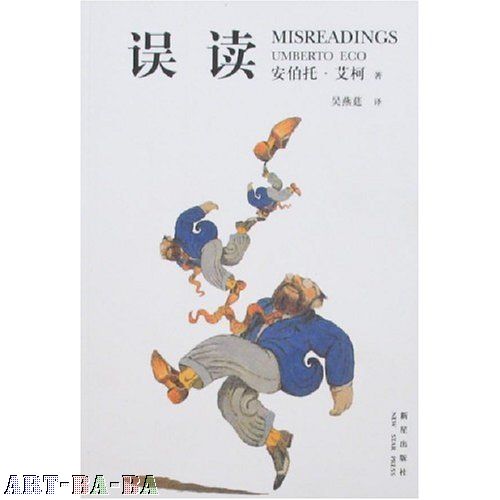

罗兰。巴特<脱衣舞的幻灭>
脱衣舞(至少巴黎的脱衣舞)是以一种矛盾为基础的:女人在脱光衣服的刹那间被剥夺了性感。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以恐惧的,或准确些说以“使我恐惧”的场景的意义为基础的。在这里色情似乎只是变成了一种美妙的惊恐,宣布了它的仪式化记号,以便使人既想到性,又想到性的魔法。
把观众变成观淫者的只是脱衣时花费的时间,但在这里正象在任何有神秘化作用的场景中一样,布景、道具和各种程式等一起和本来具有挑逗性的意图发生对抗,并终于使其淹没在无意义之中:宣布恶,以便更有效地阻止它和驱除其魔力。法国的脱衣舞似乎产生于我先前说的人造奶油的运作,这种神秘化作用在于对观众输入少许恶,以便之后将其淹没在永不遭受玷污的道理至善之中。结果由烘托表演的情境所突出的少许色情感,实际上被一种使人放心的仪式所吸收,这种仪式彻底地否定了肉体,正象牛痘疫苗和禁忌限制控制住疾病或罪行一般。
因而在脱衣舞表演中,随着她佯装要把衣服脱光而有一整套遮掩物覆盖在女人的躯体上。异国情调是这些障碍中的第一项,因为它永远具有一种固定性,这种性质把躯体放逐到传说或浪漫世界中去。例如,一个“中国女人”手拿着大烟枪(“中国女子”必不可少的象征),一位混身扭捏的荡妇配着一支特大的烟嘴,带有贡杜拉小船的威尼斯布景,带裙撑的女服和唱小夜曲的人,这一切从一开始就要把女人造成一个伪装的对象。于是脱衣舞表演结束时并未使隐蔽的深处显明,而是通过脱去不协调的和人为的衣衫使裸体意味着女人的一件自然的衣服,从而最终相当于重新恢复了肉体的绝对贞洁。
音乐厅的古典道具总是为脱衣舞表演所用,这类道具永远使不着衣衫的身体更显得疏远,并迫使它回到一种熟悉的仪式具有的弥漫舞台的轻松氛围之中:皮大衣、羽扇、手套、头饰、网状丝袜。总之,整整一套装饰物使活生生的人体归入了豪华物件类,这些物件用魔术般的装饰把人包围起来。披戴着羽饰或配戴着手套的女人在表演中相当于音乐厅中的一个固定成分;她脱掉这些饰物时的方式极具仪式性,以致于不再象是真正的脱衣动作了。羽饰、皮大衣和手套即使去掉以后也仍然以它们的魔力留在女人身上,赋予她某种使人想起一个豪华躯壳的东西,因为不言自明的规律是:整个脱衣舞的效力是存在于女人身上最初的衣衫本性之中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我们在中国女人或穿皮大衣的女人的例子中所见,后来出现的裸体就仍然是非真实的,无刺激力的,被裹严着的,正象一件美丽光滑的物体,由于它被人们过分使用而失去作用一样。这就是挂满宝石或金币的内裤具有的深刻意义,它只能是脱衣舞生命的结束。这块最后的三角,连同它的纯几何形状,它的光亮硬挺的质地,就象一把纯洁的利剑挡住了通往性部位的通路,并肯定将女人驱入了一个矿物世界;在这里宝石成了纯粹物性的不可否认的象征,对于任何目的来说它都不再有任何用处了。
与一般成见相反,从头到尾伴随着脱衣舞表演的舞蹈,绝不是一种色情因素。也许正相反,有节奏的轻微扭动此时驱散了手足无措的担心,它不仅赋予表演以艺术的借口(脱衣舞表演中的舞蹈永远是“艺术性的”),而且更主要的是它构成了最后一道障碍,而且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舞蹈是由已被看过千万遍的仪式化姿势组成,其动作具有一种装饰性,并使场景披上一种多余而又必要的姿势保护层,因为在这里,裸露行为被转化为在不大可能发生的背景中实现的依附性活动领域了。于是我们看到脱衣舞职业演员都处在令人惊异的轻松气氛中,这种气氛始终围绕着她们,使她们显得远不可及,使她们流露出熟练从业员具有的冷冰冰的无所谓的神情,高傲地躲藏在对本身技巧的自信中,结果,她们的专门技巧给她们披上了衣裳。
驱除性魔的所有这些细致的技巧,都可在业余脱衣舞“民间比赛”(sic)中从相反方面加以证实。在这里“新手”当着几百名观众脱去衣服,没有魔术的凭借或只能笨拙地求诸于魔法的护佑,这就肯定地使场景恢复了其色情力量。此时,我们一开始看到少数中国或西班牙女人,没有(剪裁入时的)羽饰或皮大衣,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伪装物,笨拙的步法,糟糕的舞姿,姑娘们老是担心无所动作,尤其是担心“技巧的”拙劣(短裤、外衣或胸罩的妨碍),这一切使得脱衣动作的姿态具有了一种出乎意料的重要性,否定了女人的艺术性假托和成为一件物体的逃避所,将其拘束在脆弱无依与羞怯难当的状态中。但是,在“红磨坊”舞厅,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类性的驱魔术,或许这是典型法国式的,这种驱魔术实际上与其说会使色情感失效,不如说想将其驯服。演出指挥者企图赋予脱衣舞一种使人心安的小资产阶级身份。首先,脱衣舞是一种运动。这里有一种脱衣舞俱乐部,它组织健康的比赛,获胜者头戴皇冠走到台前并领取有教育意义的奖品(对身体训练课的一种赞助),一本小说(它只能是罗伯—格里叶《窥视者》一类的书)或有用的奖品(一双尼龙袜,五千元法朗等)。这样,脱衣舞就被看成了一种专业(其中有新手、半职业家、职业家),也就是一种专业化的可敬的训练(脱衣舞者成了技术性工人)。人们甚至可以使其以工作作为有魔力作用的托词:即职业。人们会说,一个姑娘“干得好”或“前途大有可为”,或只说在艰难的脱衣舞表演中“刚迈出第一步”。最后尤其重要的是,竞争者都具有社会位置,她可以是女售货员或女秘书(在脱衣舞俱乐部中有很多女秘书)。在这种情况下,脱衣舞又重新被纳入公共世界,为人们所熟悉和成为资产阶级的。似乎法国人与美国观众不同(至少据说如此),他们都遵循着自己社会身份的不可违抗的倾向,只有赋予色情表现以某种习常性质才能对其加以设想,这种习常性,更多地是由每周体育运动为借口,而很少是由一种魔术般的场景的假托加以认可的。因此在法国脱衣舞已被民族化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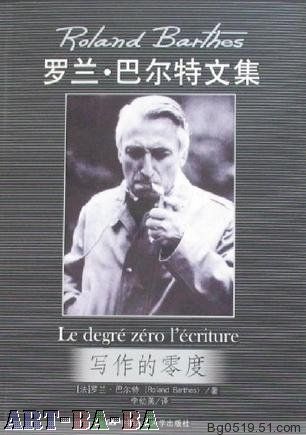
小u的脱衣舞视图。



楼上是朱大可还是汪民安啊

